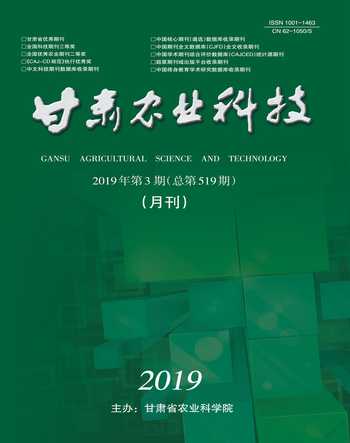起壟覆蓋方式對旱地馬鈴薯主要性狀的影響
張文偉 李利利 李可夫 陸立銀
摘要:研究了不同起壟覆蓋方式對隴薯7號、冀張薯8號、莊薯3號生育期、主要性狀及產量的影響。結果表明,在黑膜覆蓋壟上覆土方式下,莊薯3號、冀張薯8號、隴薯7號折合產量分別為32 840、46 490、41 050 kg/hm2,較對照露地栽培增產顯著,增產率分別達到31.85%、35.25%、18.90%。綜合考慮認為,隴薯7號、冀張薯8號綜合農藝性狀、產量表現較優,適宜在慶陽市種植,北部縣區推薦選用黑膜覆蓋壟上覆土方式,南部縣區推薦選用玉米秸稈帶狀覆蓋方式。
關鍵詞:馬鈴薯;旱地;起壟覆蓋方式
中圖分類號:S5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1463(2019)03-0062-07
doi:10.3969/j.issn.1001-1463.(2019)03.013
Abstract: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ridge-forming and film-covering modes on growth period, main characters and yield of Longshu 7, Jizhangshu 8 and Zhuangshu 3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yields of Zhuangshu 3, Jizhangshu 8 and Longshu 7 under the black film mulching ridge were 32 840, 46 490 and 41 050 kg/hm2,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of open cultivation, with the increase rates of 31.85%, 35.25% and 18.90% respectively. It is considered that Longshu 7 and Jizhangshu 8 had the best comprehensive agronomic traits and yield performance. They were suitable for cultivation in Qingyang City. Black film mulching on ridges was recommended in northern counties, and belt mulching with corn straw was recommended in southern counties.
Key words:Potatoes;Dryland;Ridge-forming and film-covering modes
西北黃土高原半干旱區干旱少雨、降水量時空分布不均、田間蒸發量大、農田生產低而不穩[1 ]。馬鈴薯在甘肅省大部分縣區都有種植,慶陽市近年種植馬鈴薯面積平均在3萬hm2以上,主要分布在環縣、華池縣等北部縣區[2 ]。為響應農業部提出的推動馬鈴薯主食化戰略,當地農業技術部門不斷開展新品種、新技術的試驗研究,總結和完善配套栽培技術,服務馬鈴薯產業發展[3 ]。地表覆蓋具有抑草、增溫、保墑、蓄水等作用,并使土壤保持良好結構,有利于根系生長發育及土壤微生物的活動,增強后期植株根的吸收能力[4 - 5 ]。同時,起壟種植能增加馬鈴薯結薯層,是馬鈴薯增產最為有效和簡便的技術[6 ]。我們于2017年開展了不同起壟覆膜方式試驗,以期為馬鈴薯生產中合理選用種植模式,降低成本、提高產量和品質提供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地概況
試驗區位于甘肅省慶陽市寧縣和盛鎮湫包頭村,土層深厚,光照充足,氣候溫和,屬干旱半干旱氣候。年均氣溫7~10 ℃,年日照時數2 250~2 600 h,無霜期140~180 d,年均降水量480~660 mm。試驗地土壤為黑壚土,肥沃疏松,質地均一、通氣性好,前茬作物為谷子。
1.2 供試材料
指示馬鈴薯品種共3個,隴薯7號和冀張薯8號由甘肅省農業科學院馬鈴薯研究所提供,莊薯3號由華池縣種子管理站提供。種薯材料在播前酌情進行晾曬催芽處理,并進行切塊和藥劑拌種。拌種劑選用甘肅省農業科學院馬鈴薯研究所栽培項目組研制的馬鈴薯抗旱防病拌種劑(拌薯寶TM,專利號:ZL201210097283.7)。
1.3 試驗方法
試驗于2017年進行,采用二因素隨機區組設計。設3個馬鈴薯品種(A)為主區,即莊薯3號(A1),冀張薯8號(A2)、隴薯7號(A3);4種起壟覆蓋方式(B)為副區,即,B1為黑膜覆蓋壟上覆土。人工起壟,壟高10 cm,壟面寬80 cm,壟溝寬45 cm。選擇厚0.01 mm、幅寬120 cm的黑色聚乙烯地膜,將地膜緊貼壟面,兩邊埋入壟溝內,壓緊踏實。同時,從壟溝取土在壟上覆土5~10 cm。B2為黑膜覆蓋膜上微溝。起壟及覆膜方式同處理B1。在壟面上的兩個種植行位置用開溝鋤劃微溝,深10 cm,壟面中間略高。B3為玉米秸稈帶狀覆蓋[1, 7 ]。采用起壟覆稈技術。覆蓋帶在壟間,寬55 cm,種植帶在壟上,寬70 cm,每種植帶種植2行。總帶幅125 cm。B4為露地平作(CK)。3個品種和4種覆蓋方式共12個處理組合,小區面積20 m2(5 m×4 m),每小區種植6行,每行16株,3次重復,小區四周設保護行。于2017年4月中旬結合整地施有機肥 45 000 kg/hm2、N 198.0 kg/hm2、 P2O5 142.5 kg/hm2、 K2O 75.0 kg/hm2。肥料人工均勻撒于地表,用旋耕機旋入土壤耱平。4月26日播種[7 ],采用挖穴器挖穴后人工點播種植,種植深度10~15 cm,每穴點播1個塊莖,芽眼向上。南北成行,行距60 cm,株距33 cm,密度48 000穴/hm2。生育期中耕除草2次,其他管理措施同大田。9月20日收獲,每小區取連續10株考種,全區收獲計產。
1.4 數據分析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03整理數據,用spss12.0進行數據統計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處理對馬鈴薯生育期的影響
由表1可以看出,在不同覆蓋方式且播種期一致的情況下,3個馬鈴薯品種的生育期有差異。3個品種在不同覆蓋方式下生育期在118~122 d左右,其中莊薯3號玉米秸稈帶狀覆蓋處理(B3)的生育期為121 d,其余3種覆蓋方式的生育期均為120 d,在生育期內表現無蕾。冀張薯8號玉米秸稈帶狀覆蓋處理(B3)的生育期均為121 d,黑膜覆蓋壟上覆土處理(B1)和黑膜覆蓋膜上微溝處理(B2)的生育期均為119 d,露地平作處理(B4)的生育期為118 d。隴薯7號玉米秸稈帶狀覆蓋處理(B3)的生育期為122 d,露地平作處理(B4)為121 d,黑膜覆蓋壟上覆土處理(B1)和黑膜覆蓋膜上微溝處理(B2)的生育期均為119 d,可見黑膜覆蓋能使隴薯7號早出苗、早成熟,使其生育期縮短。
2.2 不同處理對馬鈴薯生長性狀的影響
由表2可以看出,不同參試品種間出苗率的差異較大。莊薯3號在4個處理下出苗率無差異。冀張薯8號和隴薯7號出苗率受覆蓋方式影響較大,其中處理A1B3、A1B4的出苗率最高,處理A3B1的出苗率最低。對莊薯3號而言,處理A1B3、A1B4的出苗率最高,均為98.26%;處理A1B2的出苗率最低,為96.88%。對冀張薯8號和隴薯7號而言,處理A2B4、A3B3的出苗率最高,均為95.49%;A2B2、A3B1較低,分別為93.06%、88.89%。
不同參試品種的株高差異顯著,不同覆蓋方式對株高的影響因品種而異,二者交互作用極顯著。株高為59.8~78.6 cm,其中處理A3B3最高,A1B4最矮。對隴薯7號而言,不同處理下株高差異不顯著,處理A3B1最矮,為75.7 cm;A3B3最高,為78.6 cm。對冀張薯8號而言,處理A2B2最矮,為68.0 cm;處理A2B4最高,為71.9 cm;處理A2B1、處理A2B4間差異不顯著,兩處理與處理A2B2、A2B3差異不顯著。對莊薯3號而言,處理A1B4最矮,為59.8 cm;處理A1B1最高,為64.4 cm;處理A1B1、A1B2、A1B3之間差異不顯著,均與處理A1B4差異顯著。
不同參試品種間主莖數有差異,不同覆蓋方式對主莖數的影響受品種的影響較大,二者交互作用無顯著差異。在3個品種、4種覆蓋式中,主莖數處理A3B1、A3B3較高,A1B4最矮。對隴薯7號而言,以處理A3B1最多,為2.8個;A3B2、A3B4最少,均為2.2個;處理A3B1、A3B3顯著高于A3B2、A3B4。對冀張薯8號而言,處理A2B1最多,為2.1個;處理A2B2、A2B4最少,均為1.9個;4個處理的主莖數無差異。對莊薯3號而言,處理A1B1、A1B2、A1B3高于處理A1B4,其中以處理A1B1最多,為2.1個;處理A1B4最少,為1.8個。
2.3 不同處理對馬鈴薯產量性狀及商品薯率的影響
由表3可以看出,不同品種間和覆蓋方式間單株結薯數差異不顯著。不同品種間,莊薯3號單株結薯數最多,平均為9.23個;隴薯7號最少,平均為8.24個。冀張薯8號在B2處理下最多,為9.0個,在處理B1下最少,為7.83個。不同覆蓋方式間,處理B3的單株結薯數最多,平均為9.37個。其中,處理A1B3單株結薯數最多,為10.27個;處理A3B2單株結薯數最少,為7.6個。
莊薯3號的單株塊莖鮮重和平均單薯重均低于其余2個品種,平均分別減少200、32.35 g。不同覆蓋方式之間存在極顯著差異,相同覆蓋方式下,處理B1、B2、B3較處理B4均能顯著增加單株塊莖鮮重,平均值最大增加了220.0 g。處理A2B1的單株塊莖鮮重最高,為1 008.0 g;處理A1B4最低,為595.0 g。不同覆蓋方式之間,處理B1、B2較B4顯著增加,分別增加了30.62 g和32.34 g;B3與B4沒有明顯差異。從品種和覆蓋方式綜合來看,A2和A3在B1、B2方式下均能顯著增加馬鈴薯單株塊莖鮮重和單薯重。
馬鈴薯商品薯率在品種間和覆蓋方式間均存在顯著差異,二者交互作用無顯著差異。不同品種間的商品薯率差異較大,莊薯3號商品薯率最低,平均為74.94%,隴薯7號和冀張薯8號和商品薯率平均都在85%以上。從覆蓋方式來看,黑膜微溝方式下商品薯率最高,平均為86.55%;秸稈覆蓋下商品薯率最低,平均為79.01%。綜合品種和覆蓋方式來看,A3B2處理下商品薯率最優,為92.32%;其次是A2B1和A2B2,分別為89.84%和89.05%。
由表4可以看出,不同品種和覆蓋方式對馬鈴薯單株結薯數無顯著影響,覆蓋方式間單株塊莖鮮重、平均單薯重差異極顯著,品種間和覆蓋方式間馬鈴薯商品薯率分別存在顯著差異和極顯著差異,但品種和覆蓋方式交互效應對單株塊莖鮮重、平均單薯重和商品薯率影響不顯著。
2.4 不同處理對馬鈴薯產量的影響
由表5可以看出,不同品種間,冀張薯8號和隴薯7號產量表現均優,平均折合產量分別為38 716.25、38 756.25 kg/hm2,顯著高于莊薯3號(平均折合產量28 761.8 kg/hm2)。不同覆蓋方式之間,黑膜覆土產量最高,顯著高于其余處理;其次是黑膜微溝和秸稈覆蓋;露地產量最低。從品種和覆蓋方式綜合效應來看,以處理A2B1的產量最高,為 46 490 kg/hm2,較處理A2B4增產35.25%;其次為處理A3B1、A3B3、A3B2,折合產量分別為41 050、40 325、39 125 kg/hm2,較處理A3B4分別增產18.90%、16.80%、13.32%;處理A1B4產量最低,為24 910 kg/hm2。
方差分析(表6)表明,區組間產量差異不顯著,而A因素品種間、B因素覆蓋方式間產量差異均達到極顯著水平, A×B交互效應產量差異顯著。這說明,無論是改變馬鈴薯的品種還是改變馬鈴薯的覆蓋方式,或者同時改變馬鈴薯的品種和覆蓋方式,均對馬鈴薯產量有顯著影響。
3 小結與討論
試驗結果表明,馬鈴薯的農藝性狀及產量指標因品種特性而異。不同覆蓋方式對生育期、株高、主莖數、單株結薯數、單株塊莖鮮重、平均單薯重、商品薯率及產量等指標均有影響。在黑膜覆蓋壟上覆土方式下,莊薯3號、冀張薯8號、隴薯7號折合產量分別為32 840、46 490、41 050 kg/hm2,較對照露地栽培增產顯著,增產率分別為31.85%、35.25%、18.90%。綜合考慮認為,隴薯7號、冀張薯8號綜合農藝性狀、產量表現優,適宜在慶陽市種植。
馬鈴薯的生育期時間和生育期天數受覆蓋方式影響較大,主要原因在于不同覆蓋方式影響土壤水分、光照、地溫等[8 ],進而影響到生育期時間及生育期天數。不同品種間生育期的長短隨品種特性、生態條件而變 化[9 ]。品種間出苗率差異較大,受覆蓋方式影響較小,主要與品種的發芽情況和土壤因素有關。不同參試品種間的株高差異顯著,不同覆蓋方式對株高和主莖數的影響因品種不同而異,這與劉孝榮等[10 ]的結論一致。不同品種間的單株結薯數及單株塊莖鮮重差異顯著,進而影響到單薯質量差異顯著。栽培方式對單株結薯數、單株塊莖鮮重及平均單薯重影響顯著。與露地種植相比,黑膜覆土抑制單株結薯數的增加,但有利于地上主莖數和平均單薯重的增加,進而影響產量。單株結薯數和單株鮮薯重呈正相關,結薯數越高,重量越重[11 ]。選用不同覆蓋方式均可促進馬鈴薯產量的增加[12 ]。
試驗地位于慶陽市南部,6 — 9月份降雨比較集中,也極易發生高溫危害,正好處在馬鈴薯塊莖形成期和塊莖生長期。降水集中時容易造成積水,進而影響馬鈴薯的結薯率、產量和品質[3, 13 ]。高溫時地表溫度過高,可造成植株徒長,尤其地膜覆蓋容易造成燒苗等問題。而玉米秸稈覆蓋不但能提溫,對于后期高溫還具有緩解效能,加之材料易得,成本低廉,在提高馬鈴薯產量的同時,可有效解決使用地膜造成的塑料污染問題[14 ]。
綜合考慮地域、光照、降水、土壤肥力等因素,在慶陽市北部縣區,因其海拔較高,降水量較少,土壤養分狀況較差,山、臺地多,氣候冷涼,推薦選用黑膜覆蓋壟上覆土種植方式,配合種薯處理、配方施肥、合理密度種植、病蟲害防控等技術,可集雨保墑、抑制雜草,在保證產量的同時減輕土壤水肥等壓力,起到養地蓄肥的作用。在慶陽市南部縣區,因其海拔較低,降水量相對較多,地勢平坦、土壤肥力狀況較好,推薦采用玉米秸稈帶狀覆蓋種植方式,并選用早熟品種,可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時起到倒茬、抑制病蟲害發生和蔓延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韓凡香,韓 磊,柴守璽,等. 半干旱雨養區秸稈帶狀覆蓋種植對土壤水分及馬鈴薯產量的影響[J]. 中國農業生態學報,2016(7):874-882.
[2] 張文偉,李 峰,耿智廣,等. 慶陽市引進馬鈴薯新品種(系)兩種栽培方式差異比較研究[J]. 農業科技通訊,2017(8):85-90.
[3] 李元有. 旱地秸稈帶狀覆蓋馬鈴薯高產高效栽培技術[J]. 農業科技與信息,2017(8):56.
[4] 王海泉,欒曉燕,滿為群,等. 覆膜栽培大豆的土壤生態效應研究進展[J]. 大豆科學,2009(4):28-31.
[5] 譚軍利,王林權,李生秀. 地面覆蓋的保水增產效應及其機理研究[J]. 干旱地區農業研究,2008(3):50-53.
[6] 鄭元紅,王嵩,何開祥,等. 不同栽培方式對馬鈴薯產量影響研究[J]. 耕作與栽培,2008(3):12-13.
[7] 柳永強,萬繼東,陸立銀,等. 甘肅中東部雨養梯田馬鈴薯綠色高效栽培技術[J]. 中國種業,2018(9):96-97.
[8] 王 耀. 不同覆膜栽培模式與播期互作對寒旱區馬鈴薯商品性和產量的影響[J]. 中國馬鈴薯,2016(3):149-153.
[9] 牛紅莉. 秸稈帶狀覆蓋方式對種植馬鈴薯的影響[J]. 農業科技與信息,2017(13):73-74.
[10] 劉孝榮,梁小平,葉曉東,等. 旱塬地馬鈴薯不同品種栽培方式的研究[J]. 內蒙古農業科技,2008(1):38-39;49.
[11] 楊培軍,余秀珍,孫成軍. 黑色膜及不同覆蓋方式對馬鈴薯產量效應研究[J]. 寧夏農林科技,2013(6):56-60;109.
[12] 張文偉,耿智廣,黃浩鈺,等. 不同栽培調控措施對馬鈴薯產量及效益的影響[J]. 中國馬鈴薯,2017(3):144-148.
[13] 買自珍. 不同膜色和覆蓋方式對馬鈴薯地溫及水分效應的影響[J]. 寧夏農林科技,2011(5):3-4;25.
[14] 馬生發. 馬鈴薯不同覆蓋栽培方式對土壤環境和產量的影響[J]. 隴東學院學報,2013(3):48-51.
(本文責編:楊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