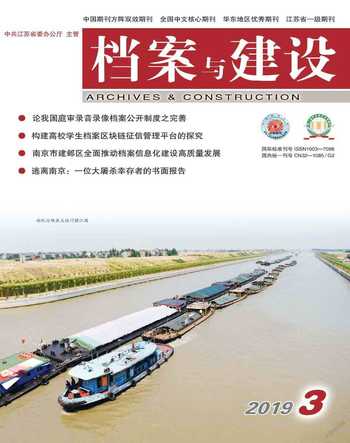清代運河經濟中淮揚官場的廉貪現象
[摘要]淮揚一帶憑借大運河鹽漕運輸以及水利等功能,幾度發展繁榮。特別是清代鹽務興盛,康熙、乾隆二帝各六次南巡,大小官員高度集聚,給城市經濟帶來繁盛。同時,廉政與貪腐一直是朝廷乃至坊間關注的焦點。論文以清代宮廷檔案以及典籍史料為依據,列舉數個典型案例,旨在揭示貪腐案產生的原因,以史為鑒。
[關鍵詞]運河經濟淮揚官場廉腐
有清一代的260余年里,貪腐犯罪與整個清王朝相始終。大案驚天,小案如毛,整個官場呈現出勢不可擋的腐敗之勢。據有關史料記載,清代朝廷懲處的中央、地方一、二品滿漢軍政大員的經濟犯罪案件共109件,處理一、二品大員132人。貪與反貪、腐與反腐貫穿了整個清朝。[1]近觀淮揚一帶,大運河運輸功能與作用顯得尤為重要,在數百年里成為了城市興盛的必備條件。憑借運河鹽、漕運輸,特別是食鹽的生產、銷售、貯存、轉運,淮、揚、泰等城市迅速發展興盛,成為當時中國乃至世界有名的富庶之地。歷史上,淮安、揚州曾與杭州、蘇州一道并稱為運河邊上的四大都市。
經濟繁榮,必然得到朝廷的重視。歷史上,淮安曾是漕運樞紐、鹽運要沖,駐有漕運總督府、江南河道總督府,有“中國運河之都”的美譽。另就揚州而言,由于兩淮鹽漕察院署等諸多鹽務管理機構的設立,清廷位高二品的鹽政御史與地方的鹽官、知府、縣令等形成龐雜的官場體系。他們之間既互相勾結、互相利用,又互相猜忌、互相爭斗,貪腐現象時有發生。隨著朝廷走向沒落,淮揚的官場上沉渣泛起,曾出現多個貪腐大案以及被朝廷誅殺懲罰之人。僅乾隆三十三年,揚州就有高恒、盧見曾、吉慶、普福等鹽官先后被革職查處。而乾隆五十七年,有被乾隆帝多次稱為“大奇”的柴楨貪腐案中案,多個涉案官員受到懲處。
不可否認的是,歷朝歷代淮揚的官場也不乏務實勤廉、受百姓愛戴的廉官,如高斌、張應詔、曾燠等。
高斌、高恒:父與子的不同人生軌跡
高斌,慧賢皇貴妃之父,清朝中期大臣。自雍正元年(1723)起,高斌歷任內務府主事、蘇州織造、廣東布政使、浙江布政使、江蘇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江寧織造、江南河道總督、直隸總督、文淵閣大學士等。高斌一生為官多職,堪稱朝廷重臣。值得今人稱道的還數他致力于治河一事,多份奏折記載下他治理河務的業績。乾隆三年(1738)正月,依高斌所奏,在淮、揚運河清河口至瓜州段相應建閘修壩的工程完畢,高斌得到朝廷的嘉獎。[2]
乾隆十四年,66歲的高斌仍然堅守在河官任上。七月二十二日,他與協辦河道事務張師載的奏疏《奏為淮揚一帶低田被淹不至成災情形事》[3]一折,通過深入調查獲得的里下河各地雨水、田禾長勢、民間存糧乃至民風民情等一手數據資料,將澇災向乾隆帝詳作報告。奏折中列出的州縣計20個,幾乎囊括淮揚徐海各屬地。在奏折的末端,他得出了結論“今年江北淮揚徐海一帶難有偏災……”從該奏折內容,可感知其務實勤奮敬業精神。
高斌辦事認真踏實,作風嚴謹細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曾賜御碑一座。乾隆二十三年(1758),高斌于河工病逝。乾隆帝念他治河有功,追謚“文定”。后人在清江浦運河北岸建“四公祠”,同時祭祀靳輔、齊蘇勒、高斌、嵇曾筠四位河道總督。高斌還同時列入京師(今北京市)賢良祠,《清史稿》有高斌傳。在今淮陰江南河道總督署御碑園中,陳列有康熙、乾隆、道光三代帝君嘉獎河道總督的御筆碑刻計14通,其中以乾隆的御筆最多,在乾隆的御筆碑刻中,又以賜高斌為多,“績奏安瀾”碑于其中最為醒目。
高恒(?—1768),字立齋,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高斌之子,清乾隆時期大臣,慧賢皇貴妃之弟。作為乾隆帝小舅子,乾隆二十二年(1757)任兩淮鹽政。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兩淮鹽政尤拔世向朝廷上奏折,揭發兩淮預提鹽引的弊政。乾隆帝讀過尤拔世的奏折,感覺到此事非同小可,令軍機大臣查檢檔案,隨之一起貪腐大案浮出水面。
柴楨貪腐案:被乾隆帝稱奇的大案
乾隆年間,在兩淮鹽官任上,曾有多名官員因貪腐被查辦,甚至一年內先后查處多起。發生在乾隆五十七年,并被乾隆帝多次稱為“大奇”的柴楨案便是其一。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兩淮鹽政全德參奏鹽運使柴楨“將商人王履泰等應納錢糧在外截留,作為己收,私自移用共二十二萬兩。”[4]案發后,乾隆帝立即派要員進行查處和審理。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初,案發僅兩個月,乾隆帝便下令將鹽運使柴楨及其家人柏順于浙江處決。不久,涉案的浙江巡撫、兼管鹽政福嵩也被正法。另有涉案的浙江司道多人,先后被革職查處。
先前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六日,身為兩淮鹽政的全德按常規上折乾隆帝,為新任兩淮鹽運使的柴楨到任謝恩。從《奏為據情代奏柴楨補授兩淮鹽運使謝恩事》[5]可知,在此前,乾隆帝曾下諭旨:柴楨由貴州舉人揀補知縣,累擢湖南常德府知府、福建興化府知府、浙江鹽道。當年四月十二日,柴楨補授兩淮鹽運使。
是年的十二月初,還是這位代柴楨上折謝恩的全德,卻以一紙《奏為兩淮運使柴楨虧挪庫項請革職等事》參革奏折飛向京城,一件貪腐奇案便浮出了水面。奏折中,全德還請求乾隆帝將柴楨革職拿問,提議將涉案人犯分別交由督、撫處理。
柴楨到任兩淮鹽運使剛半年,就侵挪庫銀二十二萬兩之多,這起驚天大案還牽出背后的人和事,成為案中之案。經審訊,柴楨、其家人柏順及庫官黃德成等涉案人,其案情與供詞基本吻合。僅一個月中,現存相關柴楨案的朱批奏折計有13件之多,如此密集,十分罕見。
十二月初十日,兩江總督書麟、江蘇巡撫奇豐額具奏《奏報到揚州查審參革兩淮運使柴楨供情事》[6],乾隆朱批“實在大奇”四字。與上折同日,兩淮鹽政全德上折《奏報查明兩淮運使柴楨侵挪庫項實數并各商罰繳銀兩情形事》[7],在折中乾隆帝朱批:“此即汝所辦不妥之處,一向不知。”十二月二十一日,貴州巡撫馮光熊《奏報遵旨查抄兩淮運使柴楨原籍財產事》,奏折末端,乾隆帝朱批“大奇之事,實不想到有此也,稍查不到,汝試思之。”
乾隆末年發生在揚州的柴楨侵挪庫項案,已過去二百多年,縱觀此案,遍布整個朝代的官大欺小、依勢盤剝、壓榨下屬等怪象,無疑是貪腐案件頻發的重要誘因。[8]
鹽官張應詔:辭官告老還鄉“無余財”
張應詔(1654—1730),字采臣,號園圖。貴州黎平府開泰先隆里所(今鎖屏縣隆里)人。清康熙辛酉(1681)舉人,初任直隸肅寧縣令。康熙末年,經推薦歷任兩淮都轉鹽運使、巡鹽御史,后因清廉而遭同僚排擠彈劾。雍正初期通過調查為其昭雪,并擢升為鴻臚寺少卿。
鹽稅是清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清朝統治者十分重視對兩淮鹽官的選拔任命。康熙朝末年,有一位以操守聞名而獲舉薦的兩淮鹽官——張應詔。
康熙五十三年(1714),兩淮運使空缺,經尚書趙申喬舉薦,張應詔由潮州知府擢升為兩淮鹽運使。張應詔上任不久,康熙帝便利用親信通過密折了解他。康熙五十六年(1717)二月二十四日,兩淮鹽政李煦在一份奏折中回復康熙帝:“……奴才查得張應詔每歲用商人經費銀數千兩盤纏過日,就其目前而論,操守算好,但才具平常,自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到任以來,不曾做得一件正經事,為人心性執滯,未見明通。”[9]康熙五十八年(1719),李煦的鹽臣任期屆滿。他循例于四月二十六日向皇帝提交了《奏報兩淮鹽務情形并鹽臣張應詔操守如舊事》[10]的奏折,提出“竊兩淮煎鹽灶戶,其每日所煎之數必立法查明,然后不敢賣于私販而盡賣商人,若不查明煎數,則灶戶奸良不一,難得無售私之弊”,有意點出了張的工作失誤“張應詔煎數未查,人事不免缺略”。對于“操守”問題,他不忘在奏折最后說上一句“再訪張應詔之操守依然如舊,合并奏明,伏乞圣鑒。”這一回,康熙帝并未糾結于張應詔的失職,反而表達了對張操守如一的滿意。是年冬,張應詔繼李煦任巡鹽御史。[11]
此后,李煦等貪官并沒有停止對張應詔的造謠與誹謗。康熙六十年(1721)八月初八日,李煦在奏折中說:“奴才近見兩淮官鹽壅滯,私販直達江、廣口岸,以致商皆虧本,公私交困。皆由司鹺者恩威不立,疏通無術,是以怨聲沸騰。蓋張應詔本系迂腐書生,未曾歷練,臨事束手。聞眾商總有公務進見,或議論參差,應詔不能決斷,輒云太爺們,你饒了我罷。兩淮傳為笑談。其舉動如此。至其操守,亦聞不能如前。……”[12]第二年,張應詔終因不與兩江總督常鼐等同流合污而受到誣陷。好在繼任的巡鹽御史魏廷珍據實查案,為其昭雪。
雍正三年(1725),官至鴻臚寺少卿的張應詔告老還鄉。辭官回鄉那天,張應詔備好了十余擔行囊,于是又有小人謠傳:張應詔裝了十幾擔金銀珠寶,滿載回鄉去了。雍正帝非常清楚張應詔的清廉,于是詢問張應詔:“愛卿帶了不少東西回老家吧?”張應詔坦然應答:“確有物資十余擔。”雍正為在朝廷上樹立為官廉潔的榜樣,傳旨讓張把帶回家的行李在朝堂之上當眾打開檢驗。結果行囊中所攜之物,無非“十余擔書籍,幾擔犁耙農具,少許衣物”。雍正帝問,為什么帶這些東西回鄉?張應詔回答:“故里貧瘠,農具不足,故攜而助之。”此語一出,朝堂之上,眾臣無不嘆服。[13]
張應詔在康熙年間因清廉得到重用,康熙末年受到彈劾而不見容于官場;雍正初年得到昭雪,并受到擢升,以清廉之名得到善終。有學者認為,由張應詔的遭遇,可一窺過渡期兩位皇帝的反貪倡廉措施:康熙末年的反貪倡廉存在“雷聲大,雨點小”的境況,而雍正年間的反貪倡廉則是“知行合一”,吏治漸趨清明。[14]
宦海五十載:清朝任時最長的鹽官曾燠
曾燠(1759—1831),字庶蕃,號賓谷。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進士,仕宦50年,歷任戶部主事、兩淮鹽運使、湖南按察使、廣東布政使、貴州巡撫等職。[15]同時,他還是清代中葉著名詩人、駢文名家、書畫家和典籍選刻家,被譽為清代駢文八大家之一。
曾燠自幼聰穎過人,為官很有行政才能。他與淮揚一帶的交集,是因為兩度出任兩淮鹽運使,縱跨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第一次是在乾隆五十七年至嘉慶十二年(1807),一干就是十余年。第二次是道光二年(1822)閏三月,因朝廷感到“兩淮疲憊日甚”,特命為母守孝剛滿服的曾懊以巡撫銜巡視兩淮鹽政,準用二品頂帶。道光六年(1826)召回北京,道光十一年病卒于北京寓所,享年72歲。
曾燠在宦海浮沉達半個世紀,主要業績之一是治理兩淮鹽政。兩淮鹽政受到清朝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曾懊先后兩次赴兩淮任職。《遵旨復奏朱諭密訪曾燠事》[16]是兩江總督孫玉庭上奏給道光帝的密折,全文近千字,大部分內容是上疏者圍繞當時食鹽銷售環節告狀,反對曾燠觀點(“封輪”)和做法。在奏折的末尾,孫玉庭道:“……至曾燠是否另有劣款,現實未有確據,容臣再行密訪,如有所聞,查實即行密奏,斷不敢辜負圣恩,自取罪戾。再,曾燠才具已在圣明洞鑒之中,即其固執臆見一節已非集思廣益之道,難云勝任,但于鹽務尚屬素習,亦知節省浮費,現亦無劣款可指,即猝換一人,亦未必遠勝于伊,可否暫留以俟慎簡得人再行更動之處。出自皇上天恩緣奉密詢,臣不敢稍有隱飾……”
盡管孫玉庭與曾燠意見不合,甚至兩人關系對立,但孫也沒指出曾有什么實質性的問題,倒是提出不必換人,繼續觀察的建議。足以證明,曾燠在為官清正廉潔方面是無懈可擊的。值得一提的是,道光帝在覽奏后的朱批,竟有286字,這在清宮御檔中也是罕見的,足見鹽務在帝君心目中的位置。道光近300字的朱批,除了指出食鹽銷售亂象,還特別強調了灶丁面臨的困境,要求官府關注民生和重視解決社會矛盾。在朱批最后,道光帝提出:“為此,密諭卿知,可將朕朱諭另錄一紙,著韓文琦、曾燠閱看,卿等和衷妥議,相機措置,務要貧丁安所不至事出意外,則善矣。勉之慎之。”
事實上,曾燠到任兩淮鹽政后,立即對鹽政中的一些弊端著手整治,但是,由于鹽政積弊太深,鹽官、鹽商舞弊,積重難返,治理工作遇到多方面的阻力,僅靠曾燠之力已難止頹勢,收效甚微也在預料之中。
曾燠在揚為官之余,倡導風雅,曾辟“題襟館”于邗上,“周植花木為倡和之所”,延納四方名流唱和,與賓從賦詩為樂。他還曾捐款在京師修建南城會館,并經常前往講學。他工詩文,其詩清轉華妙,文擅六朝、初唐之勝,在清代中葉文壇上,以才力富艷負盛名。曾燠為文磊落風雅,體正旨深,又是開清代按地域論詩人新例的詩論家之一。曾燠在任鹽官期間,身體力行,鼎力扶持書院教育。據《揚州畫舫錄》記載:“癸丑,南城曾燠轉運兩淮,親課諸生。又拔取尤者十余人,置于正課之上,名曰上舍,歲加給膏火銀十八兩。”[17]
曾燠還是一位畫家,揚州平山堂后歐陽修祠堂內,正面后墻壁上的石刻像,最初是曾燠按清宮內府藏本臨摹而來,請刻工按照他的畫本鐫刻而成。[18]
曾燠在兩淮鹽運使任上干了16年,加之以巡撫銜(正二品)巡視兩淮鹽政,直到道光六年(1826)四月他被召回京城。由此算來,曾燠任兩淮鹽官計20年,堪稱有清一代在任時間最長,且能全身而退的清廉鹽官。[19]
參考文獻
[1]魏怡勤:《〈清宮揚州御檔〉解讀綜述》,揚州市檔案局、揚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清宮揚州御檔〉解讀文集》,廣陵書社,2015年,第401頁。
[2]魏怡勤:《清代高斌家族為官興衰》,《檔案與建設》2018年第2期,第61頁。
[3]揚州市檔案館、揚州大學編:《清宮揚州御檔續編》第二冊,廣陵書社,2018年,第379頁。
[4]《奏為兩淮運使柴楨虧挪庫項請革職等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揚州市檔案館編:《清宮揚州御檔》第十冊,廣陵書社,2010年,第6829頁。
[5][6][7]《清宮揚州御檔》第十冊,第6764、6834、6736頁。
[8]魏怡勤:《鹽運使柴楨貪腐案考論》,《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第62頁。
[9]《奏為查得張應詔才具操守情形事》,《清宮揚州御檔》第一冊,第250頁。
[10]《清宮揚州御檔》第一冊,第288頁。
[11][13]李全權:《清廉鹽官張應詔》,《檔案與建設》2014第2期,第37、39頁。
[12]《奏為遵旨細細打聽張應詔聲名事》,《清宮揚州御檔》第一冊,第290頁。
[14]柴慧芳:《從張應詔在揚仕途看康雍之交的反腐倡廉》,《〈清宮揚州御檔〉解讀文集》,第80頁。
[15]盧桂平主編:《揚州歷代名人傳》,廣陵書社,2015年,第344頁。
[16]《清宮揚州御檔續編》第四冊,卷首彩頁。
[17](清)李斗著,周光培點校:《揚州畫舫錄》,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第60頁。
[18][19]朱志泊:《清朝任期最長的鹽官曾燠》,《〈清宮揚州御檔〉解讀文集》,第264、2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