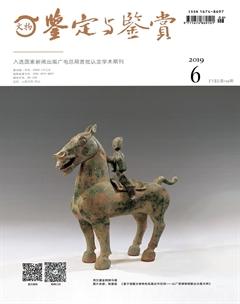河西地區漢晉時期特色人俑形象探析
李婷婷
摘 要:河西地區漢晉時期墓葬出土了數量眾多的人物俑。文章按照造型、姿勢分類,并就具有異域特色的人俑、成批出土且帶有辟邪寓意的劍形人俑及開磚雕之先河的磚雕俑等對河西地區漢晉時期特色人俑進行探析。
關鍵詞:甘肅河西;漢晉;人俑
河西地區地處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深受中原與多民族文化因素的影響,所以這個地區出土的人俑既具有自身的獨特性,又體現出與其他民族交融的特點。因此,對其形象特征的研究有重要意義。
1 特色人俑分類
帶帽俑。高10~30厘米,衣帽輪廓用墨色簡單勾勒,五官也以墨繪,著男裝或女裝,戴冠帽,女俑一般有發髻,比較典型的是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的木俑[1]。
體形瘦長俑。嘉峪關市文殊鎮漢魏墓出土的6件磚雕俑是用磚雕出身體輪廓和頭部,無臂,上身呈長方形,下身呈梯形,部分墨繪五官,高36~38厘米,寬約9.5厘米[2]。
御牛車模型俑。武威旱灘坡東漢墓出土的木俑位于車上,高26厘米,眉目、頭發為墨色勾勒,著長袍,拱手直立。牛旁還站立一俑,高24厘米,雙腿呈行走狀,黑彩繪眉、目、口及頭發[3]。
彩繪五官、衣飾俑。高臺縣漢晉墓葬出土10件,木制,拱手直立,全身涂白,但大部分脫落。其中,6件著長衫,1件上身著短衫、下身著長褲,通體修長,墨繪五官與衣飾,嘴部涂紅;剩余3件體形較寬,衣飾明顯異于其他7件,五官衣飾除以墨繪外,輔之紅彩。
舞俑。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的4件舞俑呈站立狀,木制,梳髻,向左側視。其中1俑舉左臂,右臂屈至胸部,無足,著長衣;另1俑右臂向上斜舉,左臂屈至胸前,短頸,高14.5厘米;其余2俑一個右臂彎曲向后伸,似向左方移動狀,一個左手平舉,右手置于腹部,身體后仰[4]。
牽馬俑。武威雷臺東漢墓出土的儀仗銅俑是國內首次發現的成批銅制車馬俑,馬頸刻銘文,旁立牽馬奴俑1件;有的馬車兩側站立1件或2件奴婢俑。酒泉西溝村出土的2件銅俑是模鑄而成,直立狀,其中1件牽馬俑,一手上舉,另一手自然下垂,頭戴尖頂帽,身穿緊身衣。另1銅俑兩手自然下垂,兩腿微微分開,制作較為粗糙[5]。兩俑高12~22厘米,厚0.3厘米。
劍形木俑。河西地區墓葬共出土劍形木俑50件,其中高臺縣漢晉墓葬中發現45件[6],武威磨咀子漢墓中發現5件[7]。它們的共同特征是用刀削成匕首或刀形,墨繪出人形輪廓。高臺縣劍形木俑普遍長17厘米、寬1.7厘米、厚0.4厘米,武威磨咀子漢墓5件劍形人俑長10~18厘米,兩座墓葬出土劍形木俑最明顯的不同是磨咀子漢墓人俑削刻時突出人物腰線,中間部位比較明顯地可以看出屬于人物腰身,高臺劍形人俑整體形象更像刀形,從頭部向下逐漸變窄,屬于比較特殊的人俑類別。
2 相關特色人俑形象探析
2.1 整體特征
秦兵俑按照真人大小塑造,創造了秦漢時期隨葬人俑的輝煌時期。西漢王朝統一全國之后,統治者厲行節儉,具體表現在隨葬人俑體形縮小,漢景帝陽陵出土人俑通高62厘米[8],河西地區在漢晉時期出土的人俑相對于中原地區來說體形更小,而且除武威雷臺漢墓出土銅俑外,其他出土人俑以木制為主,最高不超過50厘米。學者普遍認為西漢以后在俑的材料選擇上一般為北陶、南木為主,但河西地區這一時期出土陶俑甚少,有明確記載的僅有酒泉、嘉峪關晉墓出土的3件及武威市出土的1件。而木俑數量較多,從造型來看,大部分較為粗糙,但尋常平民隨葬俑不能與王公貴族隨葬人俑同一而論。從總體分析,較小的體形、易取的木料、粗糙的造型,這些特點與河西地區遠離政治中心、生產力低下、經濟發展較為落后不無關系,當然,整體的簡單粗糙并不影響部分人俑的獨特性。
2.2 民族融合特色明顯
高臺縣漢晉墓出土的10件立俑,其中7件出土于同一墓葬,通體涂白色,墨繪頭發、五官與衣飾,普遍著長衫。其中1件上身著交領短衫,下身穿長褲;還有1件女俑梳高髻,整體顏色深于其余幾件,從外貌衣飾推測這可能屬于居住在河西當地漢族人民的形象特征。與這7件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其余3件木人俑了,與前者修長的體形不同,這3件木人俑體形略寬,頭呈方形,鼻子繪制得也比較突出。其中1件戴三尖狀頭飾,雙手拱立,衣紋五官除以墨繪以外,還增添了紅彩,嘴部涂紅。其中2件臉部還用紅彩涂成圓圈,額心施一道紅色。與前7件不同之處還表現在這3件木俑并非身著長衫,而是著寬袖上衣下裳。
出土于新疆哈密焉不拉克村墓地的東周時期的幾件木俑,鼻子與這3件木俑類似,有學者推測“他們是西周時生活在這一帶少數游牧民族的寫照”[9]。這也可間接證明這3件木俑很可能是漢晉時期生活在河西地區的少數民族,與漢民服飾俑出于同一墓葬,證實了河西地區自古以來就居住著眾多少數民族,他們與漢族人民相互融合,有密切的聯系,但也保持著自身獨特的服飾習俗。
2.3 劍形木俑與“木辟邪”
高臺縣出土的45件劍形木俑類型多樣,造型豐富,部分形狀與1975年湖北江陵鳳凰山出土的木片俑和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代人”木牌相同,都是用刀削刻成人形后,表面再用“單線平涂的方法畫出面部和服飾”[10]。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的5件劍形木俑都位于女棺內部左側手部位置,與死者距離如此之近,實屬少見,因此有學者猜測這幾件人俑或許有厭勝之意。
“辟邪”原為古代一種神獸,名為桃拔,又名符拔,似鹿而尾長,兩角,產于西域[11],因為通民間避除邪祟之意,形象常被繪于石刻、木雕上用于趨吉避兇。隨著時代的變遷,后人對其形象進行不斷改變以適應各種場合的需要,運用浪漫主義手法將其帶入自己死后的場所內,同樣也希望達到庇護子孫、驅除邪祟的目的。河西地區漢晉時期出土的劍形木俑形象與“辟邪”有無關系呢?出土的木俑形狀皆削刻成人形,除2件分出雙腿外,其余皆無四肢的明顯分化,面部也較為抽象,不能確定是否是辟邪的形象。但放棄刻畫具體人物形象與分化四肢,將面部抽象處理,可以推測用這些劍形木俑確實是想達到驅邪避災的作用。而且由于武威磨咀子漢墓的5件劍形木俑所放位置的特殊性,因此推斷河西地區出土的50件劍形木俑也具有辟邪的寓意,故將其稱為“木辟邪”。
2.4 開創磚雕俑之先河
嘉峪關市文殊鎮出土的6件磚雕俑是用磚雕出身體輪廓和頭部,無臂,上身呈長方形,下身呈梯形,部分墨繪五官,高36~38厘米,寬約9.5厘米。磚雕藝術興起于唐宋時期,大多作為建筑構件或大門、照壁墻面的裝飾,用于墓葬中也是整塊雕刻成壁畫或者地磚使用。漢代已發展成熟的畫像磚藝術代表了當時磚雕技藝的主要特點。一種是將圖案模印在磚的平面上,施以彩繪,雕刻技法采用淺浮雕、陰刻線,或兩者相結合的技法,使整個畫面顯得生動而富有變化[12];另一種以酒泉、嘉峪關出土的壁畫磚為例,部分素面,部分先以白粉涂底再繪制圖案,都用于裝飾墻面。沒有出現像嘉峪關漢磚雕俑這樣直接以磚為材料,雕刻成人俑形象的。即便磚雕俑的雕刻手法簡單,但從時間界線上來說,河西地區這一時期出現形象具體且用于陪葬的磚雕俑以往未曾發現,因此具有開創性。
綜上所述,河西地區漢晉時期出土了數量眾多、造型各異的人物俑,整體以木俑偏多,銅俑次之,缺少中原地區常見的陶俑。其中,獨具特色的異域俑、形制奇特的劍形俑、形制簡單但材質使用時間較早的磚雕俑等都組成了河西地區漢晉時期隨葬品藝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王輝,趙雪野,李永寧,等.2003年甘肅武威磨咀子墓地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2(5).
[2]俞春榮,王春梅.甘肅嘉峪關市文殊鎮漢魏墓的發掘[J].考古,2014(9).
[3]黨壽山.甘肅省武威縣旱灘坡東漢墓發現古紙[J].文物,1977(1).
[4]黨國棟.武威縣磨咀子古墓清理紀要[J].文物參考資料,1958(11).
[5]馬建華,趙吳成.甘肅酒泉西溝村魏晉墓發掘報告[J].文物,1996(7).
[6]趙吳成,周廣濟.甘肅省高臺縣漢晉墓葬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05(5).
[7]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磨咀子三座漢墓發掘報告[J].文物,1972(12).
[8]王學理,王保平.漢景帝陽陵南區從葬坑發掘第二號簡報[J].文物,1994(4).
[9]阮榮春.美術考古一萬年[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8.
[10]紀南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整理組.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簡報[J].文物,1975(9).
[11]王連海.中華傳統吉祥圖案知識全集[M].北京:氣象出版社,2015.
[12]毛曉青.中國傳統磚雕[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