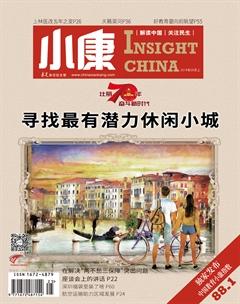在太虛之境攬鏡自照
沙子
我看到泳池下面,姑娘穿著衣服走來走去拍照;我看到好多個自我,在穿衣鏡里無限地重現;我看到一座房子被連根拔起;我看到電梯門開開再合上,每次開門都會有不同的人群乘坐;我看到不少人,在一座三層樓的外立面上飛檐走壁、各種冒險;我看到層層玻璃,重疊排列后正面顯現出惟妙惟肖的白色浮云……
這些“看到”統統發生在 “雷安德羅·埃利希(Leandro Erlich):太虛之境”展覽現場,若將英文展覽名 “The Confines of the Great Void”進行直譯,便是“無邊虛幻的邊界”。來自阿根廷的年輕藝術家把自己25年來創作的現代藝術搬到了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內部三層空間,同時還在館外展出了《游泳館》和《連根拔起的房子》兩個作品。這個展覽迅速躥紅,人們擁擠在《游泳池》《雨》《建筑》《美發沙龍》《試衣間》《教室》等作品前盡情互動、努力探索。
名為《建筑》的作品其實躺在地板上。當人們躺在地板上的建筑物表面上時,會看到自己在鏡子里有了各種奇異的行為:掛在窄窄的防火梯子上,或者坐在窗戶邊沿上,其他人坐在巨大的商店招牌上、踩在空調機上,各種頹廢冒險自殺狀態。《美發沙龍》是兩個一模一樣的美發室,很多鏡子正在反射對面的世界,你會在鏡子中看到自己,而有些窗口沒有鏡子,觀眾會錯愕地發現本該出現自己的鏡像卻出現了別人。
現代藝術已經到了這個程度——沒有觀眾就沒有藝術。
日本藝術家岡本太郎在《今日的藝術》中提出,“藝術不是聽來的,也不能靠別人教,只能靠自己去摸索發現,要把它看成與自己相關的一部分,這樣就能自然而然地直接與藝術產生聯系和碰撞。”這或許也正是雷安德羅·埃利希進行藝術創作時候的初衷。比如欣賞展廳第二層的《迷失花園》,如果沒有觀眾,作品就不算成型。當觀眾站在一個窗口之前,一座有著紅色窗戶的中國典型四合庭院便會躍入眼簾,院子里綠色植物茂盛蔥蘢,同時觀眾可能在四合院其他三面墻上的窗戶中看到自己的形象。等你離開這個觀賞角度,繞到作品背后,卻看到一堵嚴嚴實實從上到下的三角形白墻。所謂的四合庭院是沒有的,這個作品用鏡子和攝像頭讓你看到的其實并不是真的。驚訝之余,展覽墻上的提示語或許能引起你的思考——“我感興趣的是,在視覺藝術中,時間不屬于作品,而是屬于觀者”。
現代藝術已經到了這個程度——沒有觀眾就沒有藝術。藝術創作者用空間形象進行了藝術表達,但是,他們還需要另一個因素促成這個表達的完成和傳播,那就是到達現場的觀眾。作家博爾赫斯在短篇小說《小徑交叉的花園》中探討了時間為何物,探討時間有無數的系列,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的網。由互相靠攏、分歧、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絡里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 “在大部分時間里,我們并不存在;在某些時間,有你而沒有我;在另一些時間,有我而沒有你;在有些時間,你我都存在。”這位阿根廷作家寫道。
走出“太虛之境”后,展覽中的所有景象卻仍在我的腦海中不停地閃現,一個個好奇接踵而至:為什么不動的窗戶帶給我們無窮無盡的風景?為什么運動的電梯帶給我們窒息般的封閉感覺?為什么一個個普通鏡子的疊加能讓你成為無窮盡的你?博爾赫斯和雷安德羅·埃利希都給了答案,時間是交錯的背離的平行的分歧的,我們都通過時間見證藝術、發現自我、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