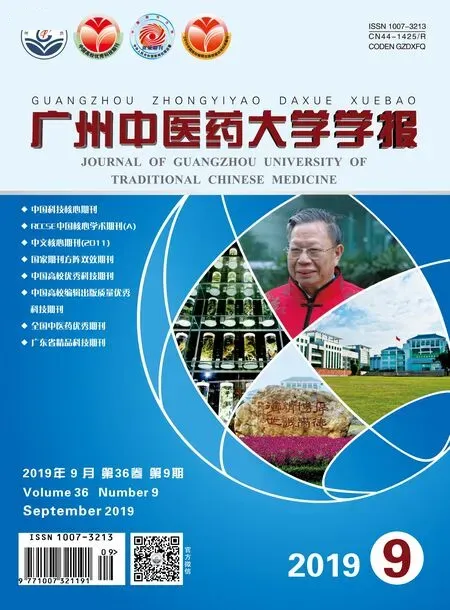基于從脾論治理論探討針刺對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臨床療效
丁鸝瑤, 于海波, 劉永鋒, 陳伊镕, 黃杏賢, 胡梨雨, 蘭凱
(1.廣州中醫藥大學第四臨床醫學院,廣東深圳 518000;2.深圳市中醫院,廣東深圳 518000)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iabetic retinopathy,DR)作為糖尿病微血管病變嚴重的并發癥之一,是成人致盲的一個重要原因,臨床上,將沒有視網膜新生血管形成的DR稱為非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NPDR),將存在視網膜新生血管形成的DR稱為增殖性糖尿病視網膜病變(PDR)。因多數糖尿病患者無定期進行眼底檢查的觀念,且DR早期往往無明顯的視力下降癥狀,故常常未能及時就診,等發展到增殖期時,患者已出現視力改變,甚則玻璃體積血或視網膜脫落,常需手術治療,難度大費用高,且預后較差,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也給社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1]。筆者采用調理脾胃針刺法聯合眼周針刺法治療NPDR,以期為探索DR的有效治療方法提供參考依據。現將研究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及分組
選取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在深圳市中醫院內分泌科及針灸科門診就診的DR患者,共68例。按照隨機數字表將患者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各34例。
1.2 診斷標準
(1)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1999年的糖尿病診斷標準[2],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可診斷為糖尿病:①具有糖尿病癥狀,空腹血糖≥7.0 mmol/L,具有糖尿病癥狀,或任何時候血糖≥11.1 mmol/L,或糖耐量試驗中服糖后2 h血糖(OGTT2h)≥11.1 mmol/L;②無糖尿病癥狀,除空腹血糖≥7.0 mmol/L或OGTT2h血糖≥11.1 mmol/L或任何時候血糖≥11.1 mmol/L外,還需一次空腹血糖≥7.0 mmol/L或血糖OGTT2h血糖≥11.1 mmol/L。(2)DR診斷標準按照1985年全國眼科學術會議通過的診斷標準[3]。
1.3 納入標準
①符合糖尿病診斷,且經內分泌科診斷為Ⅱ型糖尿病,血糖獲得有效控制者;②符合糖尿病視網膜病變Ⅰ至Ⅲ期者;③年齡在30~65歲者;④簽署知情同意書者。
1.4 排除標準
①不符合上述標準;②合并有心血管、肺、肝、腎和造血系統等嚴重疾病者;③妊娠或哺乳期婦女;④糖尿病腎病發生腎衰氮質血癥期、尿毒癥期者;⑤其他眼部疾病妨礙眼底觀察者,如青光眼、白內障、葡萄膜炎、視網膜脫離、視神經疾病。
1.5 治療方法
1.5.1 常規治療 2組均使用常規西藥如降壓藥、降糖藥、調脂藥等,降壓藥用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ACEI)、鈣通道阻滯劑(CCB)和α-受體阻滯劑(減少對代謝功能影響),有需要時遵醫囑隨時調整用藥,確保患者血壓、血糖等保持平穩,避免不良事件的發生。
1.5.2 對照組 采用眼周針刺法。針刺取穴:睛明、攢竹、承泣、球后、瞳子髎、肝俞、腎俞。針刺操作方法:取環球牌針灸針,眼周用0.35 mm×25 mm規格,余穴位采用0.35 mm×40 mm規格,穴位常規皮膚消毒后,垂直進針,得氣即止,眼周穴位得氣后不行針。所有穴位均留針30 min后取針。
1.5.3 治療組 治療組采用調理脾胃針刺法聯合眼周針刺法。調理脾胃針刺法:針刺取穴脾俞、足三里、中脘、陰陵泉、三陰交。針刺操作方法及眼周針刺法:同對照組。
1.5.4 療程 2組均每周治療3次,周末休息2 d,4周為1個療程,共治療3個療程。
1.6 觀察指標
2組患者在治療前后均進行如下檢測:(1)視網膜圖像采集:采用Canon CR-2 AF Non-Myd Retinal Camera采集眼底圖像。(2)視力檢測:視力檢查采用國際標準視力表(1分制),不及0.1者,每進0.02計為一排。(3)理化檢查:糖化血紅蛋白。
1.7 療效判定標準
結合《中藥新藥治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的臨床研究指導原則》(2002年版)中關于DR的療效判定標準制訂眼底各項指標療效評判標準:(1)視網膜微血管瘤數。顯效:由3+減少到1+、或由2+減少到消失;有效:3+減少到2+、或由2+減少到1+、或由1+減少到消失;無效:以上指標未達到要求或眼底出現新生微血管瘤。(2)眼底出血量。顯效:由3+減少到消失;有效:由3+減少到1+、或由2+減少到消失;無效:以上指標未達到要求或眼底出血量增多。(3)眼底滲出量。顯效:由3+減少到1+、或由2+減少到消失;有效:3+減少到2+、或由2+減少到1+、或由1+減少到消失;無效:以上指標未達到要求或眼底滲出量增多。其中,1+表示較少,易數;2+表示較多,不易數;3+表示微血管瘤很多,不可數,出血及滲出量多,融合成片。
1.8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25.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的統計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內比較采用t檢驗,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率或構成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Fisher確切概率法。以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2組患者基線資料比較
觀察組33例患者中,男27例,女6例;平均年齡(57.82±10.16)歲;平均病程(7.18±2.67)年;平均體質量(66.94±8.37)kg;平均身高(169.24±6.21)cm。對照組32例患者中,男26例,女6例;平均年齡(57.44±11.33)歲;平均病程(6.91±2.77)年;平均體質量(66.66± 11.99)kg;平均身高(169.41±6.46)cm。2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病程等一般情況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2組患者的基線特征基本一致,具有可比性。
2.2 2組患者失訪情況比較
研究過程中,觀察組失訪1例,對照組失訪2例。最終觀察組33例、對照組32例納入療效統計。
2.3 2組患者治療前后糖化血紅蛋白及視力水平比較
表1結果顯示:治療前,2組患者的糖化血紅蛋白及視力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2組患者的糖化血紅蛋白及視力水平均較治療前明顯改善(P<0.05),且觀察組的改善作用優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2組患者治療前后糖化血紅蛋白及視力水平比較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levels of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nd visual acuity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x±s)
2.4 2組患者眼底微血管瘤臨床療效比較
表2結果顯示:治療后,觀察組和對照組治療眼底微血管瘤總有效率分別為3.03%和3.12%,2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2組治療方法對患者眼底微血管瘤的臨床療效均無明顯改善。

表2 2組患者眼底微血管瘤臨床療效比較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icacy for fundus microangioma in the two groups n(p/%)
2.5 2組患者眼底出血量臨床療效比較
表3結果顯示:觀察組和對照組治療眼底出血總有效率分別為45.45%和18.75%。觀察組療效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3 2組患者眼底出血量療效比較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icacy forfundus hemorrhage in the two groups n(p/%)
2.6 2組患者眼底滲出量臨床療效比較
表4結果顯示:觀察組和對照組治療眼底滲出總有效率分別為60.61%和34.38%。觀察組療效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4 2組患者眼底滲出量療效比較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icacy forfundus exudation in the two groups n(p/%)
3 討論
DR屬中醫“內障眼病”范疇,現代中醫眼科學普遍認為DR的中醫病名為“消渴目病”,其并發于消渴,病因病機與消渴密切相關。治病求本,從脾論治是從其氣血生化的根本出發。張錫純先生曾提到“消渴一證,古有上中下之分,謂其證皆起于中焦而極于上下”,《劉河間先生三消論》提到“今消渴者,脾胃極虛”,此皆揭示了脾胃虛弱是消渴發生的內在原因。脾為后天之本,善化水谷,脾臟虛弱則無以化生氣血,無以輸布精微物質營養全身,久之津液干涸,燥熱內生,發為此病。如不能散精于肺,則呈現為肺燥,表現為口渴多飲;不能運化水谷,則積而化熱,消灼胃陰,出現多食善饑;脾虛致氣血不得充養四肢肌肉雖多食反消瘦乏力;津液輸布失常,則小便多而渾濁[4]。李東垣《蘭室秘藏·諸脈者皆屬于目論》云:“夫五臟六腑之精氣,皆秉受于脾,上貫于目。脾者,諸陰之首也;目者,血脈之宗也。故脾虛則五臟之精氣皆失所司,不能歸明于目矣”,指出醫者在治療眼病的同時必須顧護脾胃,否則就是妄治。由于飲食失常,或先天因素,憂思多慮,或眠少煩多,損傷脾胃,使脾胃運化功能失常阻礙氣機,脾氣虛弱,血失統攝,血行脈外出現眼底出血,氣虛血滯可形成視網膜靜脈的阻塞,《素問·至真要大論》提到若脾不能主導運化功能,致水濕內停,可呈現出各種浮腫、水濕內聚的征象,在眼底可表現為滲出物,黃斑區水腫等,中氣不足,清陽不升而濁陰不降,甚則可致視網膜脫離。因此,中醫治療消渴目病應當從脾論治,此為從本源出發。
DR確切的病因病理并不明確,目前有以下幾個方面:①多元醇通路激活;②蛋白激酶C激活;③晚期糖基化產物堆積;④持續高血糖狀態;⑤細胞因子的作用。西醫的治療方法主要有視網膜激光光凝術、抗VEGF藥物、類固醇治療、玻璃體切割術等,主要針對PDR,且多種治療方法存在的利弊也需要權衡。所以,需要對DR的發病機制不斷追尋探究,尋找更加適合有效、副作用低的治療方法,尤其是尋找NPDR的有效治療方法,提高對早期DR的診斷和檢查水平的同時進行早期治療,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護視力[5]。
針刺治療消渴目病,療效確切,已被反復證明。楊博等[6]認為針刺可以抑制細胞因子的釋放,從而間接抑制血栓的形成,并使用針灸對10例糖尿病視網膜患者的眼周局部的穴位進行強刺激,結果顯示10例全部有效,7例痊愈。張虹等[7]研究發現,針刺可以改善糖尿病大鼠的異常視覺電生理。李石良等[8]發現針刺對糖尿病大鼠的毛細血管管徑、微血管瘤等具有明顯的改善作用。付明舉等[8]通過對23例NPDR及19例PDR患者進行研究,發現針刺可以改善2組患者的視網膜中央動脈和顳側睫狀后動脈的血流速度,即改善眼周局部的血液循環狀況。蔡春梅等[10]分別采用針刺和胰島素治療DR大鼠,發現相比較于胰島素,針刺可以更加有效地抑制細胞因子的合成與釋放。王德全等[11]研究發現,針刺組糖尿病大鼠的血清脂質過氧化物和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低于造模組,且紅細胞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高于造模組,說明針刺可以清除自由基從而提高抗氧化能力。劉丹等[12]研究發現,針刺可以抑制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受體mRNA的表達。
晁俊等[13]闡述“脾胰同源”的理論,認為正是由于“脾不散精”,故水谷精微難以輸布,聚成“糖濁”,體現為患者血糖水平的不斷升高,故治療應健脾益氣,使機體“糖濁”漸化,本研究證實了從脾論治可使DR患者的糖化血紅蛋白顯著降低。《靈樞·大惑論》云“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精”,脾屬土臟,承載萬物,可使水谷得以轉化而成氣血。選用脾俞、足三里、中脘可補益中氣,使脾胃健運,氣血得生,濡養眼目,此外脾氣充足則統攝有力,血不至溢出于脈外,脈道通利則癖血消除,睛明、攢竹、承泣、球后、瞳子髎為眼周選穴,可疏通眼周局部血絡,陰陵泉、三陰交可補益陰液,隨著消渴病情的進展,治療上需顧護肝腎,以肝俞、腎俞滋補肝腎,養血填精。諸穴合用,共奏健脾益氣、活血通絡之功。眼周針治療DR療效顯著,是臨床上常用的治療方法[14],針刺眼周穴位可以有效改善患者視力及視野的損害,促進視網膜出血的吸收。
本研究基于脾虛是DR發生的基礎,采用調理脾胃針刺法聯合眼周針法治療DR,結果顯示該法能夠改善患者眼底情況,提高患者視力水平,并且能夠降低其糖化血紅蛋白,值得大力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