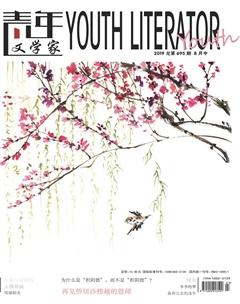雪落陽關
王國良
雪,在北方是極其平常之事,而對于敦煌而言,那是件可遇不可求的事。
1月20日,大寒,老人們常說:“大寒小寒,無風自寒。”今天有風,寒冷透過掛滿霜花的窗戶,和濃墨低沉的天色,悄然襲來,碾壓著我晨起的心情,心中隱約盼望著一場雪,這念想如濃墨入水,濃濃淡淡地在腦海里逸散開來。
今天,受友人之托,去車站送他。一路上,友妻不停地叮囑道,胃不好,少喝酒,給家里多來電話……友耐心地點著頭,不一會兒,我們來到一家商鋪門口,自從上格爾木的班車停發以后,上格爾木需乘坐敦煌汽車站發出的車,班車會在這家商鋪門口中轉。
等車的人,擁擠在商鋪前,站立在門口的幾個年青人,有說有笑,呼出的白氣就像吐出的白煙,在凜冽如刀的風中被割裂吹散,搓著手跺著腳,時不時斜著頭看著路口。
片刻,友妻的臉被凍的面紅耳赤像掛在寒風里的冬柿,友人心疼地看著妻子,把手搓熱,輕輕的放在她的臉上。
“熱了沒有?”
“嗯,熱了。”
友妻遞來溫暖的目光。
“要不,你們回吧”
“我要看著你上車”她堅決地答道。
“吱”商鋪的門開了,有人從商鋪出來,店鋪里有了空位!朋友就順勢把妻推進店里,門關上了。友妻在里面說著什么,聽不清,估計是讓他和我也進去,店里比肩接踵,人滿為患,我們只好作罷,友人微笑著對著玻璃“哈”了一口氣,在玻璃上認真地畫了一個桃心,友妻會意一笑,也“哈”一口氣,在桃心兩邊各寫了一個“I”和“Y”,友笑了,紅彤彤的臉上隨之綻開了一朵鮮艷的玫瑰,此刻,寒風中也增添了甜蜜和浪漫的味道。
車來了,友人要走了,友妻遞過包,同時也把不舍的心遞了過來,淚光晶瑩,友,順勢把妻攬入懷中,友妻哭了,他在耳邊耳語了幾句,友妻又破涕而笑,車緩緩前行,離別的情愫如同天上鉛云瞬間變濃了,友人這時在車窗“哈”一口氣畫了一個桃心,用嘴作了一個吹的動作,友妻看著,揮著手,會意的笑了,淚水已奪眶而出。
車離開七里鎮已經半小時了,估計過南湖路口了吧,要在古代,他算是出“關”了(陽關在南湖近內),我自語道,腦海里也隨之閃現出王維的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的詩,腦海中也影現出一個場景……
公元756年春,清晨,在咸陽,煙柳樹下一個客棧里,兩鬢斑白的王維,起身端酒,動情的沉吟道:“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杯濃郁的感情瓊漿在王維的手中微微顫抖著,元二接過酒,一飲而盡,看著王維,兩眼濕潤了。此刻,王維有很多的話要說,但時逢安史之亂,人心惶惶,命運難測,在這種復雜的心情之下,竟不知從何說起,把這一切都置于酒中,讓酒在離別的愁腸中,化作肺腑之言,溫暖、安慰友人的心吧。王維揮手告別好友,看著一騎黃塵的背影,向西而去,隨之,心中的離舍之情,發酵蔓延,壓在心口,無法消散。
陽關,佇立在午后的寒風中,側著身,站在不遠的地方,迎來送往,它已經看慣太多的離別。淚眼茫茫,它也吞咽太多的感傷。
17時許,雪,從天而降,紛紛揚揚、飄飄灑灑,那一片片雪花在空中舞動著各種姿勢,或跳躍、或盤旋、或飛翔,擁擠著鋪落在地上。不多時,整個敦煌都套上了靚麗的銀裝,干涸的土地變得潔白濕潤了,干枯的樹枝也好像被喚醒,輕語著,期盼著春天的到來。敦煌,終于下雪了。
此時,陽關內外,白雪皚皚,四野茫茫。一千年多前,也是在這個大雪紛飛日子里,一支駝隊,自西向東而來,在悠揚的駝鈴聲中,他們跋涉萬里,向陽關走來,雪花飄落在一個中年和尚伸出的手掌上,化作幾滴晶瑩的水珠,他把這些水珠小心翼翼的捧起,放在嘴邊,吮吸著,掩面的手掌沒有阻擋住激動的淚水,奪眶涌出,他,就是貞觀627年西去天竺取經的玄奘,17年的離別,就是17年的思鄉,歷經千辛萬苦,他,取經回來了,他又一次踏上了大唐的國土,感受到雪水的甘甜,感受到了故土的溫暖。他入“關”了,他回家了。陽關如故,他已兩鬢斑白,下馬,手捧故土,淚水悄然而下,他哭了。
《送元二使安西》在晚唐被大眾普遍吟詠之后,“陽關”一詞就成為離別的代稱,“陽關三疊”也成為了無數文人騷客筆下的詩卷,一場場肝腸寸斷的離別,在文人的筆下就這樣洋洋灑灑地彌漫了上千年。在古代,交通是人們出行最大的局限,一次離別就意味著數月或數年后才能相見,握手道別,再見,遙遙無期。所以,離別之情才顯的彌足珍貴。如今,坎坷變通途,千里路程一日還,離別的話語在嘴邊還帶著溫度,當日,故人再次重逢,如今的“陽關”,再不是人們情感的盡頭,而是人們旅途上一個過往的坐標。
春夏秋冬,朝代更替,陽關在絲綢之路上已經有千年的歷史,如今的陽關就像一位垂暮的老者,見證著人們的聚散離別,沉淀著過往行人的淚水與歡歌,如今的“陽關三疊”,不再是凄涼加離別的濃飲,而是在檀香裊裊、暖茶馥郁、燈光優雅的茶座里,人們托腮傾聽的一首古曲。
古人已逝,陽關依舊。那穿梭在絲綢古道上的駝鈴聲依舊在漫漫黃沙的腹地縈繞盤旋,獨自承載著歲月的云煙與離別。
雪,在陽關,如今不再是凄涼孤寂,而是一種獨特的風景。
雪,落陽關,給這里的人們增添了久違的浪漫,少了一種心中的離別的感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