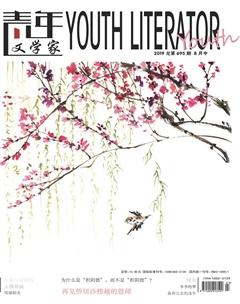王夫之“情景論”探微
郭辰
摘? 要: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情景論”始自先秦,從宋代到明代也是許多批評家關注的中心。王夫之是中國古典“情景論”的集大成者,有著豐富的詩學情論和景論思想,在論述情景關系上始終把持著情景共生的維度,并在此維度下探討了藝術構思中“景生情”、“情生景”直至達到“妙合無垠”的狀態,對王國維的“意境說”產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響,將古代詩歌批評中的情景論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關鍵詞:王夫之;情;景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3-0-02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世稱“船山先生”。他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史學家,又是一位在中國古代文論史上具有承前啟后并做出重要貢獻的文論家。其詩歌理論著作有《姜齋詩話》、《古詩評選》、《唐詩評選》等,“情景論”是其詩歌理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一、情景范疇論
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說:“文學中有二原質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為主,后者則吾人對此種事實之精神態度也。”無論在詩的創作亦還是鑒賞中,情與景都是古代抒情詩歌存在的原動力,情景論則是詩學理論探討的核心。
情感是詩歌的生命,古今中外的詩人、批評家都對此有著共同的認識。魏晉時期,陸機在《文賦》中說:“詩緣情而綺靡。”現代學者、詩人郭沫若說:“詩的本質專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詩形,也不失其為詩。”英國詩人華茲華斯在《抒情歌謠集·序言》中說:“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王夫之非常重視情感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認為詩歌的基本特點就是表達情感——“詩以道情”、“詩達情”,也認為情也是與世間萬物得以產生聯系的關鍵所在——“君子之心,有與天地同情者,有與禽魚草木同情者。”而他對“情”的界定則更多地體現在對“興觀群怨”四情的闡釋之中。
《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把詩作為一種教化民眾的工具,之后的儒生和理學家們也大都沿襲這一傳統,更多的是政治、倫理層面,對詩的文學審美性并無過多的涉及,而王夫之則對“興觀群怨”進行了全新的闡發,《姜齋詩話》云: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盡矣,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讀《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于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于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由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于有詩。
在這一論述中,王夫之打破了興觀群怨四者的界限,將四者均視為相輔相成、彼此貫通的“情”的統一體,使“情”更好地傳達。同時,將四者改為“四情”也突破了詩只存有倫理教化之用的界限,賦予詩更多的審美特質,將詩的社會功用與審美功用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一方面站在詩歌欣賞的角度,將詩之于讀者的地位與作用予以概括,經作者之手的作品——詩呈現在讀者面前,并非只允許有一種正解,讀者并非只能有一種感悟,而是各種情感或共鳴隨讀者自身實際而自由展開,給予了讀者充分的想象與聯想空間;另一方面則站在了作家創作的角度,作家情感由“興觀群怨”四者隨機結合后,任意生發,不受界限。但是不受界限并非沒有底線。關于“情”,王夫之也在《詩廣傳》里做了明確的界定:“情者,陰陽之幾也。”《周易·系辭傳下》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又云;“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兇之先見者也。”“幾”就是事物變化發展的微小征兆,所以理解王夫之的此番話就是:微妙的情是體現不可聞見的天道的。另外,王夫之還在《詩廣傳》中強調“發乎情,止乎理。”可見王夫之對情的最高價值也有著界定,即情不可違背天理,也不能過度泛濫。
王夫之《詩廣傳》云:“故外有其物,內可有情矣;內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物”就是情景論中的“景”,在此言論中,他將情與景綁在了一起,情感的產生必定有景的作用。對于“景”,王夫之做了很多的分類,比如將“景”分為“內景”與“外景”:“是故心者即目之內景。”“內景”即眼睛看到后呈現于心中的景象,那么就可以將“外景”認為是只進入到人的眼睛之中而尚未走進心中的景象,王夫之說的“煙云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賬”即屬于此類外景,而他又說此類景“寓意則靈”即言“外景”經過心靈之“寓意”成為“內景”,才可充滿靈氣,成為文學創作中必要的“景”。
王夫之還將“景”分為“景之景”、“事之景”、“情之景”,評曹植《當來日大難》一詩言:“于景得景易,于事得景難,于情得景尤難。‘游馬后來,轅車解輪,事之景也。‘今日同堂,出門異鄉,情之景也。”“于景得景”即“景之景”,相當于上面所說的進入人眼之中的外部景色,“事之景”是故事發生之背景,“情之景”即融合了人的情感狀態的一種景,類似于上面所說的“內景”。毫無疑問,王夫之最欣賞的是“情中景”,這在情景關系論中會更多詳述,此處不再贅述。
從景的規模看,王夫之將“景”又劃分為“大景”和“小景”:
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葉開時任好風”,“花覆千官疏景移”及“風正一帆懸”,“青靄入看無”,皆以小景傳大景之神。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張皇使大,反令落拓不親。
“大景”指的是規模宏大壯闊的景,“小景”指的是場面偏小而細膩的景,王夫之不喜直接繪出的大景,大景情感傳遞不夠,更會稍顯距離感,,反而欣賞“以小景傳大景之神”的景,于細微之景緩緩入手,轉而駛入規模宏大磅礴的景,更能凸顯景之神,情之動。而這些細微之景的把握需要詩人在心中不斷醞釀,不斷升華,那么人的悟性與感受總要不可避免地摻雜其中,這就像玩一個拼圖游戲,切割片數多的圖片總是要更費功夫,更需要去用些心思進去。
由上可知,王夫之欣賞的是“內景”、“情中景”、“以小景傳大景之景”,相同的是這些景無一不摻雜人的情感,可見在區分過程中,他從未把情與景割裂開來,而是將情動于中之“景”與其他“單薄”之“景”做出劃分與對比,這也更印證了王夫之的“情景論”是始終在情景共生的維度下展開的。
二、情景關系論
對于情景關系的研究,古往今來有很多大家提出了自己的論斷,但王夫之在情景關系這個領域成就最大,《姜齋詩話》云:
關情者景,自與情相為珀介也。情景雖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樂之融,榮悴之迎,互藏其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樂,用之無窮,流而不滯,窮且滯者不知爾。
他從整體的心物觀出發,主張情景相生,情景“互藏其宅”,推崇通首渾成、情景妙和的詩境。“在心”之情和“在物”之景一旦經詩人藝術構思并書寫成篇后,即在詩中自相融匯,原來的區別以及界限業已不復存在,情景此時已成為水乳交融的新整體向人們呈現著新的意蘊,這就徹底摒棄了那種在詩歌創作與批評中割裂情景的傾向。在情景“互藏其宅”的前提下,王夫之進一步將情景關系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景中情
“景中情者,如‘長安一片月,自然是孤凄憶遠之情;‘影靜千宮里自然是喜達行在之情。”王夫之以唐代大詩人李白《子夜吳歌·秋歌》為例,認為該詩以思婦的口吻抒發對遠征邊陲之夫的懷念,雖未直寫愛情,卻字字滲透著真實情意;雖沒有高談時局,卻又未離時局。“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寫出了月色如銀的京城,表面上一片平靜,而在這樣的布景下,搗衣聲卻蘊含著千家萬戶的痛苦,讀來讓人怦然心動。全詩就像一部電影,鏡頭緩緩拉開,景賦予了畫面感,更有無限“畫外音”,在光與聲中賦予了無數思婦的濃濃“玉關情”,此情之濃,不可遏制。王夫之曾言“不能作景語,又何能作情語邪?”可見,景在傳達情的過程中的分量之重。黑格爾也曾說過:“在藝術里,感性的東西是經過心靈化了,而心靈的東西也借感性化而顯現出來。”兩者都認為情感的觸發源于外物,不斷沉淀之后得以心靈化,并且再靠心靈化了的外物去顯現。在中國詩歌中,有些外物還固定地與某種情感相勾連,如“睹月思人”“楊柳送別”等,這種含蓄美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化。
(二)情中景
王夫之認為,與“景中情”相比,“情中景”尤難曲寫。“情中景”以詩人情感為出發點,對于外部的“景”有外射性的作用,使目睹到的景“皆著我之色彩”,景的呈現完全憑借詩人情感的狀態,人或喜或悲,景亦是。比如李白《早發白帝城》“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回蕩在山澗空谷的猿聲一般會給人帶來凄寒蕭索之感,酈道元在《三峽》中即言:“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反觀李白,聽到猿聲不僅凄寒之意沒有來襲,反而把它當作自己回江陵途中的協奏曲,連輕舟都使自己飛快地越過萬重山,為什么同樣的猿聲給人的感受如此不同?是因李白本來是要被貶夜郎,途中收到赦免消息,驚喜交加,于是所聞所見的一切都沾染上了“喜”的色彩,倘若詩人仍在被貶途中,想必其詩所涌之“情”便會奠定悲的基調,“輕舟”也會變作“重舟”,“猿聲”更會使詩人不寒而栗。可見,“情中景”的書寫需要詩人強烈的情感,并需要找到與這種情感合適的對應物,以此作為宣泄口,來滿足詩人訴諸于情的目的。
(三)情景妙合無垠
王夫之認為“景中情”和“情中景”由于尚能分辨景與情,有人工作用之跡,只能歸于“巧者”這一層次,他最為欣賞的是“神于詩者,妙合無垠”這一至神境界,狀景易,狀情難,詩人應當創造情景互出、景中生情,情中生景的意境:
情景相入,涯際不分,振往古,盡來今。
情景互出,更不分疆界。
可以看出,王夫之認為好詩的情與景要恰到好處地融匯在一起,分不出哪句就情,哪句依景,而詩人也只需要自然地書寫出即景所生的情,這樣的作品才無任何斧鑿之跡。因此他推崇的幾乎都是具有清純、自然、平淡風格的詩人,如謝靈運和陶淵明,這種境界一般詩人難以企及:
“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相融浹,一出語時,即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束而與景相迎者也。“日暮天無云,春風散微和”,想見陶令當時胸次,豈夾雜鉛汞人能作詞語?
他強調很多“至神之境”的詩句都是心目合一,出口即成,不能也不用去反復想如何去契合客觀與主觀之境,當然這更與詩人的胸懷品性息息相關,先要是自己內心澄明,才能做出“神語”。與之相對應,王夫之不滿以孟郊、賈島等為代表的“苦吟派”,例如賈島對“僧敲月下親門”的“敲”字反復拿捏,王夫之認為這樣刻意地去遣詞造句,即使確定下來足夠去形容該動作的字,也只是全憑借主觀之情,早已遠離了本來面目。最妙的就是即景會心,如王維的“長河落日圓”,只需要將所目之景呈現到紙上,而用不得去想哪個更恰當,如此方能將原始而又動人的情景完美地呈現出來,才能將情與景暗合得自然靈妙。
參考文獻:
[1]王夫之著,戴鴻森箋注.《姜齋詩話》箋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王夫之著,王孝魚點校.詩廣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9.
[3]崔海峰.王夫之詩學思想論稿[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