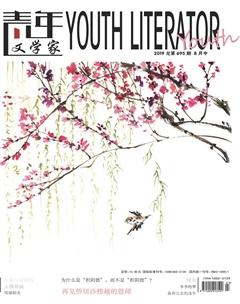東野圭吾小說《白夜行》“惡女”形象研究
許雅奇
摘? 要:日本作家東野圭吾在其作品中塑造的“惡女”形象紛繁眾多,且“惡女”們大都在偽善的外表掩飾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其中《白夜行》中的唐澤雪穗是其筆下“惡女”形象的典型代表,但從另一角度出發,拋開“惡女”殘忍的作惡手段,深究惡之根源,又讓人唏噓不已。
關鍵詞:東野圭吾;白夜行;惡女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3--01
東野圭吾,作為文壇上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作品大多以科學知識作為框架,呈現出一種較為濃厚的科學氛圍,這也恰恰是其小說具有較強邏輯推理性,能夠引人入勝的原因所在。
一、“惡女”形象的形成原因
唐澤雪穗算得上東野圭吾筆下比較典型的“惡女”形象代表,她在自身成長的過程中,由被動作惡到主動作惡,最終成長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惡女”。
(一)“惡女”形成之經濟背景
文學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的語言和文學上的傳統,而這個傳統又要受到總的文化環境的巨大影響。小說開頭的案發地點--廢棄的大樓,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當時發生在日本的泡沫經濟。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每況日下,國內的貧富差異愈加明顯,道德危機等問題逐漸凸顯,嚴重的社會矛盾引發了一系列社會丑相,如婚外情、戀童癖等。因而,文中出現西本文代逼迫女兒賣淫、桐原洋介猥褻幼女這樣的情節就不足為奇了。唐澤雪穗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逐漸走上“惡女”之路,《白夜行》中令人驚愕和憤恨的悲劇也就理所當然地呈現在世人眼前。
(二)“惡女”形成之家庭影響
家庭是一個人的啟蒙場所,個人性格的養成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身生長的家庭環境。小說的第一章,笹垣警官和古賀警官第一次去西本文代家中,唐澤雪穗就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對兩位警察,唐澤雪穗謹慎地進行了身份確認,而這一舉動恰恰傳達著一個訊息:以往非人般的遭遇給予雪穗的心理陰影之大,她害怕一開門迎來的是性格變態的成年嫖客。隨后,在等待西本文代的過程中,雪穗一直手捧著《飄》,眾所周知,《飄》的女主斯嘉麗一直追求主宰自己命運,單從這一點來看,雪穗從小對“斯嘉麗”充滿向往,飽受摧殘的心漸漸變得充滿野性。東野圭吾刻意描寫這個情節恰恰暗示了黑暗中的雪穗渴望成為像斯嘉麗那樣堅強的女性,而不是像自己的母親一樣渾渾噩噩,墮落無能。
可以說雪穗所處的家庭與社會環境,是她后來作惡的首要誘導因素,過早地接觸人性的丑惡與母親的貪婪,導致了她性格上的自私,所以唐澤雪穗在以后的大多數作惡行為也是為了掩蓋內心的自卑,在這樣的家庭熏陶下,雪穗心靈上的扭曲初步形成,為后期唐澤雪穗“惡女”形象的形成埋下伏筆。
(三)“惡女”形成之性格影響
一個人的性格在幼兒時期就打下了基礎,家庭環境影響一個人性格的形成,而一個人的性格又會約束他的處事風格。唐澤雪穗的家庭環境與童年陰影導致了她自私自利的性格和為達目標不擇手段的處事風格。成年后,為擠入上流社會嫁給家境富裕的高宮誠,她通過指使桐原亮司假扮警察的手段,使高宮誠失去了表白三澤千都留的機會,從而套住婚姻目標人物,完成人生身份的轉變……這一切舉動都表明了唐澤雪穗的嫉妒心之重,她不允許任何人掩蓋自己的光芒,自己得不到的,別人也不可能得到。從偽造親生母親意外死亡到一步步掃除身邊阻礙自己的同學朋友,唐澤雪穗心中的“罪惡之花”正在慢慢開放,如同玫瑰莖上的尖刺刺向每個人的心臟。故事發展到這兒,唐澤雪穗的“惡女”形象逐漸凸顯。
從一系列的描寫中,東野圭吾已經向讀者暗示了唐澤雪穗在成年后的性格特點,即工于心計、表里不一等,而這樣的性格在后來則影響著唐澤雪穗一生的選擇。
二、“惡女”形象的當下反思
我國學者薛玉鳳在其著作《美國文學的精神創傷學研究》一書中提到:童年心理創傷有些可以自動痊愈,但也有一些心靈創傷的影響會延續較長的時間,甚至會影響終身。
對于童年心理創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應對方式,多取決于個人的人生經歷及其性格特征。即使是唐澤雪穗也會偶爾閃現人性的光芒,因為“惡女”并不是她的自然屬性。假設每個人性格中都存在著“惡”的一面,那么好人與壞人的不同大概就是有些人能夠恰當地應對某些內部的心靈傷害以及外部的身體傷害后仍保持善良的本性,而類似于唐澤雪穗這樣的“惡女”由于缺乏后期的關愛與撫慰,則要一直背負著童年的心靈創傷,努力將自己偽裝成一枝刺人的玫瑰來保護自己受傷的靈魂,始終不肯以真面目示人。
東野圭吾塑造的“惡女”形象深入人心,比一般的“圣女”形象來得更加深刻,給人的反思也意味無窮,大部分讀者懷著沉重的心情讀完后,對于唐澤雪穗和桐原亮司的同情也遠大于批判厭惡,因為東野圭吾留給讀者思考的東西很多,而大多數讀者考慮的或許是:什么導致了本該單純的孩子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現實生活中,我們又該如何應對類似的事件?東野圭吾向人們傳達的不僅是“惡女”群體的存在,更是呼吁大眾關注兒童心理創傷的修復,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正確引導兒童應對童年時期的傷害,從而避免他們在未來的路上駛離人生軌道,背離社會人性。
參考文獻:
[1]張萌.論東野圭吾《白夜行》與《幻夜》中的“惡女”形象[J].語文學刊,2016(9).
[2]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M].劉象愚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
[3]肖霞.全球化語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學[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
[4]張葉.談東野圭吾的消極文學——從“白夜”行到“幻夜”的女人和她們的武器[J].文教資料,2017(7).
[5]朱文清.警惕不同家庭模式對幼兒性格發展的負面影響[J].科學導報,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