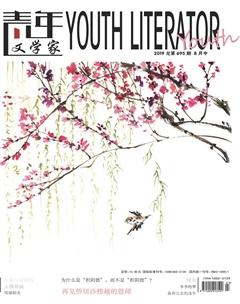河南地方戲《卷席筒》的敘事組合與聚合
孫伯翰
摘? 要:《卷席筒》在河南戲曲界已經流行了40年且未有降溫的跡象,這種現象在建國后新創作的河南地方戲中是十分罕見的,可是縱觀全劇,我們可以看到《卷席筒》情節結構較為簡單、人物性格單一、敘事手段單調,故事本身似乎沒有什么特色,但是緊靠演員的演技能夠讓一出戲火爆四十年似乎也不大可能,小蒼娃的最著名扮演者“海連池”在舞臺生涯中塑造形象眾多,可大多數觀眾記得的還是他扮演的“小蒼娃”。結合敘事學與符號學的手段分析《卷席筒》可以解決為何簡單的故事同樣可以吸引河南觀眾這個疑問。
關鍵詞:卷席筒;標出性;丑腳
[中圖分類號]:J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3--02
一、作為敘事組成的丑腳
《卷席筒》雖然是大團圓結局,但細讀劇本可見其中有一些不夠團圓的因素,拋開家產盡失不說,小蒼娃與曹寶山的父母雙雙死亡就為整出戲增加了幾分悲劇色彩,因為家產問題弄得家破人亡的故事在各類文藝作品中屢見不鮮,但是像《卷席筒》這樣把這種故事演成喜劇的確是少見。這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首先,在《卷席筒》中,“悲”或是“喜”的效果并不由整個故事的人物命運決定,更大程度上是由敘事者的敘事視角決定,觀眾只會在意被敘事者強調的那個人物,也就是主人公的最終命運,只要敘事者認定主人公高興,即使主人公父母雙亡,觀眾依然會將此劇作為喜劇來看待。《卷席筒》能夠讓觀眾完全被敘事者牽著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主人公小蒼娃所使用的腳色行當是“丑腳”。在戲曲觀演的實踐中,丑腳更能夠吸引觀眾的注意力,而在戲曲觀演的默認規則中,丑腳本身就意味著該人物的行為可以超出日常社會的行為價值規范,對該人物的評價也要超出日常社會的倫理體系,更重要的是,在傳統戲曲中,丑腳相對于劇中其它人物大多有著較強的獨立性,似乎游離于劇情之外,即使使用丑腳的劇中人物與其它劇中人物有著親屬、朋友、同事之類的關系,這種關系相比其它腳色行當構建的關系也不夠緊密。在觀劇時,由于小蒼娃“使用”了“丑腳”這一行當,因而整體上觀眾們便不會太在意該人物相關的其它人物。在此可以發現,至少在河南地方戲中,腳色行當對敘事的效果造成了重要影響,應當像“情節”、“性格”、“視角”一樣被列入戲曲敘事的諸要素之中。
《卷席筒》中得小蒼娃為丑腳,而丑腳在眾戲曲腳色之中有其特殊之處。其在產生只時就不是為了塑造人物形象或是推動敘事而出現“丑腳之命名大抵因其前身副凈色表演風格輕松笑鬧,以出丑、賣乖的喜劇形態示人,后又吸收了紐元子的伎藝之長,加之戲曲舞臺上滑稽演員往往搽灰抹土,較旁人略顯丑態,于是,此多重因素共同造就了一個‘丑字。”[1]總的來看,丑腳是對敘事文本的一種修辭,而修辭的詞匯自身多數是抽象的而非具象的。在句子中這點最為明顯,我們說“這是一支丑陋的筆”或是“幾個漂亮的小姑娘在跳舞”當中作為修辭的詞不可能是有具體形象的存在,擴展到戲曲文本,在觀眾對丑腳的認定中,丑腳被默認為修飾其它腳色或是整個劇情的存在,(例如,插科打諢對故事顯然是一種修飾作用)因而其人物可以抽象化而不必成為劇中實存的角色。
二、以倫理為導向的敘事
《卷席筒》中,主人公本身缺乏足夠的行動動因,也缺乏性格的變化,小蒼娃唯一的行動動因就是“義”,對與其沒有血緣關系的兄弟“曹寶山”及其妻兒之“義”,這點上照常理可以有文章可做,從故事情節來看,小蒼娃的親生母親,以為小蒼娃奪得財產為動因去謀害“曹寶山”之妻兒,而小蒼娃為了“義”而保護“曹寶山”之妻兒,這里涉及到了“血親”與“仁義”之沖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血緣關系是建立社會關系的基礎,而孝道則是最重要的為人原則,而仁義則是社會倫理的最高原則,對于這些原則之間的關系討論千年來爭論不休,孔子似乎也面臨過類似的選擇。《論語·子路》中有這么一段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顯然,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儒家文化更注重血親關系。《卷席筒》中,小蒼娃明顯是放棄了“血親”以及建立在血緣基礎上對親生母親的“孝道”而不假思索地選擇了“仁義”。甚至有悖孝道的對母親施以暴力行為,在母親看望他時咬了母親。即使母親有罪,但是這種暴力也是在傳統文化中難以接受的,又為何能在民風保守的河南地區得到認可呢?倘若從敘事符號的“標出”[2]原理來看,這種現象便很好解釋,所謂標出,指的是在一對對立的范疇/項中,人們通常會把具有特殊意義的范疇/項加以標出,給與特別描述。在《卷席筒》出現的“血親”與“仁義”這對項中,作者顯然更想要突出“仁義”的意義,故而會將人物的行為做出更有利于表現“仁義”的特殊處理,而不是像《哈姆萊特》這樣的文藝作品中常用的那樣,讓人物處于矛盾中搖擺不定,將內心的沖突展現給觀眾,進而引發觀眾的思考。“標出原則”與“展現內心沖突”除了會產生藝術效果差異之外,更多是文化差異,前者的目地在于利用“標出原則”建構觀眾的價值觀,而后者在于通過“展現內心沖突”引發觀眾對人性的思考;前者是敘事者給予觀眾價值觀,后者是敘事者引導觀眾自行產生價值判斷。
三、敘事的背后是身份認同
戲曲藝術自身也是整個社會文化的象征符號,不同類型的戲曲、不同的腳色行當背后都隱喻著不同的社會身份。我們現在說中國傳統戲曲中少有以丑腳為主角針對的是大劇種,而地方二小戲、三小戲其實有很多都是以丑腳為主角,但這類戲曲主要是以抒情而非敘事為目的。但曲劇的一大特征就是敘事,《卷席筒》最早產生于曲劇之中,開啟了河南地方戲對于小人物的敘事,使得作為民眾符號的丑腳從修飾語上升到了主語。但是作為主語的丑腳是建立在“眾”而非“個體”基礎上的。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史意味著權利,意味著最高價值。唯有有身份的人物才能于敘事中作為主角,擁有有個性的權力。身份卑微的丑腳則多被塑造成類型化的人物,即使成了主人公,這一特征也難以改變。與此相關,出現在中國敘事中的“民眾”不大可能有個體精神,這是中國文化之傳統,也是中國藝術的傳統, 如果想讓作為修飾符號的丑腳以及其所代表的“大眾”上升為主語,就必須賦予其某種“大眾”某種共同認定的性質的理念,使其具有抽象品質的代表性。小蒼娃似乎是觀眾自身某一理想的外在投影,而這種理想顯然是基于“眾”之基礎,“眾”不同于個體,只能是一般性的,抽象性的。從歷史敘事的角度來說,無論是作為大歷史敘事(歷史劇),還是生活歷史敘事(家庭劇),只可能是單線索的,單一視角的,觀眾與敘事者與主角三位一體的。這是一種對于生活真實而非藝術真實的追求,更深層次則是對自我認同的追求。一個與自己相似的“人”能夠出現于舞臺當中,便是身份上的承認。與此相對,切換敘事角度、區別敘事者與主角則很難讓觀眾找到自我身份的投射點。無論是歷史劇還是家庭劇皆是如此。
最后,河南觀眾在一開始就預設了他們理想中得戲曲模式中,一定要帶有倫理價值判斷,且倫理觀念必須符合當地人的理想,不容任何質疑。一些劇目即使在產生之初破壞了傳統倫理價值,也會在演出過程中被逐漸“修正”。例如,《李豁子離婚》本是為了宣傳婚姻自由,以及女性的離婚權利,但是在不斷的改編中已經成了對“李豁子”的同情,以及對離婚的諷刺。而這似乎可以解釋為何在一些《卷席筒》演出中小蒼娃咬其母親的情節消失了,這個情節顯然與多數河南農村觀眾(尤其是作為主要觀眾群體的家庭婦女)之倫理觀念有所沖突。由此可見,由抽象理念外化成的角色是河南許多地方戲觀眾的要求,他們要在戲劇中看到自己群體“眾”外化出的理想。
參考文獻:
[1]丑腳與紐元子關系辨析[J].韓淑帆,四川戲劇,2016,04,48.
[2]參見趙毅橫:符號學原理與推演[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