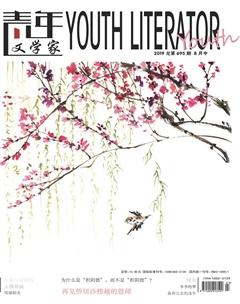“祖靈信仰”:電影《賽德克?巴萊》的人類學儀式闡釋
陳棟
摘? 要:電影《賽德克·巴萊》中飽含臺灣原住民原生態文化,其中核心是“祖靈信仰”。通過對電影中各種“儀式”的解讀,揭示其深厚的文化意義,即祖靈信仰與血液崇拜有關,祖靈之地的神圣性,原始而野蠻的本質。
關鍵詞:賽德克·巴萊;儀式;祖靈信仰;文化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3--02
一、《賽德克·巴萊》的人類學儀式敘述方式
電影《賽德克·巴萊》講述的是清政府向日本“割臺”后,臺灣“原住民”反抗日本侵略中、最具代表性的“霧社”事件。從部落間的沖突到日軍的殘酷 統治,最后部落覺醒與反抗。導演魏德圣并不是簡單地還原歷史,而是盡可能地有深度、更復雜、多元化的展現那段歷史。在電影中, 有許多儀式可供我們理解那段文化沖突中的歷史。
反抗的一方是以賽德克族為代表的臺灣原住民。電影中的背景是19世紀末期,在影片中,導演真實地再現了賽德克族的具有原始氣息的生活狀況和生態環境。從賽德克族的生存方式來看,其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仿佛還停留在原始社會階段。族群中的男人以打獵為生,女人們在家織布。影片的開頭就展示了主人公莫那·魯道率領族人用弓箭和火繩槍狩獵的情景。族人將打的獵物剝下的皮與山下漢人交換來吃的米、鹽。買賣雙方還是通過最原始的物物交換的方式來獲取的。賽德克族中族群與族群之間,主要是通過有特定顏色和條紋的衣服來區分的,族人穿的衣服非常簡單,不論男女均為長袖長衣,女性長衣直到腳邊;男子不穿褲子,只穿寬松的長衣。并且不論冬夏秋冬,族人服裝都是一個樣式。在住的方面,族人住的是簡易的欄桿式的茅草屋。草屋不高,并且屋內空間狹小,睡覺的床也只是土炕或是用木頭達成。另外,賽德克族生活在山林之中,山林密布、河流縱橫。地面凹凸不平,而在電影中,不論大人還是小孩兒、不論是在家還是在叢林中同敵人廝殺,族人們都是不穿鞋襪的,光著腳跑。這樣原始而傳統的生存、生活方式,也體現了賽德克族人追求簡單、自由的生活態度。
彭兆榮老師在《人類學儀式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提到將“小至個人,比如出生、成年、嫁娶、做壽、喪葬、祭奠等一系列活動”[1],都可以視之為與儀式有關。賽德克族生活中的“獵頭”、“刺面”甚至是唱歌跳舞,都可以看作是儀式中的一部分。
最能體現臺灣原住民原生態文化的就是賽德克族的“成人儀式”。整個儀式過程又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獵頭”儀式,第二部分是“刺面”儀式。兩個部分也是有先后順序的。“獵頭”在前,“刺面”在后。在賽德克族中,青年人一定要去獵頭。如果有男性成員到了一定年齡,就會在部落的頭目的帶領下完成他們的“成人禮”。就是要去獵殺敵方部落的男人并親自砍下他們的頭,帶回部落作為自己的戰利品,才有資格“刺面”。在完成了這些“成人儀式”后,才有資格娶妻生子,才能在部落中生存下去。男莫·那魯道在完成了“血祭祖靈”后,回到部落中,由母親幫助他完成“成人儀式”的最后一個環節——“刺面”儀式。儀式的過程十分簡單,就是由母親在他臉上刺上“男人的記號”,完成“紋身”的儀式。紋身的方式落后、工具簡陋,紋身的主要工具竟然只是一個是有釘子頭的木錐。在這樣簡單的儀式后,莫那魯道就必須要遵守祖律的約束,才有資格守護獵場、守護部落。
在賽德克族中,女性也能“刺面”。以馬赫坡社為例,女性只有成家后并且要善于紡織才能有面部紋身,額頭上都是上下方向的三道,鼻子以下和整個臉頰都布滿了紋身,臉上的紋身分布也非常有意思,恰好是男性長胡須的地方,所以,“刺面”后的女性,看起來就是一個刮了滿臉胡須的男人的形象。總之,有資格“刺面”的女性也能通過彩虹橋、前往祖靈之地,她們在部落中也有一定影響力,在男人們外出打獵以及與敵方部落作戰的時候,她們就成了部落的領導者。
電影還向觀眾展示了賽德克族人娶妻的儀式。莫那·道魯追隨心中的“鹿”打到獵后,回到族中,將獵物當作聘禮娶妻子,在族中歡慶婚禮的篝火盛會上,族人圍著篝火邊唱邊跳,跳的“舞蹈”也只是幾個簡單動作的不斷重復,但就是在這簡單的儀式卻非常歡快的氣氛中,莫那·道魯與他的妻子完成了神圣的結婚儀式。
二、儀式重構:“異文化”介入對《賽德克·巴萊》的影響
彭兆榮老師還提到儀式的混亂還與“異文化”的介入有關[2]。《賽德克·巴萊》中講述的是兩個完全不同層次的文明之間爆發的沖突。相對于賽德克族信奉“萬物有靈”的原始的文明而言,日本的現代文明則更加相信掠奪與擴張。在日本占領“霧社”后,賽德克族受到了日本的嚴格管制,沒收槍械,神圣的“獵場”雖然在,但是“獵人”卻消失了。日本海軍在基隆港登陸后,受到了臺灣民眾“以卵擊石”般的抵抗,他們自發組織起來,以刀槍木棒為主要兵器,在影片中,戰爭的雙方都將自己的行為視為神圣的。現代化的日本將賽德克族稱為“生番”,認為土著民的語言、吃穿住行、生活習慣、生存方式都是野蠻原始的產物,因此在“霧社”大興土木建造現代化的城鎮,建立日式學校、讓生番學習日語,還禁止生番狩獵、刺面。日本人相信這是給未開化的土著帶來現代文明,將原始野蠻的民族帶向“太陽旗”照耀下的文明社會。然而,在賽德克族人眼里,日本人的做法卻是對神圣的獵場和祖靈之地的冒犯與破壞。打破了這種和諧永存的狀態。阻礙了他們與祖靈的交流。
三、“祖靈信仰”: 人類學儀式視角《賽德克·巴萊》的母題呈現
第一,賽德克族的血液崇拜。我們能從那些沾滿鮮血的儀式中,感受到賽德克族的祖靈信仰都與“血液”有關。另外,賽德克族男人的戰衣是有紅色的條紋,紅色是與血液相關的。可見,土著民對“血液”的崇拜也是祖靈信仰中的一部分。所有的儀式都需要“血液”或者紅色來展開。在“獵頭”儀式中,砍下敵人的頭顱,是需要莫大勇氣的。在生與死的抉擇中,敵人只能是獵物。還有在“刺面”儀式中,必須用到自己的血液來完成“成人儀式”中的最后一部分。當然,人天生就怕血,不怕血的人,在心理上就會有極大的優勢。電影中,莫那·道魯殺了鹿后,生飲血、生吃肉,仿佛鹿血有靈力,喝了后就能治療自己,讓自己強大。血液是生命力的體現,越新鮮的血液,生命力就越發顯得強大。因此,莫那·道魯相信,鹿的部分生命力會從喝下去的鹿血中釋放出來,這股力量將會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從而增強自己的生命力。我國古代社會中,就有鮮血祭旗的歷史。軍隊出征前,將帥一般都會“祭旗”,就是殺死人或動物,并用其鮮血獻祭神靈,讓神靈品嘗,期望求的神靈的庇佑,打贏敵方。當然,還有其他的含義,比如鼓舞軍隊士氣、殺一儆百。
從目的來看,這都是為了生存而狩獵、殺戮,在殘酷的生存環境中需要血液不斷地刺激自己的神經,帶來持續而強烈的興奮感,鍛煉極強的心理素質。讓見血就興奮成為潛意識,增強作戰能力。因此,賽德克族人關于祖靈的信仰是與血液交織在一起的。
第二,祖靈之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電影中,祖靈鳥多次出現,并直接影響了故事的發展。在莫那·道魯完成了“成人儀式”后,父親帶著他和族人狩獵,莫納向父親尋求幫助解釋夢中出現的“鹿”,這時祖靈鳥的出現打斷了他。在賽德克族人眼里,祖靈鳥是祖靈派來的,祖靈鳥的歌聲是吉利的,預示著未來的美好。因此父親讓他去追尋夢中的鹿、去完成娶妻生子的神圣儀式。在日軍殘酷統治下,莫那·道魯迷失了、失去了對祖靈的信仰。在小溪邊,耳邊傳來祖靈鳥的歌聲,恍惚之中他見到了逝去已久的父親,與父親來了一場久違了的和歌起舞,再與父親靈魂的交流中找回了對“祖靈”的信仰。因此,祖靈鳥的形象也是神圣的。在賽德克族人看來,樹木見證了祖靈的傳說從無到有的過程,因而也是神圣的。臺灣地形和氣候的影響下,樹木一般長得高大、堅硬,樹木的生命力也十分頑強,只要根部不受嚴重的損壞,既是將樹砍倒,它還能從“樹樁”長成大樹。樹的生命周期長,從樹苗長成小樹、再長成通天般的大樹,這由小到大的生命過程也肯定見證了祖靈。因此樹以高大的外形和強大的生命力讓賽德克族人認為是神圣的。在日軍大規模的砍伐中,樹沒了,森林里的生靈也消失了。因此,在影片中,賽德克族人感嘆原來的“獵場”不見了,沒有了狩獵、沒有了血祭儀式、沒有了刺面,也就無法通過彩虹橋,到達祖靈之地了。
在原住民眼中,獵場的生靈都是祖靈提供的、賜予的,在祖靈的庇佑下,族人開始偉大的狩獵,是神圣光榮的。這樣的狩獵生活在他們眼中也是美好的、神圣的,這是對祖靈最好的、最虔誠的禱告。因此,哪怕感受到了日本的現代文明帶來的生活上的改觀,即便有過短暫的迷失,賽德克族也依然遵循對祖靈的承諾,守護好神圣的獵場。反對外族人——日本人的侵略與破壞。他們也相信,得到祖靈庇佑的賽德克族會贏得這場力量懸殊的戰役。哪怕戰死在獵場,在彩虹橋的那頭,祖靈將會等待戰士們英勇的靈魂到來。彩虹橋的神話和祖靈之地的傳說,讓族人相信通過了相應的儀式的考驗后,最終會跨入永生的行列、進入到“祖先永遠的靈魂獵場”。
第三,凸顯了賽德克族原始而野蠻的文化。正是因為賽德克族原始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狀況,他們的信仰和文化也都凸顯了原始而野蠻的一面。電影中,莫那·道魯為了娶妻獵殺鹿時,差點射殺族人,還蠻橫的警告族人,不要搶他看上的獵物。殺死獵物后,他用小刀劃開獵物肚子,喝鹿血、生吃鹿肉。表明自己占有之后,再與族人分享,場面非常殘忍而且血腥。還有一幕,莫那·道魯在伏擊敵方部落首領之子——道澤的鐵木瓦力斯時,卻誤傷族人,還怪罪并警告族人不要跑在他前面。殺小孩就是將敵對部落的希望殺死,這是他與族人在“擁擠的”獵場殘酷的生存方式,在他們眼中,這也是守衛和擁有獵場的最佳方式。這也是極其殘忍而血腥的。還有在“霧社事件”中,這也是影片爭議最多的部分。在“霧社事件”中,賽德克族人得了魔癥一般、喪失了人性,不分士兵還是手無寸鐵平民,就連日本女人和孩子都不放過。在“大出草”后,賽德克族遭受了日本的瘋狂報復。原來幾千人的大族群,戰后只剩下不到三百人的奴女兒童,其中最彪悍的馬赫坡社竟然被滅族了。除開日本殘忍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自身的野蠻和殘暴。為了給族中男人留下口糧、不拖累男人們,大多數婦女紛紛自殺,其中以馬赫坡社最為嚴重。族人擔心兒童的哭鬧聲會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暴露男人們的行蹤,為了不影響戰斗,父母竟然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孩子,所謂“虎毒不食子”,當莫那·道魯大敗而歸時,竟然拿著槍指著自己族中的婦女和兒童,逼迫她們為了所謂的“祖靈”崇拜自殺。不給馬赫坡社留下一顆種子,要知道,生命的延續、生命的繁衍,也是祖靈崇拜中的一部分。這也足以體現賽德克族文化的原始而野蠻的特質。
注釋:
[1]彭兆榮.人類學儀式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
[2]彭兆榮.人類學儀式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
參考文獻:
[1]彭兆榮.人類學儀式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魏建亮.《賽德克·巴萊》人物形象的文化闡釋[J]. 電影文學,2013(12).
[3]許樂.《賽德克·巴萊》:文明沖突之痛[J].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14(02).
[4]曾亞玲.從《賽德克·巴萊》看臺灣原住民賽德克族文化[J].電影文學,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