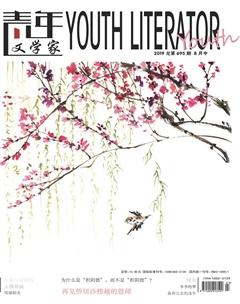布爾加科夫象征藝術的獨特性分析
楊雅文
摘? 要:布爾加科夫創作的文學世界是一個象征的世界,但狹義上的象征,作為藝術假定形式的一種,在其創作中并非獨立出現,而是被作者巧妙地融于各種藝術形式之中,從而構成一個宏大的象征世界,這也是布氏象征藝術最突出的特點。本文將從這一角度,結合《大師和瑪格麗特》中怪誕和神話所體現出的象征性,對此進行分析。
關鍵詞:布爾加科夫;象征;大師和瑪格麗特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3--02
象征本身所包含意義的無窮性和深邃性,能夠不斷引發人的聯想和思索,從而產生新的意義,就像是一個多棱鏡,在陽光的折射下釋放出異樣的光彩,繽紛奪目。顯然,象征已成為作者創作中一種獨特的藝術語言,在小說中常常與怪誕、神話、夢境等多種藝術表現手法同時出現,“它們的共同特征都是在表層上人為地拉大現實與作品之間的距離,以達到文學的‘奇異化效果。這些形式可以使讀者通過新穎的角度去重新看待因常看而失去感覺的現實。”布爾加科夫正是靈活地運用這些手法,從而加深讀者對作品的感受和認知,不斷拓寬作品的廣度和深度,使讀者在他所精心建構的語義紛繁的象征世界盡情遨游。
1、怪誕與象征
怪誕是布爾加科夫最常用的藝術表現手法,文學中的怪誕通常是將作品形象或表現形式以非理性的方式夸張和變形,從而展現出一個反常的、荒謬的世界,帶有強烈的諷刺效果。如果說布爾加科夫的創作是世界的一面魔鏡,那么怪誕一定是組成這面魔鏡必不可少的因素。他的作品往往都不是對現實世界直接客觀的反映,而是將之以一種奇異的方式呈現出來,富有奇特的魔力。
談及怪誕與象征的關系時,乍一看兩者之間并無直接聯系,因為作品的人物或情節用怪誕的方式處理后,最直接的是增加了閱讀的快感,引起讀者心中笑、吃驚、恐怖、甚至是惡心等復雜感受,可能并不帶有明顯的象征意義。但要知道,文學中的怪誕并不是單純依靠作家天馬行空的幻想虛構而成,“怪誕的標志是可被人們意識到的虛幻和現實的混合”,因此怪誕是對現實生活的映射,將之置于實驗性的想象中,盡管用一種荒誕化的描述方式表現出來,卻是在魔幻中尋求真實,以異常象征常理,促使人們重新審視當下的生活以及他們的道德靈魂,在驚訝中引發深思,而這一過程正是怪誕的象征性所在,讓人們去思索光怪陸離的現象之外蘊含的更廣泛的意義。在這方面,卡夫卡的《變形記》可謂是經典的代表作品,作者通過展現主人公變為甲蟲之后所面臨的生活以及周遭人對他態度的變化,充分反映了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和人們內心真實的生存狀態,在控訴病態社會現實的同時,也表達了追尋人性完善、個體性和社會性相協調的愿望。同卡夫卡一樣,布爾加科夫善于將自己對現世的態度和觀點隱藏在怪誕現象的背后,從而賦予作品更深層次的寓言意義。
在《大師和瑪格麗特》中,作者塑造了來自彼岸世界的撒旦和其手下的形象:左眼珠呈綠色、右眼珠漆黑的魔王沃蘭德;身材像竿子一樣纖細、戴著一副奇怪眼鏡的唱詩班指揮卡維羅夫;一只無比碩大、會開口說話的黑貓;長著棕紅色頭發、露出獠牙的阿扎澤勒。這群魔鬼在傳統意義上象征的本是使人墮落的邪惡勢力,在布爾加科夫筆下卻成為伸張正義的戰士,盡管他們的到來把整個莫斯科鬧的雞犬不寧、人心惶惶,但所做之事無不透露著善戰勝惡、光明戰勝黑暗這一樸素而永恒的真理,將人性的美與丑展露得一覽無余。在沃蘭德的魔術表演中,大把的鈔票從天而降,人們在金錢的誘惑面前立刻暴露出貪婪、自私的本性,為了不讓報幕員戳穿這美好的、如夢境般的現實,有人甚至直接說出“掀掉他的腦袋”這樣泯滅人性的話。于是沃蘭德真的讓他腦袋搬家,血濺當場,這才喚起了人們的同情和憐憫之心。然而,當沃蘭德的把戲繼續進行,把舞臺瞬間變成一個豪華的、供人免費挑選的商場時,人們又一次沉浸在物質的世界里無法自拔。毫無疑問,這些人們在后來都受到了應有的懲罰,比如走在街上身上的華麗衣服突然不翼而飛,鈔票在使用時卻變成了白紙等等。怪誕的情節實際上象征著當時莫斯科真實的社會現狀,暗含著作者的價值取向和道德判斷,正是在這之間潛在的象征聯系,促使讀者忍俊不禁的同時也對自我和社會進行重新考量。
小說中類似的怪誕情節俯拾皆是,如瓦列劇院的經理瞬間從50號住宅里被拋到了雅爾塔的海岸邊,房管所主任因家里無故多出許多外幣而被查處,劇院財務協理里姆斯基深夜在辦公室看到裝扮成人樣的女尸等,但最為怪誕的莫過于撒旦的那場上元舞會,在舞會上出現了莫文聯主席柏遼茲的頭顱,這是一個因不信上帝和魔鬼的存在而被沃蘭德預言死亡的人,沃蘭德讓身首異處的他親眼看到這個他不相信的彼岸世界,并把他的顱骨當做酒杯盛滿鮮血,至此柏遼茲徹底化為虛無。這一無比怪誕的情節,不僅反映了沃蘭德對于信仰缺失、靈魂缺失之人的憎恨和報復,更是一個好戰型作者強烈意志的象征。然而,在當時壓抑的政治環境下作者強烈的思想情感無法在現實中得到釋放,小說自然就成為感情抒發的出口。小說的世界完由他主導,因此,他在自己的小說中塑造了諸如沃蘭德這樣超乎自然力的、擁有主導一切力量的人物形象,用一系列打破正常思維邏輯的怪異情節為自身強烈的情感發泄找到了依托。正如萊斯莉·米爾恩所說,布爾加科夫“在一個小說空間里征服了他的敵人,在這個空間里他和沃蘭德一樣,是大師”。
作者正是利用大膽浮夸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營造出一個超出常理之外的世界。盡管怪誕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品的寫實性,但作者正是通過這種奇特的方式在現實和超現實之間尋求一定的象征聯系,從而體現創作的哲學理念和意蘊。
2、神話與象征
神話在不同場合中有多種解釋,但在傳統意義上,神話自遠古時期就已流傳下來,包含著人們對世界起源、宇宙開端等方面的猜測,作為集體共同創造的產物而代代相傳,體現著集體意識和人類精神。因此在神話中蘊含的各種人物和自然的原型,其本身就象征著人類的意志,涵蓋了人類最原始的潛意識里對是非判斷的準則。榮格曾說:“要了解藝術創作與藝術效果之秘密,唯一的辦法是,回復到所謂的‘神秘參與狀況——回復到并非只有個人,而是那人人共同感受的經驗,那種個人之苦樂失去了重要性,只有全人類的生活經驗”,神話因自身所具備的這些特點,無疑是文學創作者展現藝術本質的最佳途徑。
《大師和瑪格麗特》是作者藝術創作的頂峰,在這部最具特色的代表作中到處洋溢著“神話的喧唱”,把圣經神話合理地引進《大師和瑪格麗特》,使之對現實生活構成一種隱喻和對照,這一方面加強了作品對像是生活的縱深開掘,賦予了作品的歷史感。布爾加科夫不僅運用了圣經神話原本所具有的象征意義,更是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天才的重構,并賦予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更深刻的內涵,從而創作出屬于作者的新的神話。
小說中非現實的人物主要有三個,魔王沃蘭德、基督的化身耶舒阿和猶太總督彼拉多,構成了以沃蘭德訪問莫斯科和古代時期彼拉多處死耶舒阿的兩條主線,因此無論是在莫斯科的現實時空還是耶路撒冷的古代時空,都有神話因素的參與,二者之間相互滲透,這點首先體在人物形象上有所體現,鬼神之中帶有人性,而在普通人的身上卻又彰顯了神性。彼拉多和耶舒阿的故事是作者根據《福音書》改編而成,耶穌是耶舒阿的原型,兩人具有相同的命運道路,但又有所不同。耶舒阿在小說中并非是神的兒子,只是一個不記得自己父母是誰而四處流浪的哲人,作者給這一形象注入了更多的人性,以人的角度化解了無法感觸的神性和高高在上的真理及道義,也正因此才深深觸動了彼拉多,讓他意識到了自身的怯懦。魔鬼沃蘭德也有別于人們一般印象中冷厲可怕的惡鬼形象,具有更多人的情感,他在上元晚會上應瑪格麗特的請求而減少了弗莉達的痛苦,他自己也說:“有時候,慈悲之心會狡黠地穿過最小的縫隙完全意外地鉆到我這里來”,沃蘭德更是成全了在苦難中飽受煎熬的大師和瑪格麗特,給予了他們永恒的精神家園。與之相對應的,大師和瑪格麗特,兩人都來自現實,卻不屬于并且超脫于現實。尤其是瑪格麗特,在她身上沒有一絲來自世俗的愚昧迂腐之氣,始終堅持著愛和理想,為了見到大師,不惜變成魔女,投奔于魔王,在這個普通女子居然有著如此超然于世的執著、善良、對愛情的忠貞和追隨的勇氣,作者賦予了她神一般的完美的光環。
由此一來,作者筆下的現實世界便融入了神話色彩,而神話的世界也充滿了更多的人性,讓不同時空中的人與神具備了更多相似的特質,盡管他們的身份不同、立場不同,但他們都對一直以來人類所認可的精神價值有著不懈的追求,都在自身追尋真理的道路上不斷前進。布爾加科夫利用神話所構建起的兩個時空,在本質上所包含的精神實質具有共通性,從而使二者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交匯到一處,在整體上構成一個龐大的象征體系。
3、結語
全文以《大師和瑪格麗特》為例,淺析了布爾加科夫是如何巧妙運用不同的藝術手法,體現出作品巨大的象征內涵,從而形成了個人獨特的創作風格。在《大師和瑪格麗特》中讀者能看見一幅幅奇妙的畫面:光怪陸離的現代莫斯科、大師和瑪格麗特真實動人的愛情、集宗教神話和日常生活于一體的復雜時空等等。在這些現象的背后,都深藏著一個精心構建的象征世界,包含著一位作家或者說作家所代表的知識分子對這個社會的洞察、對這個時代的沉思。而融于各種藝術手法之中又通過其所表現出的象征性,在表象之下隱射了更為普遍的、深刻的意義,這無疑成為布爾加科夫表達藝術創作的最好方式、情感抒發的最佳出口。
參考文獻:
[1]王宏起,布爾加科夫小說的虛幻世界[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2年,第5頁。
[2]P·湯姆森,A·欣奇利夫,J·江普,荒誕·怪異·滑稽——現代主義藝術迷宮的透視[M].杜爭鳴等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5頁。
[3]米·布爾加科夫,大師和瑪格麗特[M].錢誠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147頁。
[4]萊斯莉·米爾恩,布爾加科夫評傳[M].杜文娟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第262頁。
[5]榮格,現代靈魂的自我拯救[M].黃奇石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第261頁。
[6]王宏起,布爾加科夫的虛幻世界[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2年,第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