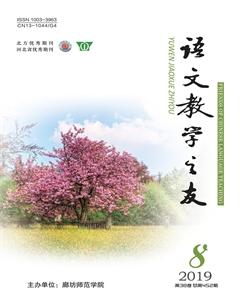淺談阿長身上的“母親”影像
王元貞 袁海鋒
摘要:阿長是《朝花夕拾》中反復出現的人物形象。“母親”的影像在她身上強烈聚焦——阿長對“母親”的身份有著強烈的渴望,以至產生誤認;“魯迅”對母親角色則因缺失而有意地尋找。以此為抓手,追問二者間的復雜互動,對理解阿長文本行為、把握魯迅創作心理,繼而推進《朝花夕拾》“整本書閱讀”都是有益的。
關鍵詞:“母親”影像;阿長;整本書閱讀
阿長,“是一個一向帶領著我的女工”(《貓·鼠·狗》)。在魯迅創作《朝花夕拾》諸文之時,阿長“辭了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罷”(《阿長與〈山海經〉》)。無論從魯迅與阿長的身份關系,還是時間隔膜的長久,魯迅內心的阿長形象都應該是淡漠的。事實上,女工阿長之于魯迅的印痕卻是深刻、難忘的。《朝花夕拾》的十篇文章中,除專寫阿長的《阿長與〈山海經〉》《貓·鼠·狗》《二十四孝圖》《五猖會》《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四篇文章,亦有涉及阿長的文字。相形之下,母親魯瑞在魯迅作品里出現的次數則要少得多,且面目模糊感情淡薄。阿長無疑是《朝花夕拾》,甚至是魯迅童年回憶的第一女主角。在魯迅與阿長的意識深層,聚焦在阿長身上的都有某些“母親”的影像。以阿長的形象探究為抓手,追問阿長身上的“母親”影像,是理解阿長文本行為、把握魯迅創作心理,甚至深入推進《朝花夕拾》“整本書閱讀”的有益嘗試。
一、阿長“母親”身份的渴望與誤認
阿長雖在《朝花夕拾》中占據的篇目極多,但對她身世背景的交待卻不過只言片語。即使專門為她而作的《阿長與〈山海經〉》中,篇首、篇尾處涉及身世的文字不過百余,可謂語焉不詳。不過,依托這些散落各篇的零散文字,足以重構出阿長的一些生活輪廓,以及她由此產生的對“母親”身份的渴望及誤認。
“僅知道有一個過繼的兒子,她大約是青年守寡的孤孀”,《阿長與〈山海經〉》中這句介紹阿長身世的話,是窺破阿長“母親”身份渴望的是佳切口。過繼是傳統宗族社會中的一種收養行為,宗族男丁無子,收養同宗之子為后嗣,以續香火。阿長有過繼的兒子,說明她有過婚姻,并且婚內未生男丁,甚至沒有子女。繼子與原生家庭、親生父母的情感并未完全中斷,他與繼父母的情感建構是個重大問題。但過繼制度并不聚焦這樣的問題,因為它的核心更多是一種宗族傳承關系。連“元旦”都未休假回家,都要陪著“魯迅”(為與作家魯迅區分,文中涉及其童年時皆以“魯迅”指稱),這足以證明她“青年守寡的孤孀”這一身份,更從側面反映出她與繼子的情感關系。有這樣經歷的阿長,對兒子、孩子的渴望必然超出常人,對“母親”這一身份的渴望也超出常人。聰明可愛又頑劣好動的“魯迅”介入阿長的生活,必然會對阿長心中的母性情感有著巨大刺激與強烈滿足。阿長身上這種渴望情緒的確認,對于理解《朝花夕拾》中的阿長形象具有極大意義。
保姆阿長照料“魯迅”的日常起居,此時,保姆的身份與母親的角色便有了自然的重合。阿長陪好動貪玩的“魯迅”日常游戲——“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常常拔它(何首烏藤)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曾因此弄壞了泥墻”“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雖然常因此而被批評——“說我頑皮,要告訴我的母親去了”,而這卻是阿長為著孩子安全的另一種關心與呵護。雖然會因為阿長的胖、擺成“大”字的睡姿、擱在“魯迅”頸子上的胳膊而讓“魯迅”不大佩服,但陪伴他度過童年一個個漫漫長夜的阿長,卻分明在承擔著本該母親履行的職責;阿長還是個“只要一看圖畫便能夠滔滔地講出這一段的事跡”(《二十四孝圖》)的民間故事高手,她的“美女蛇”“長毛”的故事都有她質樸的、寓教于樂的教育目的,也含有引導“魯迅”不要到園中搗亂、要聽話的母性善意。在“魯迅”與阿長關系中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山海經》事件,是阿長“母親”身份影像的一次最為強烈的顯示。“大概是太過于念念不忘了,連阿長也來問《山海經》是怎么一回事”,這足以說明“魯迅”對《山海經》渴望之巨,這份渴望的流傳之廣,以及成年的親人世界對“魯迅”愿望的漠視之甚。“哥兒,有畫兒的‘三哼經,我給你買來了!”阿長的這份禮物讓魯迅“似乎遇著了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因為這里邊有著太多出乎意料:“別人不肯做”,不肯找書的無疑是那位遠房的叔祖;“不肯真實地回答我”一定是“魯迅”認為說了懂它、說了有益的人;“不肯做(買)”的恐怕應該是孩子最為親近的,像母親一樣的人!“不能做的事”之人范圍自然包括阿長,這里不止她窮困的處境,更有她傭人的身份。阿長出乎意料地買來的《山海經》,雖然“刻印都十分粗拙”“紙張很黃;圖像也很壞”,但足以顯示她對“魯迅”心愿的在意,對“魯迅”的一種超出功利的關愛、呵護。阿長所做的這一切,于客觀于主觀都有著一種濃烈的“母親”身份渴望,甚至有意的誤認。
在看護“魯迅”飲食起居過程中,一些母性的職責會融入阿長的工作。這樣的融入又使得保姆身份與母親角色在阿長內心重合。對于一個沒有孩子、渴望孩子又做不得母親的女人來講,這樣的角色融入無疑是一種刺激、一種呼喚。它讓阿長在有意無意間承擔了“母親”的角色,滿足了她對這一身份的渴望。長久地陪伴“魯迅”,讓她更有了一種超越主仆關系的身份誤認。籍此,善良的阿長給了“魯迅”母親特有的關愛與溫情。對阿長而言,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幸福的付出。
二、魯迅“母親”角色的缺失與尋找
在照顧“魯迅”飲食起居時,阿長“母親”角色的臨時擔當,也意味魯瑞母親角色的臨時出讓,進而凸顯了魯迅與母親的實際母子關系狀態。在“魯迅”的日常生活中,比如睡覺、游戲、講故事、買《山海經》……母親魯瑞常常處于缺席狀態。即便偶有提及,也是在父親絕對權威的籠罩下,母親只是一個無力反抗亦“無法營救”的形象。吊詭的是阿長也出現在這樣“無法營救”的行列,不知是不是魯迅筆下的有意為之(《五猖會》)。在“魯迅”向母親訴苦阿長的睡姿以求解脫時,母親對阿長“怕不見得很好罷”的提醒是如此輕飄,以致“魯迅”對這件事絕望到“實在是無法可想了”(《阿長與〈山海經〉》),這絕望有幾分是對著母親的亦是耐人尋味。至于“魯迅”心心念念的《山海經》,他更傾向于母親充任“雪中送炭”的角色吧,可惜卻“不肯做”。《朝花夕拾》中涉及母親的文字,魯迅并未在其中表現出母子應有的溫情。
成年魯迅與母親的關系也并不那么和諧融洽。母親魯瑞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對新思想新觀念了解、認同有限,在精神層面與魯迅有著相當大的隔膜。比如婚姻,魯迅屈從了母親的安排,與舊式女子朱安成親。在魯迅看來,“這(朱安)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朱正《魯迅傳》第六章“母親的禮物”)。這段有名無實的婚姻,造成二人數十年的生活悲劇。魯迅晚年一再強調“母愛的偉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母愛如同濕棉襖,脫了感到冷,穿著感到難受”(馮雪峰《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我們做父親的人……決不能昧了良心,說兒子理應受罪”(《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這些表述,或明或暗,話里話外,分明折射著魯迅對母親復雜的情緒。這些情緒深層映射出魯迅內心對母親的隔膜、矛盾,以致缺失。
魯迅與母親復雜的親子關系、不甚愉快的過往經歷,都在魯迅這里形成一種隱性的力量,促使著他在紙上重構文學化的童年生活。魯迅的創作在反思母愛本身的同時,其實也試圖重新尋找“母親”角色。這時,照顧自己飲食起居、長久相伴相守的保姆阿長之于魯迅的角色意義也就逐漸變得清晰起來。
睡在保姆阿長身邊,當時的感受雖然不好,但阿長卻像母親一樣在黑夜中陪自己。雖然因翻磚、拔草而被阿長批評、被投訴,阿長卻像母親一樣擔心、關愛著自己。在“美女蛇”“長毛”“二十四孝圖”的民間傳奇故事里,阿長像母親一樣帶著自己遨游在神異的傳奇世界里。面對苦背《鑒略》,在“都無法營救”的人群里,除了母親,魯迅給阿長著重寫了一筆——“長媽媽即阿長”。雖然在當時看來這些瑣碎無趣甚至迷信,多年后卻給魯迅帶來了別人無法取代的精神慰籍。阿長湊了四五天假期,給她的哥兒“魯迅”買來她以為的“三哼經”——四本粗拙的小書,卻是魯迅“最為心愛的寶書”。阿長做的這些不僅滿足“魯迅”的一個個現實心愿,她的關心還填補了“魯迅”因母親缺席而導致的親情缺失,某種程度上實現了魯迅對“母親”角色的期望。也正因此,“魯迅”對阿長懷有深沉強烈的感念之情。“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的懷里永安她的魂靈”,直白而強烈地抒發了對阿長的懷念之情。這樣強烈地直抒胸臆在魯迅作品中是極其少見的,這足以顯示阿長在魯迅心目中近乎母親的重要地位。阿長之于魯迅,猶如大堰河之于艾青,阿琳娜奶媽之于普希金。在親情缺失的孤寂童年中,這些質樸的人給孩子們帶來了最底層、最淳樸卻也最溫暖的關愛與溫情。阿長以其“發自天性的質樸的愛”,粗糲而真切地陪伴著“魯迅”,在魯迅尋找重構童真世界的歷程中,成了魯迅理想的“母親”形象,甚至替代了母親的存在。在魯迅于家道中落、飽嘗世態炎涼的煎熬中,作為他蒼涼人生的一抹亮色,讓他在孤獨地抗爭與吶喊中,還有一個可以溫暖靈魂的棲息之所,不至于回首蕭索,茫然無助。或許,這正是《朝花夕拾》中一再提到阿長的原因所在。
“黃胖而矮”、睡覺擺成“大”字、把《山海經》誤以為是“三哼經”、粗俗而親切的阿長,在魯迅記敘的幾件小事中,她血肉豐滿地植根在魯迅的印象中,時隔多年回想起來,那些可笑的缺點、溫情的對待,都隱隱地顯出了阿長“母親”式的善良可愛。《朝花夕拾》對于“母親”形象的解構與建構是雙向的,其中既有阿長對“母親”身份的渴望與誤認,也有魯迅“母親”角色的缺失與尋找。從這個角度介入《朝花夕拾》的整本書閱讀,魯迅的一些“別有用心”處才會彰顯出來。
作者簡介:王元貞(1976—),女,廣東省中山市翠亨村中山紀念中學一級教師,主研方向為文本細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