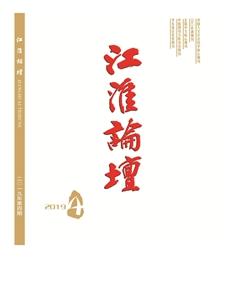朱熹對“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詮釋及其意蘊
樂愛國
摘要:對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歷來有不同詮釋,現代不少學者將該句視為對女性的歧視。朱熹《論語集注》將“小人”解為“仆隸下人”,將“女子與小人”解為“臣妾”,即家里的女仆與男仆,把孔子所言僅限于家的范圍。他還進一步闡述與臣妾的相處之道,要求對待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朱注不僅實現了從漢唐諸儒解“女子”為全稱者,到解“女子”為特稱者的轉化,而且實現了從漢唐諸儒的解讀把“女子”歸為小人而包含對女性的歧視,到進一步探討如何與“女子與小人”相處的轉化,消解了以往解讀中的歧視女性之意。朱熹之后的學者解讀孔子所言,重在闡述君子,尤其是有家國者和“女子與小人”的相處之道,實與歧視女性無關。
關鍵詞:朱熹;《論語集注》;女子;小人;臣妾
中圖分類號:B244.7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19)04-0082-007
《論語·陽貨》載:“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對此,歷來有不同詮釋,既有將“女子”解為全稱者,也有解為特稱者。[1]56-61現代有不少學者則將孔子所言視為對女性的歧視。近年來,朱熹《論語集注》將“女子與小人”解為“臣妾”的詮釋受到關注。錢穆《論語新解》說“此章女子小人指家中仆妾言。……因其指仆妾,故稱養”[2]464,把“女子與小人”解為妾侍和仆人。2015年出版的李澤厚《論語今讀》也采納朱熹注,并將孔子所言解讀為:“只有妻妾和仆從難以對付:親近了,不謙遜;疏遠了,又埋怨。”[3]339但是,這些解讀并未對朱熹的詮釋所具有的深刻內涵作深入的分析和發掘。事實上,朱熹《論語集注》的詮釋,不僅將“女子與小人”解為“臣妾”,而且由此進一步闡述與臣妾的相處之道,要求對待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這既與歧視女性無關,又對今人探討男女、上下如何相處,具有參考價值。
一、漢唐諸儒的解讀
《后漢書·楊震傳》載,東漢楊震通過講“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后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以言明“婦人不得與于政事”[4]1761。《后漢書·爰延傳》載,東漢爰延講“昔宋閔公與強臣共博,列婦人于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并且引孔子“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說:“蓋圣人之明戒也!”[4]1619顯然,楊震、爰延是以個別女性的行為導致災禍,而嫁禍全稱女性,而且還通過引述孔子所言表達對全稱女性的歧視。
東漢荀悅《漢紀》說:“夫內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為亂,自古所患,故尋及之。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性不安于道,智不周于物。其所以事上也,唯欲是從,唯利是務……是以明主唯大臣是任,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嬖請求之事,無所聽焉。”[5]493顯然,與楊震、爰延一樣,荀悅也是以孔子所言表達對全稱女性的歧視。
應當說,以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表達對女性的歧視,并不意味著該句本身包含了對女性的歧視,至多只能說明楊震、爰延以及荀悅將該句解讀為對女性的歧視。但無論該句是否具有歧視女性之意,這些事例至少可以說明,該句很容易被理解為對女性的歧視。現代有不少學者將該句解讀為對女性的歧視,或許也正由于此,因而也可說明,這樣的解讀與楊震、爰延以及荀悅是一致的,只是立場各有不同。
西晉杜預注《春秋左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說:“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6]3946顯然,這是依照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而言“婦女之志”。這里雖然只是講婦女,而沒有牽扯小人,但其中包含了對婦女的歧視。
南北朝時期,劉義慶《世說新語》載:“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劉孝標注:“孔子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劉尹之意,蓋從此言也。”[7]327這里把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中的“女子”與小人等同起來。
皇侃《論語義疏》解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不僅把“女子”與小人等同起來,而且還將“女子與小人”和君子對立起來,說:“女子、小人,并稟陰閉氣多,故其意淺促,所以難可養立也。……君子之人,人愈近愈敬,而女子、小人,近之則其承狎而為不遜從也。……君子之交如水,亦相忘江湖,而女子、小人,人若遠之則生怨恨,言人不接己也。”[8]472皇侃把孔子所言“女子與小人”和君子對立起來,實際上可以成為今人將孔子所言解讀為對女性歧視的重要理論來源。
唐代釋道世所撰《法苑珠林》說:“書云:仲尼稱難養者小人與女子。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已。是以經言:‘妖冶女人有八十四態。大態有八,慧人所惡:一者嫉妒,二者妄瞋,三者罵詈,四者咒詛,五者鎮壓,六者慳貪,七者好飾,八者含毒。是為八大態。是故女人多諸妖媚。”[9]694-695顯然,這是佛教借孔子所言表達對女性的歧視。
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卷二十八“小人九”門,在“小人從邇……難養”下注“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10]35,也是把孔子所言“女子”歸為小人一類。
需要指出的是,晚唐皮日休撰《陵母頌》,說:“孔父稱:唯小人與女子為難養也。夫女子之忠貞義烈,或聞于一時;小人之奸詐暴亂,不忘于一息。使千百女子如小人奸詐暴亂者,有矣。使千百小人如女子忠貞義烈者,未之有也。”[11]55顯然,皮日休反對把女子與小人歸為一類,因而不贊同孔子所言。然而,這恰恰說明他也把孔子所言“女子”解為全稱者,并歸為小人一類。
皮日休推崇孔子,稱“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則昌,舍之則亡”[12]2482。但是,他依照漢唐儒對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解讀,把該句中“女子”歸為小人一類,因而質疑該句。其實,皮日休完全可以由此批評漢唐儒對該句的解讀,而不是簡單地質疑孔子所言,但是他終究沒有走出這一步。
二、“此小人,亦謂仆隸下人也”
北宋邢昺《論語注疏》解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強調“女子”并非就全稱女性而言,說:“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6]5489顯然,這里將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中的“女子”,說成是“舉其大率耳”,不包括“稟性賢明”的女性,明顯不是就全稱女性而言。
南宋朱熹《論語集注》解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說:“此小人,亦謂仆隸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13]183顯然,朱熹把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僅限于家的范圍,“小人”指的是“仆隸下人”,“女子與小人”則指的是“臣妾”。漢孔安國傳《尚書》:“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6]542朱熹《孝經刊誤》引《古文孝經》所言:“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14]3211也就是說,“臣妾”即家中地位較低的男仆與女仆。
以“臣妾”解孔子所言“女子與小人”,可見程頤《程氏易傳》。《周易》遁卦:“九三,系遁,有疾厲,畜臣妾吉。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程頤傳曰:“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系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15]868這里既講“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又講“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明顯是以“臣妾”解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中的“女子與小人”;同時,這里又講“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把臣妾與小人區別開來。對此,朱熹說:“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腳手頭,若無以系之,則望望然去矣。”[16]1823也就是說,臣妾不同于與君子對立的小人。
關于《論語》中“小人”之意,楊伯峻《論語譯注》認為有二:一是指無德之人(20次),一是指老百姓(4次)。[17]317比如,注“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領導人的作風好比風,老百姓的作風好比草。”[17]186注“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做官的學習了,就會有仁愛之心;老百姓學習了,就容易聽指揮,聽使喚。”[17]264尤其是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說:“這個‘君子‘小人的含義不大清楚。‘君子‘小人若指有德者無德者而言,則第二句可以不說;看來,這里似乎是指在位者和老百姓而言。”[17]212其實,南北朝皇侃《論語義疏》就有類似的解讀,解“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說:“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也。”[8]88又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說:“君子,人君。小人,民下也。言人君所行,其德如風也;民下所行,其事如草。”[8]314這至少可以說明,《論語》中的“小人”并非全都是指無德之人,也有可能指普通百姓,或是“民下”。
朱熹《論語或問》說:“何以知其為仆隸下人也?曰: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唯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18]889按照孔子所言,對于“女子與小人”,不只是遠之,也要近之,因而不可能是指與君子對立的小人。
《周易》遁卦《象》:“遁,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程頤傳:“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15]867朱熹《周易本義》解道:“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19]114也就是說,君子對待小人,應當避而遠之,不以惡聲厲色,以免致其怨忿,而要“矜莊威嚴”“自守之常”,使小人知敬畏而“自不能近”。《孟子》載:“孟子為卿于齊,出吊于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朱熹注:“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13]247因此,朱熹《論語或問》認為,君子對待“為惡之小人”應當避而遠之,“唯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
然而,與此不同,孔子在講“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同時,又講“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對待“小人”,既要“遠之”,又要“近之”,還在意其“不孫”和“怨”。據此,朱熹認為,孔子所言“小人”并非“為惡之小人”,而應當是“仆隸下人”。同樣,孔子所言“女子”,與“仆隸下人”并列,應當是指與“仆隸下人”同等地位的女性,而且對待“女子”與對待“仆隸下人”一樣,既可“遠之”,又可“近之”,還要在意其“不孫”和“怨”。所以,朱熹在把“小人”解為“仆隸下人”的同時,把“女子與小人”解為“臣妾”,是有道理的。(1)
朱熹把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中的“小人”解為“仆隸下人”,把“女子與小人”解為“臣妾”,將其中的“女子”解為妾,為女仆,為特稱者,并非如漢唐諸儒解為全稱者;“小人”解為“仆隸下人”,為男仆,與“女子”為女仆相對應,并非無德之人。這樣,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講的是主仆關系,而不是君子與小人、男性與女性的關系,因而不具有把女性歸為小人的意味,不存在漢唐諸儒的解讀中所包含的對女性的歧視。
三、“莊以蒞之,慈以畜之”
孔子講“女子與小人”“難養”,具有“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的品性,只是為了表達對“女子與小人”的看法和情緒,還是另有其他目的、包含其他道理?漢唐諸儒的解讀停留于字面上的注釋,較多地討論為什么“女子與小人”“難養”。如上所述,皇侃《論語義疏》說“女子、小人,并稟陰閉氣多,故其意淺促,所以難可養立也”。與此不同,宋代諸儒的解讀,更加關注孔子所言包含的道理,從“女子與小人”“難養”、具有“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的品性,而進一步討論和“女子與小人”的相處之道。
陳善《捫虱新話》中有“女子小人自有固寵之術”一節,說:“孔子以女子、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此固中才庸主之所無可奈何者。然彼小人、女子,亦自有固寵之術。……然孔子但言其難養,而不言所以處之之術,何也?”[20]69顯然,關注的重點不在于“女子與小人”之所指,以及如何難養、為什么難養,而是要弄清楚“處之之術”。
程頤《程氏易傳》不僅把《周易·遁卦》與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結合起來,以“臣妾”解孔子所言“女子與小人”,而且又以該卦《象》所言“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闡發“遠小人之道”,認為對于小人不能“惡聲厲色”而致其怨忿,而應當“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從而遠離小人。但是,程頤并沒有就“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中的“小人”與“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中的“小人”做出明確的區分。
二程門人接受程頤對《易傳》“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的解讀,并運用于解讀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對孔子所言,謝良佐說:“此君子所以不惡而嚴也。”楊時說:“《易》之《家人》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故男女有別而不相瀆。《遁》之《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夫如是,則不孫之與怨遠矣。”侯仲良說:“女子小人不安分,故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尹焞說:“是以君子遠之,不惡而嚴。”[21]593需要指出的是,二程門人以“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解“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似乎又回到了漢唐諸儒的解讀,把“女子”歸為小人一類;但是,他們認為對待“女子與小人”應當“不惡而嚴”,實則是要探討和“女子與小人”的相處之道。
呂祖謙也把“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與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結合起來,說:“‘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僭,遠之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自然遠矣。《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要當思其所以處之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所難。蓋常人不惡則不嚴,茍欲其嚴,必作意而為之,亦如‘恭而安。尋常人恭敬者多拘束,才安肆則不恭矣。惟性情涵養,則自然嚴恭,茍內不足,則必待造作。”[22]73顯然,這也是通過解讀“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來探討和“女子與小人”的如何相處。
張栻解《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說:“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于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23]284認為對待“女子與小人”,應當取“和而有制”“不惡而嚴”的待之之道。
與以上討論不同,朱熹首先將孔子所言“小人”解為“仆隸下人”,將“女子與小人”解為“臣妾”,因而不以“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作為和“女子與小人”的相處之道,而是提出“君子之于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論語·為政》載,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孔子說:“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朱熹注:“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于己。”[13]58也就是說,對待百姓應當“莊以蒞之”。《論語·衛靈公》載:“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朱熹注:“蒞,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于內而不嚴于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13]168在朱熹看來,對待臣妾不僅要“莊以蒞之”,而且要“慈以畜之”。《孟子·梁惠王上》講“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韓嬰《韓詩外傳》說:“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24]98顯然,朱熹講“君子之于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與“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有著明顯的不同。
由此可見,在朱熹那里,孔子所言“女子與小人”即臣妾,不僅不是小人,而且君子對待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也不同于君子對待小人應當“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朱熹要求對待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強調家庭內部各成員之間相互尊重,包括對臣妾的尊重。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朱熹對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詮釋,不僅把孔子所言僅限于家的范圍,“女子”解為特稱者,“小人”解為“仆隸下人”,因而不同于漢唐諸儒解“女子”為全稱者而具有把女性歸為小人的意味;而且還從孔子講“女子與小人”“難養”、具有“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的品性,而進一步討論孔子所言包含的道理,討論和“女子與小人”的相處之道。也就是說,在朱熹看來,孔子所言不只是表達對“女子與小人”的看法和情緒,更在于講明一個道理,闡述和“女子與小人”的相處之道,尤其是,朱熹講“君子之于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與對女性的歧視并無關系。因此,朱熹的詮釋,不僅實現了從漢唐諸儒解“女子”為全稱者,到解“女子”為特稱者的轉化,而且實現了從漢唐諸儒的解讀把“女子”歸為小人而包含對女性的歧視,到進一步探討和“女子與小人”相處的轉化,消解了以往解讀中的歧視女性之意。
四、對后世的影響
朱熹《論語集注》對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詮釋,對后世影響很大。后來學者的解讀,大都不同于漢唐諸儒把“女子”歸為小人的解讀,而且主要是圍繞如何和“女子與小人”相處而展開的。
宋代趙順孫《論語纂疏》解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述朱熹的注釋,并引朱熹門人輔廣:“此正所謂不近不遠之間道理也。夫小人、女子雖有難養之情,在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蒞之,則有以銷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有以弭其多怨之意。”[25]474與此不同,錢時《融堂四書管見》則說:“不必專言仆妾。凡女子、小人皆然也,近之既不孫,遠之則又怨,將安所處乎?夫子此語正是欲人就其中思所以處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反己而求,庶乎其可矣!”[26]667明代劉宗周說:“女子小人難養,自古皆然。知此,便須得反身正物之道。區區謀所以養之之術,鮮克勝者。”[27]500錢時與劉宗周對“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解讀中,“女子與小人”并非只是指臣妾,而且強調對待“女子與小人”應當“反己而求”,“得反身正物之道”,與朱熹略有不同,但都是圍繞如何和“女子與小人”相處而展開的。
尤為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學者還認為,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是為統治者立戒。宋戴溪《石鼓論語答問》說:“圣人察于人情之際亦微矣,上而宦官宮妾,下而家人臧獲,皆是物也。遠之不可,近之不可,則亦難乎!其為養也,不求諸家而求諸身,得其所以養矣。”[28]99蔡節《論語集說》說:“女子、小人之情其望于人者,無有紀極,近之則狎侮生,遠之則猜嫌起,故難養也。圣人患之,為世立戒,使夫有國有家者,不昵不惡,則庶乎其可矣!”[29]696明代湛若水說:“人主之于臣妾,奈何?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必莊以蒞之,慈以畜之,明以斷之,斯為得御之之道矣。”[30]358又說:“人主御臣妾之道,誠不可不講也。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傳者云‘莊以蒞之,慈以畜之,然后能無二者之弊。……不莊不慈,可謂御臣妾之道乎?”[30]367明清之際,顧炎武說:“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顰笑有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以逾,何有外戚、宦官之禍乎!”[31]15王夫之解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引朱熹的注釋,并且說:“夫子曰:為人上者,制奸有道,懲惡有法,格頑有禮,教不能有恩,皆君子所不難也。唯妾媵之女子與左右之小人,服勞于上,上之所養也,而養之難矣。蓋其人安于卑賤而不知名義,近于君上則妄自尊高,而抑旦夕所不能無,禍患所不勝防,欲使畏我而懷我,難也。以其日在吾前而供使令,必且近之,嚬笑狎而不遜之習漸成,于是以其不可近而遠之,一旦失恩,而怨蘊于心矣。近之而又遠之,不遜之余怨不可戢也;遠之而又若近之,怨不忘而不遜抑加甚焉。權移于宮闈,而禍伏于弒逆,豈不難哉!”[32]934-935
清代方苞編選《四書文》,收入方應祥和王揆分別論“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之說。方應祥說:“御幸之難,鑒于意之倚也。蓋不孫與怨,固近之、遠之所自取耳。幸人之難養以此與?……夫能中喜怒哀樂之節,而遠近之節偕中矣;調不孫與怨之情,而天地萬物之情俱調矣。‘關雎所以嗣徽于好逑,‘虎賁所以庶常于知恤,皆謹其難以善吾養者也。君子宜何處焉?”[33]293王揆說:“圣人論女子、小人之難養,欲人主慎之于早也。蓋女子、小人養之不得其道,故近與遠皆有其患,慎之于早,而又何難之有哉?……師傅保母既掌后妃之教,而下逮嬪御,亦為之正其服位、禁其奇衺,而統之以內宰世婦之官,則侵竊惑移之患絕;宮正宮伯尊以大夫之秩,而賤及閽寺,亦為之選其德行、考其道藝,而領之以冢宰小宰之職,則左右近習之士端。嗚呼!此所謂女子、小人養之得其道。”[33]833
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歷撰《<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論》,說:“治國必始于齊家,而齊家又在于修身。身修則孚與威自然而合。待之以誠,而不使之怨;臨之以莊,而不使之狎,則家道永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矣。……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夫惟以威御之,則近而不至于不孫,以誠待之,則遠而不至于怨。雖然,所謂威者豈鞭撻棰楚之加,而所謂孚者豈煦煦焉徒事姑息為哉?自勝其私,語言可愛,行止可法,而不蹈非禮,則人自畏其威矣;自勉以仁,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則人自感其誠矣。此又反身之要,而治家者所宜先也。”[34]84-85直至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也認為,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此為有家國者戒也”[35]709。
五、余 ?論
如果不了解自漢代以來歷代關于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的不同注解,而只是借用現代漢語從字面上解讀,就很容易得出或接受類似楊伯峻《論語譯注》的譯文:“孔子道:‘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難得同他們共處的,親近了,他們會無禮;疏遠了,他會怨恨。”[17]276毫無疑問,在崇尚男女平等、反對性別歧視的今天,這樣的解讀會使人們以為孔子所言包含了對女性的歧視。應當說,這樣的解讀,在表面上類似漢唐諸儒因歧視女性而作出的解讀。但需要指出的是,現代學者做出這樣的解讀,不可能是要表達對女性的歧視,相反,往往包含了對這種歧視的反對,并且包含了對孔子所言的批評,實際上是對漢唐諸儒解讀的批評,因此在根本上不同于漢唐諸儒的解讀及其對孔子的追隨;而且,這樣的解讀,以為孔子所言包含了對女性的歧視,與朱熹以及其后大多數儒者的解讀更是大相徑庭。也就是說,現代學者把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解讀為對女性的歧視,完全不同于自漢代以來歷代的解讀。
當然,現代也有一些學者接受朱熹以及其后大多數儒者的解讀。唐文治《論語大義》注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引朱熹注“莊以蒞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并案:“《易·遁卦》三爻曰‘畜臣妾,吉。……修身齊家之道,惟在寬嚴相濟而已。”[36]303呂思勉作《釋“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指出:“《論語·陽貨》:‘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斯言也,讀者惑焉。人有善惡,男女一也,安得舉天下之女子,而悉儕諸小人?曰:此所謂女子,乃指女子中之小人言,非謂凡女子也。小人猶言臣,女子猶言妾耳,古臣妾恒并稱。”[37]660明顯是接受朱熹《論語集注》的注釋。蔣伯潛《論語讀本》說:“‘女子小人指宮闈的嬪妾、閹宦,和士大夫的婢仆而言。養,猶待也。見劉氏《正義》女子小人所以難對待者,和他們親近,必至不謙遜而弄出非禮的事情來;和他們離得遠了,又必至生怨恨也。”[38]714-715金景芳解《周易·遁卦》“九三,系遁,有疾厲,畜臣妾吉”,則引程頤傳,說:“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系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39]260此外,錢穆《論語新解》解“女子與小人”為“妾侍和仆人”,還說:“善御仆妾,亦齊家之一事。”[2]464李澤厚《論語今讀》雖然于2008年版注孔子所言為“只有婦女和小人難以對付:親近了,不謙遜。疏遠了,又埋怨”[40]527,但于2015年版則把“女子與小人”解為“妻妾和仆從”,采納朱熹注。
值得關注的是,杜維明說:“有的人常常談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但是我認為那絕對不是性別論說而是政治論說,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男人或女人,你作為政治領導在與他們相處時就要特別小心,不能太親近他們,讓他們說你濫用權力;又不能太疏遠他們,讓他們說你不體貼下屬。怎樣處理這種復雜的人際關系,維持你正常的生活,同時不被他們所蠱惑,又要他們幫忙維持你的行政運作。所以,這只是政治論說,不是歧視婦女的性別論說。”[41]695這段論述,將孔子所言“女子與小人”解為“沒有受過教育的男人或女人”,并將對孔子所言的解讀與“怎樣處理這種復雜的人際關系”相結合,并認為“那絕對不是性別論說而是政治論說”,實際上是對朱熹以及其后大多數儒者的解讀的一種發揮。
當然,現代不少學者將孔子所言“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解讀為對女性的歧視,而與現代人與人相互平等的理念對立起來,目的不只在于批評孔子的思想,還在于對那些依據孔子所言而歧視女性的批評。然而,人與人的平等和相互尊重,不能只是口號,也不能停留在口頭上對歧視女性的批評,更要落實到人與人的相處之道中去。朱熹對孔子所言的解讀,不僅將其中的“小人”解為“仆隸下人”,避免了把“女子”歸為小人的性別歧視,還進一步揭示孔子所言包含的道理,闡述和“女子與小人”的相處之道,要求對待臣妾,相當于今天所謂下屬、家政服務人員之類,“莊以蒞之,慈以畜之”。這不僅不能理解為歧視,而且很可以理解為一種尊重,這正是朱熹解讀的意蘊和現代價值之所在。
注釋:
(1)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勞悅強《從<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章論朱熹的詮釋學》說:“朱《注》謂‘此小人亦謂仆隸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莊以蒞之,慈以畜之,注文中先總說‘小人亦謂仆隸下人,意謂‘女子亦為‘仆隸下人,而下文所說的‘臣妾則分指‘小人與‘女子。注文中‘臣妾二字正從《尚書》孔《傳》中‘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的說而來,淵源有自,有根有據。”(勞悅強:《從<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章論朱熹的詮釋學》,《漢學研究》,2007年第25卷第2期,第141頁)
參考文獻:
[1]廖名春.孔子真精神:《論語》疑難問題解讀[M].貴陽:孔學堂書局,2014.
[2]錢穆.論語新解[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3]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中華書局,2015.
[4][南朝宋]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5][漢]荀悅,[晉]袁宏.兩漢紀(上)[M].北京:中華書局,2002.
[6][清]阮元.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2009.
[7]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3.
[8][梁]皇侃.論語義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3.
[9][唐]釋道世.法苑珠林校注[M].周叔迦,蘇晉仁,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10][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類集(貼冊6)[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1][唐]皮日休.皮子文藪[M].北京:中華書局,1956.
[12][唐]皮日休.襄州孔子廟學記[C]//傅云龍,吳可.唐宋明清文集(第1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13][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2.
[1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杰人,等.朱子全書(第2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15][宋]程顥,程頤.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4.
[16][宋]黎靖德.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7]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
[18][宋]朱熹.四書或問[M]//朱杰人,等.朱子全書(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19][宋]朱熹.周易本義[M]//朱杰人,等.朱子全書(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20][宋]陳善.捫虱新話[M].北京:中華書局,1985.
[21][宋]朱熹.論孟精義[M]//朱杰人,等.朱子全書(第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22][宋]呂祖謙.呂祖謙全集(第2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23][宋]張栻.張栻集(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5.
[24][漢]韓嬰.韓詩外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5.
[25][宋]趙順孫.四書纂疏·論語纂疏[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1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26][宋]錢時.融堂四書管見[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3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27][明]劉宗周.劉宗周全集(第2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28][宋]戴溪.石鼓論語答問[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9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29][宋]蔡節.論語集說[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0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30][明]湛若水.格物通[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6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31][清]顧炎武.日知錄集釋[M].黃汝成,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4.
[32][明]王夫之.四書訓義(上)[M]//王夫之.船山全書(第7冊).長沙:岳麓書社,1991.
[33][清]方苞.四書文[M]//王同舟,李瀾.欽定四書文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
[34][清]愛新覺羅·弘歷.樂善堂全集(卷2)[M]//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3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5][清]劉寶楠.論語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90.
[36]唐文治.論語大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7]呂思勉.釋“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C]//呂思勉.論學集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38]蔣伯潛.四書讀本(下)·論語讀本[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2013.
[39]金景芳.周易講座[M].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87.
[40]李澤厚.論語今讀[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41]杜維明.杜維明文集(第5卷)[M].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
(責任編輯 ?吳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