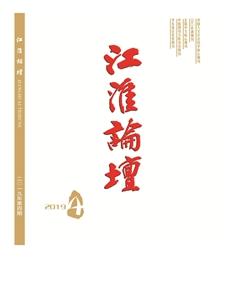王羲之的北伐態度及其人物評價
祁小春
摘要:公元351至355年,王羲之正在會稽內史任上,在此期間,殷浩率領東晉軍隊開始了大規模的討伐北方異族的北伐戰爭。對此時的東晉北伐,王羲之持消極反對態度,并極力上書阻止。王羲之對殷浩北伐所表明的態度和主張,以及為此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是其一生中對政治的最大一次關注與介入。王羲之在北伐問題上所持的立場與態度,引發了后世的種種議論,因這一問題與王羲之的政治主張、處世態度以及人生觀等關系密切,是否能夠公正客觀地看待與評價,其意義甚大。本文就王羲之對北伐所表現出來的態度、立場及其原因等問題加以討論。具體而言,就是將王羲之置諸當時的門閥士族社會,就其生活環境、政治主張、處世態度等多方面的相關問題試作考察,以便了解當時的一些重要歷史場景,還原王羲之的一些真實人生圖景。
關鍵詞:王羲之;北伐態度;人物評價
中圖分類號:J292.23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1-862X(2019)04-0154-008
一、東晉永和時期的歷史背景和北伐形勢
東晉在江南建立政權以來,遼闊的華北大地成為北方匈奴、鮮卑、氐、羌、羯等胡族以及部分漢族政權之間交替征戰的舞臺。在此期間,匈奴族的劉氏前趙政權被同屬其族的石氏勢力所滅,誕生了后趙石氏政權,其勢力范圍之廣,遍及整個華北區域。當時與石氏后趙并存于北方的其他異族勢力有鮮卑族慕容部(今東北地域)、鮮卑族拓跋部(今山西北部)、漢族張氏政權(今甘肅地域)等。永和五年(349)四月石虎(295—349)亡,其十余子為繼承帝位而相繼展開爭斗。對于東晉政權而言,趁華北之亂,一舉北伐,收復故國山河,正是不可多得的絕佳時機。史載“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1]2039,可見當時東晉仁人志士之心態與志向。此時之東晉,庾亮(289—340)弟庾翼(305—345)、庾冰(296—344)二人掌握重兵。庾氏是外戚,效忠晉室,故尚無大事。
至于北伐,東晉并非無有此志,而且也陸續有所動作:庾氏兄弟都為北伐做過準備,尤其是庾翼,曾有過率軍征伐的不小舉動,盡管庾氏兄弟之北伐另有其目的。[2]123-124建元元年(343)七月,東晉朝廷下詔經略中原,庾翼于是率部北伐。正當此時,王羲之特意呈表朝廷,表示極為關注庾氏的北伐進展,反映了他的支持態度。(1)此次北伐,庾翼雖然也曾有過“東西齊舉”之勢,然終因出師不利,無功而返。其時又逢康、穆二朝新舊交替之際,其事遂寢。未久,外鎮武昌的庾翼于永和元年(345)病死。臨終之前,上表薦請其子繼任,朝廷未允,而以桓溫(312—373)為安西將軍,假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1]193-205,荊州刺史,代掌庾翼上游軍事[3]353-354。如此一來,庾氏經營多年的基業地盤,悉數轉入桓氏,東晉軍事大權也從庾氏漸歸桓氏,在東晉軍事地理版圖上,長江之間又重新形成了上游荊州威逼下游建康之勢。永和二年(346)桓溫率周撫等討西蜀成漢國,歷兩年而蜀地全歸東晉。于是長江上游的廣闊地域,亦盡納入桓溫勢力范圍。永和四年(348) 桓溫以平蜀之功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威名大振。桓溫勢力迅速坐大,引起朝廷恐懼,為了對抗桓溫勢力,會稽王司馬昱(320—372)起用揚州刺史殷浩參綜朝政,以抑制桓溫勢力,桓對此不滿。與此同時,“華北之亂”出現,朝野上下北伐的呼聲極高,紛紛主張趁機收復故國失地。桓溫趁勢上表要求北伐,未被朝廷采納。
永和五年(349)石虎之死,正是興師北伐的絕好機會。征北大將軍褚裒(303—350)上表請伐趙,于是朝廷加封褚裒為征討大都督,都督青、揚、兗、徐、豫五州諸軍事。征討之初尚屬順利,然褚裒才略不足,結果慘敗。褚裒回朝以后不久郁憤而死。永和六年(350),后趙局勢更加混亂。正月,石虎養孫漢人石閔(?—352)殺后趙帝石鑒以自立,改國號為大魏,恢復冉姓,史稱冉魏。冉魏建立后,后趙許多將領割據一方,并不聽從冉命。冉閔大量殺戮胡族,華北地域陷入極度混亂狀態。冉魏還與東晉取得聯系,請求派兵共同討伐胡人。對于這一突如其來的形勢變化,東晉打算再次北伐。于是朝廷任命揚州刺史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卻未用桓溫。永和七年(351)冉魏諸將領紛紛向東晉獻城投降,其中有豫州牧張遇(生卒年不詳)。此后大將姚弋仲(280―352)也派遣使者請降,姚弋仲與其子襄(生卒年不詳)皆受晉封。姚為羌人,部眾皆善戰,若善將安撫,對東晉北伐將十分有利。十二月,桓溫“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眾四五萬。”[1]2569此行固為北伐,也有顯彰聲威、恫嚇建康之意。中朝聞之驚恐,會稽王司馬昱以書阻勸,桓亦以時機未成熟而罷。雖然朝廷決定由殷浩擔當這次北伐重任,但面對桓溫咄咄逼人的勢頭,殷浩心中大概也頗存矛盾:一方面,他懼怕桓溫氣勢,曾萌去意,以避桓勢,后被王彪之(305—377)勸阻,乃強撐面子勉力為之,此中隱情亦不可不察。(2)另一方面,殷浩覺得今后若與桓溫抗衡,須有實績方可樹立聲望。因此,殷浩亦頗愿借北伐以建立功業,用以自固,也當屬實情。而東晉當權者主要是想借助殷浩以抗衡桓溫。從當時個中情勢觀察,殷浩已身不由己地陷入了矛盾的旋渦之中。
二、王羲之對北伐的態度
當是時,王羲之認為不宜北伐,尤其對殷浩率軍北伐表示擔心,他的主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他認為客觀條件不成熟。北伐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規模戰爭,為此必須準備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備征用,而以當時東晉國力,并不具備這種條件。如果強行北伐,則勢必大大加重江南各地的各種賦役,在一些情況本來就不太好的地區,例如當時東晉糧倉的會稽地區,相繼遭受到災害和饑饉的困擾,人民更無法承受賦稅負擔。(3)
第二,他認為“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1]2094。在大敵當前,壓到一切的就是需要內外團結,只有如此方能克敵制勝。然而這次北伐是在殷浩、桓溫權力斗爭的背景之下出現的,是在毫無充分準備的狀況下做出的匆忙決定,因而取勝把握不大。
第三,他認為北伐之任,帥非其人。雖然王羲之先后曾支持過庾翼、桓溫北伐,但是此時他卻認為不宜,因為殷浩并不具備桓溫那樣的軍事才略和統軍作戰能力,即《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后略稱“本傳”)所言“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者也。對于殷、桓的爭奪與對抗,王羲之已預料到殷浩非桓溫對手。
基于以上考慮,王羲之此間寫信給會稽王司馬昱力陳不宜北伐:
又與會稽王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愿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于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自非圣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于眾,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后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余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征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嘆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愿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于反掌,考之虛實,著于目前,愿運獨斷之明,定之于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系,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后機,不定之于此,后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愿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1]2098-2097
此外他還連續寫信給殷浩、荀羨,竭力勸說殷浩與桓溫和解,而殷未能聽從,這些都可以察知彼時王羲之對北伐的基本態度以及焦急的心境,這些書簡大部分收于《晉書》本傳。
桓溫與殷浩,二人自幼齊名,又各有擅長。殷浩為出色的清談大家,有玄談的智慧而無務實的才干。桓溫則是東晉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殷浩的北伐,借用王羲之評謝萬北伐之語,就是“違才易務”。桓溫、殷浩都是王羲之的好友,以個人關系來看,王羲之更近殷浩。殷、王有此關系,應和他二人在庾府曾是同僚有關。以當時政界派系而言,王羲之屬殷浩一派。庾亮生前稱王羲之有“鑒裁”[1]2094,應包含其有知人之鑒識。王羲之對自己的幾位好友確實看得很清楚。比如以將才治事而論,王看好的人物是庾翼、桓溫、謝安,而不是殷浩、謝萬,事實也都證明他的判斷基本準確。可貴的是,他并不因親疏關系而改變看法,這可從對待殷浩、桓溫的北伐態度看出。所以在探討王羲之對殷浩北伐所持態度之背景時,這一點也應該被考慮進去。
如前所述,王羲之對殷浩北伐所表明的態度和主張,以及為此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可以說是他的一生中對政治的最大一次關注與介入,此時也是其仕途生涯中最活躍的一段時期。王羲之之所以介入政治,除了作為士大夫所具有的憂患意識和強烈責任感外,個人利益的因素當然也不能說一點沒有。作為殷浩派羽翼(4)的王羲之,無論如何都不愿意看到殷浩因北伐失敗而失勢。《晉書》本傳所收王羲之與殷浩書的主旨,不外是為了國家、為了殷浩本人也為了王羲之自己,希望殷浩與桓溫和解,停止北伐,如此殷浩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于當權。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愿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征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1]2095
遺憾的是,殷浩并沒有接受王羲之的忠告。其實,就當時的客觀形勢來看,這種忠告也只不過是一種幻想而已,不太可能實現。結果是,殷浩在北伐中因為不能安撫降將,致使張遇、姚襄反叛,終以慘敗而歸,于永和十年(354)被廢為庶人。殷浩失勢后,王述接任揚州刺史,王羲之與王述不和,遂于永和十一年(355)稱病辭官,結束了其仕途生涯。
三、對王羲之北伐態度的評價
(一)關于肯定與否定的兩種評價
在王羲之的政治主張中,最有爭議的大概莫過于其反對殷浩北伐時提出的所謂茍且偏安之論。在此問題上,后世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是不齒而加以否定,一是嘉許而予以肯定。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從歷史的立場研究東晉問題者,多為否定派,其中以歷史學家居多;從文化藝術(書法)角度研究王羲之者,則多為肯定派,其中以藝術史論學者與書法評論家居多。后者的基本觀點體現為:在全面贊揚充分肯定王羲之書法藝術之偉大的前提下,對于其他言行事跡普遍采取包容態度,一如唐太宗作“盡善盡美”的詮釋那樣,在對待殷浩北伐的問題上,一般不做褒貶評價,甚至大多持肯定態度。關于此派觀點,已多見于各類相關的文化、藝術或書法史論研究。(5)否定派的著眼點,則往往超出王羲之個人范疇,而是從歷史、階級和民族的立場看問題。故在殷浩北伐問題上,多不以王羲之為然。其中最有代表性者,乃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的觀點,王夫之《讀通鑒論》卷十三中有如下論述:
羲之言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業已成乎區區之勢,為天下寒心,而更以陵廟邱墟臣民左衽為分外之求,昌言于廷,曾無疚媿,何弗自投南海速死,以延羯胡而進之乎?宋人削地稱臣,面縛乞活,皆師此意,以為不競之上術,閉門塞牖,幸盜賊之不我窺,未有得免者也。
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非有懷奸誤國之心也,乃其侈敵之威,量己之弱,創朒縮退阻之說以坐困江南,而當時服為定論,史氏侈為吁謨,是非之舛錯亦至此哉!
嗚呼!天下之大防,人禽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即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于戴異類以為中國主,況僅王導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奸,不必深察其情,而繩之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蔡謨、孫綽、王羲之惡得不與汪、黃、秦、湯同受名教之誅乎?[4]
在王夫之看來,王羲之等懼北胡而求保全江南的偏安想法,實開后世乞活茍安之先例,為南宋偏安提供了可以倚恃的理論依據。故擬之與秦檜同類而不齒,言詞頗為激烈。很顯然,這一種意識明顯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王夫之寧愿認可桓溫逆篡晉祚,也不容忍胡族入主中原的觀點,就極為典型。在王夫之看來,他認定東晉是有能力贏得北伐勝利的,故有此過激之論,唯所恨者,是東晉政權能為之而不作為,一再延誤北伐戰機,以及滿足現狀的茍安策略。然而,王夫之顯然將是否應該與能否贏得北伐這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混同而論,卻不曾考慮萬一北伐潰敗,則將導致胡人長驅直入,最終導致東晉全土淪陷。關鍵是這種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其實,王羲之擔心的也正是這一點,因此在假定東晉北伐必勝的前提下,否定王羲之的主張,我們認為是有失客觀公正的。
后世史學家如近代的呂思勉、王仲犖等,亦承王夫之觀點,而尤以呂氏最為嚴厲。呂思勉斥王羲之“本性怯耎之尤,殊不足論”,并認為王羲之勸殷浩、桓溫和解一事,也無非是為茍安計,因為實際上桓溫已無可能同殷浩和解,所以也不能罪怪殷浩之不從王羲之忠告云云。(6)
(二)關于王羲之反對北伐的原因探究
筆者以為,對于北伐問題應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社會原因,一是個人原因。
先論前者,即社會原因。東晉北伐,屢征不利,自當有其更深層的原因所在。陳寅恪曾分析總結了“南朝北伐何以不能成功”的原因,認為有四點:“一為物力南不及北;二為武力南不及北;三為運輸困難;四為南人不熱心北伐,北人也不熱心南人的恢復。”[5]236第一、二點正是王羲之據以反對殷浩北伐的理由所在,第三點也應屬此范圍。至于第四點,亦不須諱言,這在王羲之等當時的南渡北人士族心中,確有此情。陳寅恪說,“南渡人對于北伐的態度,可以王羲之為代表”,并認為王羲之提出的“‘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代表了南渡北人對北伐的一般看法”[5]236,這就是說王羲之等并非完全反對北伐,而是覺得時機尚未成熟。當然,也不能排除王羲之等南渡的原北方士族,在南渡以來基本安定的環境之中,欲保持現狀而心存茍安之念。至于王羲之本人是否有此想法,不得而知,也不重要。問題是,作為局中人,即便心存此想亦不足為奇,不應上升到民族大義的高度予以苛責。從當時的客觀情況來看,南朝貴族的生活環境,的確比戰亂頻仍的北方要安定優裕得多,士族不愿北還,即有此客觀理由存在。陳寅恪在論述當時南北社會的差異時,分別從經濟生活、社會習俗等各個方面,論證了“南北朝有先后高下之分,南朝比北朝要先進”之事實。[5]325東晉自渡江后初步穩定,到了永和時代,社會各方面尤其是經濟生活方面,已經相當安定富足,對于南渡的原北方高門大族來說,尤其如此。王羲之與謝萬信中曾說道:“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余,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1]2012這正是王羲之等南渡的原北方士族們樂不思蜀生活的真實寫照。
在北伐問題上,王羲之是反對殷浩而支持桓溫的,因而殷、桓的北伐之作為及結果,自然會影響到后人對王羲之的評價。一般認為,因殷浩不聽王羲之勸阻而強行北伐,后遭失敗,因而認為王羲之意見正確。這一點確實不能否認,但也應避免以成敗結果評人論事。盡管東晉北伐的領軍主帥適任與否很重要,但并非決定北伐成敗的全部因素。從這場規模龐大的戰爭來看,還有不少其他因素甚至是極為偶然的因素左右戰局及其結果。比如將帥間的人際關系導致指揮失靈以致倒戈,又比如因某些戰術性失誤而導致全局潰敗。此外由于桓溫、殷浩的不和,致使前者在一方觀望北伐,造成后者討伐力量的相對不足,也是敗因之一。呂思勉亦認為“殷浩之敗,實敗于兵力不足”,“知姚襄等之不足恃而用之者,乃不得已也”[6],總之北伐之敗,并非全由殷浩無能所致,而以桓、殷北伐之勝敗結果評判王羲之主張的是非功過,也是不夠客觀的。
次論個人原因。王羲之本無意于政治,此志朝野皆知,可以說他是游離于權力中心之外的一種另類存在。因而他的意見對于東晉當權者來說,會在多大程度上予以重視?對于東晉政權的最終決策能產生多大影響?這些問題不能不加以考慮。盡管王羲之與當時主政者個人之間的關系極其密切,但其影響力相當有限。之所以如此,當有其個人原因。筆者以為,欲對王羲之作較為客觀的評價,不應單純地因人論事或因事論人,而應結合東晉尤其是永和年間的世風與人物之特點特征,做綜合考評。田余慶論及永和時代及永和名士時說:“永和以來長時間的安定局面(7),使沈浮于其間的士族名士得以逐漸遂其閑適。他們品評人物,辨析名理,留下的佚聞佚事,在東晉一朝比較集中,形成永和歷史的一大特點。”[2]164其間士族名士特征,田氏總結為“既無避世思想,一般又是重恬適而輕事功,無積極處世態度”[2]167。實際上,也正如田氏所論,在東晉名士中“重恬適而輕事功”的風氣極為普遍,也最具有代表性,此乃當時士族名士所共有的人生觀和價值取向。在永和政壇上,當軸人物如簡文帝、殷浩、謝萬等,同時也是名士階層中眾望所歸的領袖人物,他們是當時重恬適、輕事功的清談名士集團的代表人物。《世說新語》文學篇記謝萬嘗作《八賢論》,劉注謂其文之旨為“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可見謝萬的“處優出劣”輕視出仕的處世態度,甚至超過了名士孫綽的“出處同歸”之論。在隱逸出世方面,王羲之的人生觀比較接近謝萬,這從王羲之退官后寫給謝萬的書簡中大談隱逸,可見二人意氣相投,實乃同路之人。[1]2102也正因為如此,王羲之才極力反對桓溫使謝萬帶軍領兵,認為是“違才易務”[1]2087。以庾翼、桓溫、謝尚等為代表的出將入相之材,他們的處世觀則與重恬適輕事功的王羲之、謝萬略有不同,其特征是,既重風流玄談,亦不廢事功。此兩類名士雖有差異,但并非互相排斥。因為士族之間的主流價值觀,是被雙方所接受的,所謂差異唯在各自的偏重程度之不同而已。對此田余慶曾論云:“東晉當軸人物,一般都有水平不等的玄學修養,否則就難于周旋士族名士之間。”[2]166這應該是符合實情的。以類別之,王羲之應屬重恬適而輕事功的名士之列,盡管他并不善于玄談,有時甚至批評,如冶城對話[3]115,即其明證。但王羲之并未否定玄學,非但如此,有時甚至十分仰慕清談,這也是事實。(8)重要的是,王羲之對于事功毫無興趣的人生觀,就注定了他與那些有經國濟世大志之實干者有其本質上的不同。
四、對王羲之這一歷史人物應如何評價
呂思勉斥王羲之“本性怯耎之尤,殊不足論”[6]202,此評頗關王羲之這一歷史人物的正負面評價。因為王羲之的政治主張與其人生思想和處世哲學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所以能否正確客觀地評價王羲之,最為重要的還是應該對其人本身做詳細的分析與考察,即將王羲之置諸東晉門閥社會的大環境之中,他究竟屬于哪一類名士?
若對東晉名士做進一步分類,學界一般分成以下四類:慕道、清玄、事功、學術,而王羲之總的來說應歸“慕道”一類,早在南朝梁時,陶弘景即已稱王羲之“頗亦慕道”[7],此為比較客觀的評語。另外顏之推亦評云:“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8],此評語亦值得玩味。蓋蕭散最與事功相抵觸,亦與學術學問無關。“蕭散之人”即屬道中之人,此類型的名士在人生價值觀念上,一般只在意于活得自在愜意,盡管他們也有能夠成就經世濟國偉業的能力、地位、條件和機會,但卻并不愿傾力為之。其實,在老莊思想的強烈影響下,向往遁世隱逸、慕求仙道的人生觀,于當時的豪族貴游之間相當流行,因為實踐遁世隱逸是他們超越現實世界、走向神仙世界之途徑與手段,而到達神仙世界的彼岸,才是他們的終極目的。所以這類追求蕭散慕道的名士,對自己的人生信仰是懷有相當的優越感的,也令一般人羨慕。蕭散慕道一派名士的趣尚發展到極致,便導致了視事功為鄙俗風氣的出現,甚者乃至廢棄。例如,在對待行政庶務方面,如果說王羲之在任期間尚能恪守職責的話,那么其子王徽之在官時則完全是優游廢務,無心綜事。(9)因此在這一點上也可以說,蕭散慕道派甚至還不如清玄一流人物,后者雖好談虛玄但并非不務事功。如殷浩、謝安等同屬清談名士,他們并沒有像王徽之那樣走火入魔,盡廢事功;如果說二人在事功作為方面有何不同的話,那也只是結果意義上的殷浩失敗而謝安成功而已。
永和時期,蕭散風流、談吐玄言為士族名士之間流行的一種風氣。但是在門閥政治制度之下,本族之中必須有人出仕以保障家族利益。此間的庾翼、桓溫、謝尚以及王氏族中之俊杰,都是出色的實干家,在政治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會稽王司馬昱、殷浩、謝萬等人雖以風流玄談負盛譽,但在政治上卻未能有太大作為。這些確實是事實,然而后人則多以經世致用的價值觀念評定永和人物,以致足可稱道者也就十無一二了。清李慈銘謂“人材莫衰于晉”[9],即代表了這種意見。
必須注意到,當時名士中能濟世者不一定不好玄談,而擅玄談者又未必無經世才干。崇尚玄談在當時士族名士層屬于主流文化,不重事功為名士的一般思想,殷浩即屬此類,而且被當時名士奉為玄談的領袖人物。庾翼、桓溫雖以“寧濟宇宙”自負,揚言殷浩只能束之高閣(10),殷浩之敗也證明了庾言之不謬,然此正見庾、桓輩于殷浩情結之深。蓋以己之長抑人之短,人之常情耳,庾所以作此豪言,正說明在當時名士文化環境的背景下,應有令其自慚不及殷浩之處。(11)在經營實務方面,殷浩確實不敵庾、桓英略,這點歷史已早做出結論,而后人多以成敗論人事,則有失兼察。若殷浩真屬無能之輩,以王羲之知人善鑒之銳利,當察而遠避之矣,何以相契若此?王羲之一向敬重殷浩,曾贊浩“思致淵富”[3]195,自不待言,他主要佩服的當然還是殷浩的談辨,是其仰慕主流文化的一種心理反映。人各有志,于魏晉時代尤其如此,正不必以國家民族大義等價值觀繩準之。當是時,士族有存志于經世者,亦有自愿遁世者;有熱衷治事理政者,亦有向往閑適優游者。在名士中此兩類人生觀并非相互排斥,往往兼而有之,所不同者,唯在能力高低而已。謝安則是少有的全能代表,他在世人心目中是一位理想的晉人名士代表,被后世高度贊揚。筆者嘗想,倘若謝安不喜清談優游,又不縱情山水,唯以淝水一役而功垂后世,則在后人眼中,他恐怕也不過是一位能臣而已,于后世未必能獨享英名若斯矣。
王羲之的智慧在于知人察世,在政壇上,他雖屬殷浩派系,卻能看出浩非國器干材,亦非桓溫對手。他認為朝廷對殷浩委以北伐重任并以之抗衡桓溫,無異于自擇敗途,所以每為規勸。王羲之與殷浩從本質講應同屬一類名士,皆非扶危濟世之棟梁偉器,所不同者,前者有自知之明,而后者卻無。但是反過來也可以說,殷浩尚存經世之懷,而羲之則本非廊廟之器,這從殷浩致書羲之敦請出仕為社稷蒼生效力,而羲之答書拒之可以看出。從這層意義說,若以經世濟國的愿望與才干而論,王羲之不比殷浩強多少,更無法與庾、桓及王氏家族的王允之、王彪之等同日而語。田余慶評曰:“王羲之在事功方面與王允之不同,并非經國才器”[2]163,持論公允。毛漢光在《中古大族之個案研究──瑯琊王氏》一文中,按政治行為將王氏人物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無為型,二是積極型,三是因循型。王羲之父子四人,羲、獻被列入因循型,徽之、凝之則置諸無為型。據毛氏解釋因循型:“這類士人政治行為是兢兢業業,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隨波逐流,憂讒畏譏,但并非完全不做一點事情,有時做一點,大部分時間皆蕭規曹隨,因循不變。”[10]毛氏認為,此三種類型可視為王氏對現實社會的三種反應,應該說毛氏界定的因循型,在很大程度上是適合于王羲之的。王羲之不喜經世,然他并非毫無經世才干,他的消極乃其人生觀使然。不管后人如何看待此種人生觀的價值,至少在當時名士中此種人生觀是令人羨慕的,向往蕭散優游的隱逸生活方式,如同一些士人希望出仕以成就“寧濟宇宙”之偉業然,乃其人生之追求。總之,了解與分析當時士族名士具有何種人生觀、屬于何種類型的人物等,是客觀評價王羲之的基礎。
正如《晉書》本傳所載,王羲之不堪屈居于揚州刺史王述治下,再加上王述為自己所受前辱而施加報復,時常有意借故刁難,于是王羲之遣人前往朝廷,提出把會稽郡從揚州獨立出來置為越州的要求。關于要求分會稽為越州一事,歷來多被認為是王羲之一氣之下提出的一個極不近情理的要求,但結合當時情況看,似并非全是無理取鬧(12),后因種種原因,這一建議遭到時賢譏笑,令他深懷愧嘆。永和十一年(355)三月,王羲之在父母墓前祭奠告靈,發誓從今以后絕意仕途。隨即稱病,辭去會稽內史,隱居浙東。(13)據《晉書》本傳稱,當時朝廷以王羲之誓苦,不再征召他出仕了。這意味著他永遠訣別了官場,其在東晉政壇能夠發揮較大影響力的時代,也由此而宣告結束。
小 結
本文參考借鑒了史學界前輩學者的許多寶貴意見與重要觀點,并結合筆者自己的研究,大致梳理了王羲之對于北伐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態度與立場,探討其深層的原因所在。王羲之這個案例具有極其典型意義,因為王羲之實際上代表了東晉永和時代大部分士族名士的基本態度與立場。當我們詳細了解了王羲之生活的那個時代環境,就不難理解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為什么會有那樣的人生觀。通過以上的考察分析,我們對王羲之這一歷史人物有了更加具體的清晰的認識與理解,為如何客觀公正地評價王羲之,提供了必要的事實參考。
注釋:
(1)《右軍書記》361帖:“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克定有期也。羲之死罪死罪。”“稚恭”乃庾翼字,故此帖當書于建元元年(343),這也是王羲之并非反對北伐的主要證據之一。見張彥遠《法書要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74頁。
(2)《資治通鑒》卷九十九永和七年條:“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 殷浩欲去位以避溫……”見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3120頁。
(3)《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時東土饑荒,羲之則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憂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除此之外,王羲之曾建議恢復加強漕運、谷倉管理制度,以利賑災救民,他還為賑災而采取具體的措施,禁止以米釀酒等。另外,王羲之還建議朝廷采取具體措施防民流逸等(均見《王羲之傳·與謝尚書》),見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094-2097頁。
(4)《資治通鑒》卷九十八晉紀二十永和四年條:“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為吳國內史、羲之為護軍將軍,以為羽翼。”見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3084頁。
(5)如雒三桂《王羲之評傳》一書就比較有代表性。作者在論及對王羲之北伐態度時云:“當時,關于是否北伐收復中原,東晉朝廷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嚴守邊境,伺機北進以恢復中原,這一派以庾翼、桓溫、殷浩為代表,在朝廷之中屬于主戰派。另一派則以王羲之、孫綽等人為代表,主張量力而行,根據當時東晉的實際能力,采取保守政策退居江南,依靠長江這樣的天然屏障來保護江南……他(筆者注:孫綽)指出,不僅江東與北方在地理形勢上有天然的分隔,而且經過數十年之后,遷居到南方的北方移民已經在南方安家立業,客觀上已經很難讓他們拋棄已有的一切而重新回到動亂的北方。” 見雒三桂《王羲之評傳》,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149頁。
(6)如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第五章第一節“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與東晉王朝的建立”,論及殷浩北伐失敗:“東晉的世家大族本來就不主張北伐,至此北伐遇到挫折,大地主瑯邪王羲之(王導從子)便主張不但應該放棄河南,就是‘保淮之志,也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見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頁。呂思勉在《兩晉南北朝史》中指出:“殷浩之敗也,王羲之遽欲棄淮守江。羲之本性怯耎之尤,殊不足論。其與殷浩書謂當時‘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又與會稽王箋,謂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征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亦近深文周納,危辭聳聽。”“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浩不從。溫與朝廷,是時已成無可調和之勢。晉朝欲振飭紀綱,自不得不為自強之計。羲之性最怯耎,其說浩、羨與溫和同,亦不過為茍安目前之計,然亦未能必溫之聽從也。而世或以不能和溫為浩罪,則瞽矣。”又論:“當時不欲出師者,大抵養尊處優、優游逸豫,徒能言事之不可為,而莫肯出身以任事,聞浩之風,能無愧乎?”此論所指,殆亦斥羲之也。見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204頁。
(7)關于東晉永和時期何以能出現較為安定局面的原因,田余慶的說明是:后趙石氏盛極而衰,對南方壓力大減,是其外因;庾衰桓盛雖成趨勢,但桓尚未能完全代替庾氏發揮其作用,士族門戶的競爭正處在相持與膠著狀態中,一時高下難判,此是其內因。田氏還指出“就連呼聲最高的北伐,也被這種膠著狀態的政局牽制,表現出不尋常的復雜性”。以“膠著狀態”比喻永和政局之相對安定,十分確切。見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168頁。
(8)《世說新語》言語篇七十: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費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15頁。
(9)王徽之亦道中人。《真誥》卷二十“翼真檢”二“真冑世譜”許邁傳載其“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徽之)乃修在三之敬”,可知在王羲之諸子中,隨其父慕道信教者不惟凝之,獻之,徽之亦是其類也。據《世說新語》簡傲篇十一載“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劉注引)《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又同篇十三記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按,《晉書》王羲之傳附徽之傳亦載其事。王徽之在桓沖幕下任職時“蓬首散帶,不綜府事”。桓沖批評他在府日久,也應該做些正事(料理)了。徽之卻聞之先是高視而不答,后又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了事。即使是當時之人,對于王徽之的“雅性放誕,好聲色”之“傲達”亦不能完全接受,只是“欽其才而穢其行”(《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附徽之傳)而已。由這些均可見其慕道廢事的程度之甚。見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013頁。
(10)《世說新語》豪爽篇七“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條劉注引《漢晉春秋》:“(庾)翼風儀美劭,才能豐贍,少有經緯大略。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埽蕩群兇之志。是時,杜乂、殷浩諸人盛名冠世,翼未之貴也。常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清定,然后議其所任耳!其意氣如此。唯與桓溫友善,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翼輒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沔,將謀伐狄,遂次于襄陽。”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19頁。
(11)庾翼雖謂殷浩“宜束之高閣”,亦不能說明其無欽羨殷浩之心。《晉書》殷浩傳載:庾翼“相謂曰:‘深(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托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余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皆可以見。見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044頁。
(12)田余慶認為王羲之作此請“說明會稽等郡有可分之勢,此議在東晉雖未成為事實。但宋孝建元年(454年)割會稽五郡為東揚州,實際上實現了王羲之先前之議”。見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頁。
(13)據《金庭王氏族譜》所收隋沙門尚杲撰《瀑布山展墓記》引智永語:“晉王右軍乃吾七世祖也,宅在剡之金庭,而卒葬于其地。”古剡即今浙江嵊州,若智永所述可信,王羲之晚年當隱居于此。又袁六橋《王羲之的晚年行蹤》、張忠進《王羲之在古剡金庭遺跡考》二文均持此論。見山東臨沂王羲之研究會編《王羲之研究》,山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122頁。
參考文獻:
[1][唐]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3][南朝]劉義慶,著.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M].北京:中華書局,2011.
[4][清]王夫之.讀通鑒論[M].北京:中華書局,1975:424.
[5]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M].合肥:黃山書社,1987.
[6]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日本]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真誥校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496.
[8][南北朝]顏之推.顏氏家訓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93:570.
[9][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M].北京:中華書局,1963:211.
[10]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390.
(責任編輯 黃勝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