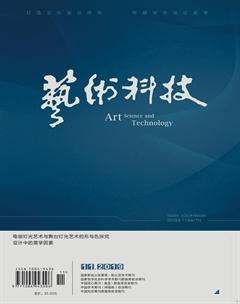藝術永遠在路上
徐怡恒
摘 要:藝術是什么?從發生過程、表達形式、傳播目的等不同角度進行描述,會得出不止一個定義。而對于任何一件藝術作品,我們都無法用某一定義去描述,晦澀又不具體。品畫作詩文也好,賞音律吟唱也罷,沒有同一評價模板可以套用。藝術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它本身就是個矛盾體,沒有絕對的是與非、對與錯。也正因如此,藝術在自身碰撞以及相互碰撞中盡顯氣象萬千之態。好的藝術作品能在矛盾中找到平衡點,準確又獨特地表現出驚人的藝術魅力。而藝術最大的魅力或許就在創造藝術魅力和感受藝術魅力的過程之中。藝術是變化的,大到中西方美術史的變遷,小到一支變奏曲,都在錯綜變化中給人以強烈又細致的心靈顫動。創作者受題材、體裁、意象、受眾需求等各方面的影響,要對繁復的信息進行編碼,在宣泄自我的同時也讓人為之駐足流連。藝術創作沒有固定線路,條條大路通羅馬,而如何在錯綜變化中找到每個藝術個體通往羅馬的最佳道路,這是一場痛苦又快樂的探索。本文是作者通過對自身播音主持藝術專業的思考,結合學習各藝術門類的體會作出的隨想。
關鍵詞:藝術;播音主持
1 藝術源于感知并傳遞感知
列奧納多·達·芬奇在《繪畫論》中寫道:“你有沒有在陰晦的黃昏,觀察過男人和女人的臉,在沒有太陽的微光中,它們顯得何等柔和!在這種時間,當你回到家里,趁你保有這印象的時候,趕快把它們描繪下來吧。”[1]這充分體現了一個偉大藝術家的易感性。他關注周遭一切,哪怕是一個稀松平常的瞬間,而藝術往往就來自于這些靈動的瞬間。捕捉這些瞬間需要藝術家有靈敏的器官和善感的心。這種對世界的感知就像一股消滅黯淡的電流,將生活的瑣碎照亮為藝術的瞬間。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蘇軾的這首《臨江仙·夜歸臨皋》因最后的千古名句被人們記憶流傳,由對小舟之于滄海的感知聯想到自身之于塵世,于是一個遺世獨立的曠達詩人形象躍然紙上。很多人說,詩文除了“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都平淡無奇,筆者認為不然。普通男人是不會對酒過三巡后的場景進行此般記錄的,沒有心思根據天色去猜測時辰,更不會關注院內是否有鼾聲,敲門不應后不是撒潑就是順勢倒在門邊睡了。而蘇軾知醒知醉,會想時間,能行至江邊,不是因為他喝得不夠多,是他的各種感官在事物的刺激下能做出更細致具體的反應,促使他“倚杖聽江聲”,并為“夜闌風靜縠紋平”所動,由此感發“江海寄余生”,這才有了這亙古的藝術名篇。
文章寫至此,耳機里正播放著由高旗譜曲的童聲合唱版的《臨江仙》。筆者總在煩躁時聽此曲以撫慰不安的內心。想必,筆者便是感知到蘇東坡之感知了。
藝術源于感知,卻不止步于感知,更是將感知傳遞,這是一種交流。如果東坡當時有無限感慨卻只寫下“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雖是直抒胸臆表達感知了,卻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能讓人感同身受。很多詩文能傳頌甚久,正是因為它留下了能啟發作者又感動讀者的意象。春代表希望,梅代表堅韌,蓮代表高潔,這些都不是憑空規定,也不是約定俗成的。這是感知共享后的認知共識。其實其他藝術形式也是如此。在音樂中,我們用快節奏來表現急促,又在高音調中體會歡快的情緒;在繪畫中,我們用明亮的色調來體現溫暖,又在溫潤勾勒的線條中感受柔和;在朗誦中,我們用低音來表現愁緒,又在輕快的語氣節奏中享受明朗。
由于身處一個年輕的藝術學科,筆者常把自己融入整個藝術大環境中去對比、去汲取。播音主持和其他藝術門類一樣也源于感知,而作為一門基于文字再創作的門類,它更是藝術傳遞感知的典型例子。
再拿《臨江仙》來說,筆者以“醒復醉”的心理狀態,用聲音再現此文,引發不了聽眾與我一起“倚杖聽江聲”的沖動便沒有任何意義。最理想的是,筆者還能在受眾的眼中看到“何時忘卻營營”的自我拷問的火花,從而進一步激發筆者傳達“江海寄余生”的表現欲。
藝術就是如此,由感知起,可以傳遞甚遠,可以循環往復。有感知并能為感知所動的人,不論是藝術家,還是學習藝術的我們,必然是對生活充滿好奇的。而這份好奇來自對世界中那些美好或灰暗的沒有緣由、不計得失的深深的愛。
2 藝術基于自然又走向自然
前兩天,導師與筆者分享了《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中的一句話:“藝術革命有一個永遠不變的公式:一種藝術漸趨呆滯死板,不能再行表現時代趨向的時候,必得要回返自然,向其汲取新藝術的靈感。”[2]我們深感認同。這是傅雷總結的藝術經驗,也是千萬藝術家從自然所得的教訓。這里的自然當然不單單指“大自然”,它更是真實、單純、質樸。
藝術源于自然,關于這一點已不用贅述。或許我們當下更應對“走向自然”加以關注。這是長遠的創作道路,也是具體的創作方法。
在音樂美學家周海宏老師的講座中,筆者記住了一句話:“簡單的事被弄亂了,就很難回歸簡單。”對于這句簡單的話筆者卻不想簡單地理解,因為這句話其實反映了人們在藝術創作和藝術賞析中遇到的瓶頸。
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說。喬托的畫作《圣方濟各向小鳥說教》能讓人們感動到忘了形式上的笨拙而專注于它的簡潔和諧;小詩《清平樂·村居》中,辛棄疾舍棄修辭,只為大家描繪最真實的鄉土景象,可謂是朗朗上口,讓人一看便明白、一聽便記住;音樂方面,筆者想以鋼琴家巫漪麗為例,當筆者正在搜索演奏視頻的時候,卻刷出了老人家去世的消息,她帶著她的藝術人生化蝶而去。1958年,陳鋼與何占豪根據我國民間故事,以越劇曲調為素材作出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在那之后,《梁祝》以不同樂器的不同演奏形式成為人們最熟悉的旋律之一。但當我們看到巫漪麗88歲的手指在鋼琴鍵上躍動,沒有炫技,偶有半拍遲鈍,那一刻全場寂靜。這不是對年邁的憐憫,而是對真誠的崇敬。再說說有聲語言表達。作為播音系的學生,有幸在現場聽過許多名家對文字的演繹,但筆者最喜歡在導師家坐在她身邊,聽她念她用生命寫出的文字。沒有音響燈光,就在那張沙發上,筆者聽到了最完美的表達。不知該如何形容,拋開聲音的渲染和技巧的加持,仿佛是在頭發絲上作畫。別無他法,唯有真實。
說到這,不得不提人們對朗誦的誤解。好的朗誦不是嘶吼,更不是濫情。不是看似華麗的表達就一定高貴,也不是看似平和的表達就一定低級。其實這也是人們對藝術欣賞的誤區。平和不是平淡,筆者想到汪曾祺先生的文字,看似結構隨意、抒情自由,卻透著恬靜的熱情,他用最自然的情感流露緊緊地握住了大家的心。藝術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也不可能被所有人理解,作為一個學藝術的學生,筆者或許可以接受周遭對藝術的置若罔聞,但不愿意看到人們把垃圾當藝術品。
自然是出發點,也是必然歸宿。
3 藝術展現美卻不局限于美
當地時間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在火光中損毀了容顏。這使本就蒼老的建筑加快了斑駁的速度。不知那個在此為愛而亡的丑陋的敲鐘人是否也為之嘆惜。加西莫多,雨果筆下一個獨眼、駝背、有語言障礙的吉卜賽畸形人,從頭到腳都寫滿了“丑”,而他能成為眾多文學作品中流傳甚廣的一個人物,必然不是因為他的丑,而是他讓人們感受到了某種力量,這種力量是美的,所以說藝術展現美,卻不會拘泥于美。
導演任長箴在紀錄片《生活萬歲》中用3個月時間記錄了15個普通人的生活。它記錄了艱苦、反映了困頓,用絕望表現希望,讓我們摸到一顆顆溫熱的心。觀影時,筆者在一瞬間淚如雨下:一對老年盲人夫妻面對面坐著,酒杯好不容易碰到了一起,飲盡,女人說,你摸摸我的臉蛋,我是不是個漂亮的女孩子呀。
她是最漂亮的女孩子。筆者相信每個人看到這里都會認同。這就是藝術展現的美,沒有評判標準,卻由內心告訴你毋庸置疑的答案。
藝術是什么?依舊無解。但我們在求解的路上似乎離藝術更近了。而藝術也一直在自我求解的路上,它的目標應該是離我們更近吧!
參考文獻:
[1] 列奧納多·達·芬奇.繪畫論[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
[2] 傅雷.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M].現代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