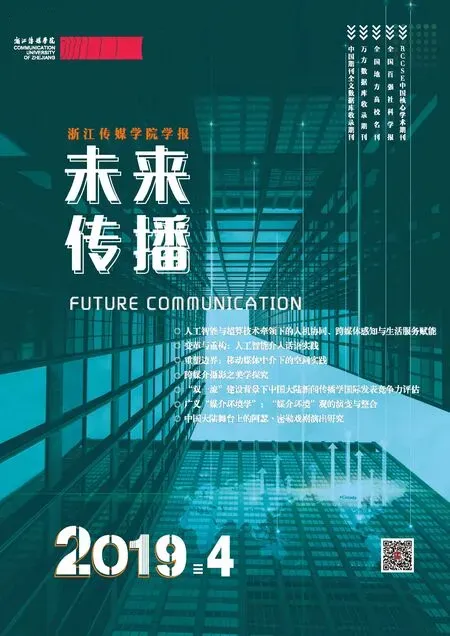廣義“媒介環境學”:“媒介環境”觀的演變與整合
王 潤
如今,“無處不在的傳媒成為當代社會一道亮麗的風景線,社會也在傳媒的發展、擴張、彌漫和滲透之中不斷建構和重構”,[1]“媒介正在以不斷變換的方式將世界置入我們的日常事務中”。[2]這些對現代社會的描述似乎構成了媒介技術與社會環境變遷的普遍刻畫,特別是隨著新媒體、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以及5G新技術的出現,傳播媒介已毋庸置疑地成為當下社會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傳播學學術流派來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媒介環境學(media ecology)在美國高校開設課程,即標志著將“媒介作為環境”(media as environment)研究的開始;而近年來,國內外學界開始討論傳播研究的“媒介化”(mediatization)轉向,其中心意旨也試圖揭示出媒介在社會中的作用和以媒介運作為邏輯的社會形態特征。[3]這兩個學術流派有何異同,以及如何理解媒介環境學派強調的“作為環境的媒介”到傳播研究“媒介化”的轉變是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本文在比較分析兩種“媒介環境”觀的研究范式和“媒介”內涵的基礎上,綜合性地提出了廣義的“媒介環境學”,并試圖全面理解現代社會的“媒介環境”,深化對北美環境學派與歐陸媒介化學派的勾連與整合。
一、北美媒介環境學視角中的媒介與環境
說到傳播學對媒介與環境關系的認識,北美多倫多大學的媒介環境學派是一支重要的學術流派。延續早期媒介環境學派先驅的思想,媒介環境學的重要奠基人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創立媒介環境學課程時指出,“媒介環境學把環境當作媒介來研究”“研究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的感知、感情、認識和價值”。[4]因而,媒介環境學對媒介與社會關系的考察,將“人、技術和文化的三角關系為研究重點,以泛環境論著稱,主要旨趣在技術和媒介對人和社會心理的長效影響”。[5]值得關注的是,媒介環境學對媒介之于人和社會影響的考察,著重體現在符號環境、感知環境和社會環境對人們思維和感知的塑造上,矯正了以往經驗學派獨霸、批判學派式微的傳播研究現狀。
該研究視角一方面反映出媒介環境學派吸取了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關于媒介技術對人類感官影響的基本觀點。[6]媒介環境學派重要人物麥克盧漢提出“媒介即人體的延伸”的觀點,認為“一切技術都是肉體和神經系統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并且“人在正常使用技術的情況下,總是永遠不斷受到技術的修改。”[7]這預示著人類通過技術革新延伸人體的一部分發明媒介,并在使用媒介的過程中影響到人類的感知。而事實上,在麥克盧漢之前,芒福德、伊尼斯也從技術與文明的關系、媒介與傳播的偏向等視角提出“技術進步的人性化”[8]“技術偏向的時空感知”等觀點,[9]媒介技術對社會感知的影響成為媒介環境學派學者關注的焦點問題。基于此,媒介環境學認為媒介固有的物質結構和符號形式塑造著什么信息被編碼和傳輸、如何被編碼、傳輸和解碼,以形成特有的偏向,并促成各種心理或感覺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結果。因此,當傳播媒介成為社會環境,以媒介環境學視角對媒介技術進行考察時,最初是以技術和符號的社會感知作為認識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媒介環境學創立之初所體現的人文主義關懷。受到生物學生態(ecology)概念的指引,媒介環境學強調媒介與人互動產生平衡而健全的環境,以促進文化的象征性平衡。[4](44)當傳播媒介作為環境在社會中予以應用,該學派重點在于協調人與傳播媒介的關系,把維持媒介與人的動態平衡關系視作最終的歸宿,突出符號、媒介和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強化文化、科技與人類傳播之間的互動共生關系。麥克盧漢也曾指出,“一種新技術讓我們的一種或多種感官得以延伸,并在社交世界擁有得以外化的具體表現時,那么我們所有的感官將在特定的文化中形成新的平衡比率。”[10]可見,媒介環境學派反思媒介技術的工具論,試圖擺脫技術理性指導下的傳播異化,將生態學的理念和文化價值觀放置在特定的媒介技術環境下思考,把和諧與平衡作為處理技術與社會關系的目標,希望最終形成媒介技術與社會的良性互動關系。
無論是媒介技術對人類感知的影響,還是媒介技術與人類的人文主義關懷,宏觀地看,媒介與文化是媒介環境學考察“作為環境的媒介”的一對重要關系:媒介作為人們的外部環境對個體產生影響,強調社會和文化對媒介感知的平衡作用。媒介環境學強調對人類、媒介和社會進行系統觀察,開辟了在結構和互動關系中動態考察媒介的視野,所倡導的協調、平衡觀念是作為最高的前提存在的,回應了20世紀70年代后生態主義的政治話語。[11]因此,媒介環境學契合了“生態”概念最基本的內涵,賦予作為環境的媒介與文化價值觀的生態平衡、和諧與穩定,提供技術生態主義的構想,旨在關注媒介本身如何影響社會和人的發展,使之區別于傳播學研究的其他兩大流派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12]
然而,這一學派也具有研究視角的局限性,比如過于偏重科技生態的呈現,而缺乏對生態問題中作為核心話語的文化生態和生態倫理方面的系統論述,導致對生態認識起決定性作用的政治經濟方面的分析弱化,從而忽視了媒介主體的作用。同時,由于該學派關注媒介技術對社會和人類發展的影響,因而也就將媒介技術作為社會影響的前提,而人類和文化對技術的反應則僅是作為系統調適和平衡來運行。即使媒介環境學研究“不否認多元因素對社會歷史變化的影響,也不否認人與社會在媒介面前的主觀能動性”,[13]但建立在技術生態論基礎上的技術反應與調適是有限和脆弱的,科技人文主義浪漫式的想象背后缺乏的是對媒介技術形成的社會脈絡和技術實踐中權力因素的考量。技術與文化的互動機制一旦失去平衡,就會成為媒介環境學派難以解釋的對象,因此,政治經濟力量和媒介主體能動性的缺失成為從媒介環境學視角理解媒介技術與文化關系時天然的缺陷。
二、歐陸“媒介化”視角中的媒介與環境
近年來,歐洲學界興起的“媒介化”專題的討論,成為理解媒介與社會環境之間關系的又一概念。研究者將“由媒介運用而來的社會與文化生活的轉型,并以適合媒介再現的方式而呈現的過程”稱之為“媒介化”,該概念重新審視了媒介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強調媒介介入社會進程,甚至重塑其他社會場域中特定的制度化實踐。[14]因此,也就將傳統媒介環境學所關注的“媒介”環境轉移到當下的“媒介化”環境之中,由“媒介作為環境”過渡到“媒介化”環境/媒介化社會的演變。
盡管“媒介”環境和“媒介化”環境都離不開媒介技術作為傳播和擴散的最基本前提,但“媒介化”概念不僅在于強調媒介作為技術載體和平臺,更在于強調現代社會中社會與文化生產的“媒介邏輯”(media logic),[15]特別突出媒介具有促成不同社會生活或相關領域社會實踐的可能性,媒介邏輯成為當代社會邏輯的一部分。丹麥學者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也指出“媒介化”被用于描述社會和文化綜合發展中的一種狀態或階段,即媒介對其他社會制度或系統施加特殊的主導性影響。[16]在媒介化環境中,媒介已經不再是處于被支配和信息中介的角色,而是成為社會或文化變遷的能動實施者,媒介被進一步整合進入相關領域,成為主體以媒介邏輯予以運作后的存在。
“媒介化作為一個分析概念,試圖將特定的媒介科技形式的使用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與更廣闊的社會過程接合,且更強調前者(媒介)對于后者(社會過程)的介入或干預”。[17]而媒介的這種介入或干預成為現代媒介化社會公眾認知與架構社會現實的一種特殊框架,揭示出媒介在再現和建構世界的過程中自然化地成為社會的中心,形成圍繞媒介中心而產生的社會邏輯。[18]的確,在現代社會環境下,情境的再現日益需要通過媒介形式予以呈現,媒介在作為建構世界的獨特機制以及形成公眾認知的社會框架方面,起到基礎的中介作用,同時公眾能動地借助于媒介邏輯的運作使媒介與社會處于互構和再生產的關系之中,從而促進媒介對政治、文化和社會的重塑。
與傳統的媒介環境學派不同的是,媒介化研究彌補了以往媒介研究的缺陷,即“媒介不再是社會之外的一個獨立存在,而是作為社會和文化的一部分發生著影響”。[19]“媒介化”環境中的“媒介”不再是媒介環境學中線性單一的、依附在人類感知和文化目的之下的媒介技術,而是體現出“媒介與社會建制的互動過程”,媒介的技術形式在社會動態過程中與既有的社會建制發展出復雜的互動關系。[17]媒介技術與社會場域之間形成相互的勾連,技術背后的主體能動地參與和建構媒介,主動地介入到日常生活與社會世界,參與到社會進程之中。
“媒介化”概念逐漸成為現代社會中人類互動實踐與媒介技術相關聯的考察對象,[20]擺脫了以往技術協調式發展的科技生態論,媒介使用主體的社會實踐打破了技術平衡觀,媒介(技術)與社會環境的關系不斷被重塑,并處于深度地互動和建構之中,形成了在媒介化進程中依托媒介技術而形成的社會實踐。此外,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的“媒介域”(mediaspheres)概念也類似于“媒介化”的研究取向,都在于討論技術的主體和社會關系結構,考察“參與符號生產和事件生產的相互交織的中介實體和動力程序的關系邏輯”“把技術變量作為agency(能動)來考慮,技術配置和主觀意圖相結合、行為和再現相統一的技術文化同時觸摸社會心理的邊界”,[21]強調技術演化與信息發送、接收形成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過程。
因此,媒介化研究的技術和社會建構論思想將媒介應用背后的主體能動邏輯引入對媒介與社會關系的思考,從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媒介環境學派的技術生態觀點,其考慮到媒介與社會權力、外部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讓技術的應用主體處于媒介環境之中,能動地進入到媒介的社會建構進程之中,從而實現“媒介與社會建制的互動”。
三、兩種“媒介環境”觀的范式與內涵差異
媒介環境學和“媒介化”研究是從不同的視角來理解和把握媒介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的,前者強調“作為環境的媒介”,后者強調“媒介與社會建制的互動”,兩種視角在學理上呈現為研究取向的差異,但它們的共同點在于把媒介視為社會外部環境的一部分,媒介進入社會各個領域并產生影響。現代社會正處于“媒介”環境和“媒介化”的社會形態中,如何理解與認識兩種不同的“媒介環境”觀,以及兩者對“媒介”的認識和研究取向又有何不同?
(一)兩種“媒介環境”觀的研究范式
從研究范式來看,兩種“媒介環境”觀具有不同的研究傳統和旨趣。傳統的媒介環境學派延續了人類生態學理論學家霍利(Hawley)關于社會環境與社會系統的認識,特定環境中整體相互依賴的單位,彼此建立聯系以適應相應的功能,技術的增長和進化會與其他技術或文化形成均衡,達到平衡的狀態。[22]這種研究傳統以結構主義為基礎,沿襲功能主義的傳統,將任何一種環境均視為一種結構,每一種結構都有約束其內部行為的外部規律法則。[23]可見,傳統的媒介環境學研究范式中,媒介是外部社會結構的因素,而文化的感知與調適是外部的法則,體現出作為結構的技術與作為外部約束機制的文化之間的平衡與制約關系。結構功能主義取向試圖想要建立結構與功能的協調與平衡,與人類生態學和媒介環境學所倡導的技術生態主義理念不謀而合。[24]放置在傳播活動中,結構功能主義模式把傳播結構視為一種外在于人的實踐的功能性結構,人作為實踐的主體特征在傳播結構中趨于消失。[25]
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改變了(結構)功能主義者視野中將“結構”視為社會關系或社會現象的某種“模式化”的狀況,而將“結構”理解為一種社會再生產的產物,在實踐活動中導引具有認知能力的行動者。吉登斯所稱的結構是規則和資源,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并“內在于”人的活動中。這里結構變得不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可以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26]在以往媒介技術與社會環境這對關系中,媒介技術作為社會結構對社會產生影響,被視為脫離于人的行動的外在之物,即使媒介與文化的互動關系和符號感知作用也是以媒介技術作為社會環境和社會結構一部分為前提的。而結構化理論則認為規則與資源在社會系統中的實踐與互動過程是不斷循環往復的動態過程,媒介技術不再只是人們施加行為的對象,而是媒介在人們實踐活動中能動的過程,通過和在行動的反思性監控中得到組織。行動者的自主性和反思性成為人作為主體從事社會實踐的重要特征,而這種反思性體現在傳播活動中則是行動者(主體)按媒介邏輯進行運作的傳播實踐活動。
當然,在現代社會的背景下,“媒介”的復雜性在于其具有雙重屬性:媒介(技術)不僅是作為社會結構的中介載體,同時又是人們能動地實現相關社會實踐的對象。媒介化研究正是注重考察媒介環境與社會互動過程中“被媒介化”的現實情境與日常生活的建構,以及主體進入到媒介建構的進程中逐漸成為按媒介邏輯進行社會運作的制度化過程。因而,媒介化的研究取向具有社會建構論的色彩,媒介技術(結構)與社會行為是互構和再生產的過程,媒介成為人們按媒介邏輯進行社會實踐的對象,在媒介運用過程中體現出人對“媒介”的反思性和能動性特征。
(二)“媒介”概念的不同內涵
當然,對不同“媒介環境”觀的認識,也體現出對“媒介”概念不同內涵的理解。傳統媒介環境學中的“媒介”,把“媒介作為環境”,媒介是人體感知的延伸,無論是作為技術意義上的媒介,還是作為隱喻意義上的媒介,媒介(技術)是作為人的存在方式。從海德格爾存在主義的視角理解“媒介”的特性,媒介(技術)不僅是作為人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是構造出人與技術的一種新關系參與到事物、自然和世界的構建中,體現為技術(媒介)與主體之間復雜的互構關系。[27]因而,“媒介”彌漫于人們經驗世界的所有努力中,成為人們在世存有的“中介”,是一個容納人、技術、權力和資本要素的“行動場域”。[28]因此在傳統媒介環境學研究中,媒介環境和文化對人類媒介感知的協調與平衡是重要的調和方式,體現為技術作為人的存在方式和技術文化的調和統一。
而“媒介化”研究中的“媒介”則體現出新的內涵和延伸,“媒介化”概念一方面被視為制度化過程,“媒介融入其他社會制度與文化領域的運作中,同時其自身也相應成為社會制度”,[16](21)使媒介的角色以獨立的社會力量形塑現代社會;另一方面體現為社會建構特征,將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化視為主體與媒介的社會互動過程,人們通過與媒介的互動來改變其建構社會的方式。如克羅茨(Krotz)將“媒介化”視為“元過程”(Meta-process),媒介逐漸地與日常生活、社會和文化作為一個整體的建構緊密相關,“媒介化”的動態過程建構起與全球化、個體化、商業化并行發展的社會趨勢。[29]無論是“媒介化”的制度化過程,還是社會建構特征,“媒介化”反映出人、技術、權力、資本等要素在“物化”裝置中的相互匯集與互構的過程。
在媒介化進程中,“媒介”不僅是作為人的存在方式與技術文化的調和,而且還將這種存在方式發揮到極致,媒介背后的主體(人類)能動地介入到媒介的建構過程中,容納各種要素的“行動場域”動態地整合與互構,彼此滲透和再生產,體現出“媒介”的能動性和自主性。此外,庫爾德里提出的媒介研究的新路徑,更是強調“不是把媒介當作物件、文本、感知工具或生產過程,而是在行為的語境里參照人正在用媒介做什么”。[30]這種對“媒介”的認識從“作為環境的媒介”到“作為實踐的媒介”(media as practice)的轉向,使得媒介研究的實踐路徑揭示出現代社會媒介所具有的社會實踐屬性,也體現出兩種“媒介環境”有著不同的“媒介”觀。
綜合兩種“媒介”的內涵,以在世存有觀念去理解“媒介”,“媒介”都是人經驗和投身世界的一切技術與非技術中介物,是以介質為基礎的載體而存在。而媒介環境學與“媒介化”研究中“媒介”的差別在于容納各種要素的“行動場域”和“行動場域”內部不同要素的互構之間的區別,這體現出作為存在主義的媒介環境觀與作為互構實踐的媒介環境觀的差別。兩種“媒介環境”概念,雖然同中有異,但均以“媒介”與環境的關系作為考察對象,呈現為靜態與動態的結合,內涵具有互補性與延續性,反映出“媒介環境”的不同面向。
四、整合與建構:廣義的“媒介環境學”
研究范式和對“媒介”概念內涵的不同認識厘清了兩種“媒介環境”觀在研究取向上的演變與差別,事實上,正是近年來歐洲學界興起的“媒介化”研究開啟了對于“媒介環境”新的理解,對我們在現代社會背景下重新理解“媒介環境”成為可能。筆者試圖整合傳統北美的媒介環境學派與歐洲的“媒介化”研究,建構廣義的“媒介環境學”。
胡翼青等將媒介化社會理論視為“第二個芝加哥學派”,以符號互動論為理論線索梳理了芝加哥社會學派從布魯默、戈夫曼、布迪厄到媒介化理論的延續與變形,梳理了芝加哥學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將結構納入行動的考察之中,并與符號互動論整合在一起,從而提出重新理解傳統的芝加哥學派。[31]這種研究視角有一定的可取之處,芝加哥學派作為社會學發展的早期對社會系統的運行做了整體上的宏觀學理架構,研究議題包羅萬象,勢必涉及到傳播媒介及社會互動的多個方面,因而當前歐洲學派所討論的媒介化理論追溯到芝加哥學派自然有相應的理論淵源。然而,這種追溯的局限性也在于:一方面,其忽視了將媒介技術作為單獨的研究對象在傳播學的研究中加以延伸討論,而這正好是媒介環境學派把媒介技術視為核心議題的獨特性所在,即突出強調了媒介技術在傳播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媒介環境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如伊尼斯、麥克盧漢等,他們自身的學術淵源都部分來自于芝加哥學派,把媒介化理論追溯到更為歷史漫長的研究學派顯得過于遙遠。本文將歐洲學派的媒介化研究視為“第二個媒介環境學派”,是傳統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的延伸和發展。
在整合兩種“媒介環境”觀過程中,舒爾茨(Schulz)的“媒介化”過程的四層次和夏瓦(Hjarvard)的“媒介化”研究為整合兩個學派提供了必要的思想來源。首先,舒爾茨把媒介化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歸納為以下方面:[3](101)(1)延伸(extension):在時間和空間上延伸人類的交流能力;(2)替代(substitution):替代傳統的面對面交流活動;(3)融合(amalgamation):將日常生活中不同層面的交流活動融合起來;(4)適應(accommodation):行動者有意識地按照媒介邏輯從事交流活動。分析這四個層面,第一個層面與媒介環境學的代表人物麥克盧漢的“媒介是人體感官的延伸”以及伊尼斯所推崇的“時間和空間的偏向”有緊密的聯系,把媒介視為環境來認識,屬于早期媒介環境學的分析視角。而第二、三、四層面則強調媒介與社會其他領域的互動、媒介作為社會的“塑造力量”、現代社會按媒介邏輯參與到行動者的日常活動之中,[32]這是屬于“媒介化”研究的“社會建構論”視角。其次,夏瓦的“媒介化”研究構成了對舒爾茨“媒介化”研究的補充,他將媒介視為獨立于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形式,以其獨立的制度性要素而對社會進行重構,[33]被稱為“媒介化”研究的“制度化視角”。
以上舒爾茨“媒介化”的四個層面加上夏瓦“媒介化”研究的“制度化視角”,構成了理解與認識兩種“媒介環境”觀的五個層面(見表1)。五個層面包括從微觀、中觀到宏觀,從技術的感知與延伸到媒介形式對傳統面對面交流形式的替代,過渡到媒介與日常生活的交流與融合,再到以媒介邏輯來建構社會交流和傳播活動,最后到最為宏觀的以制度化的形式確立媒介的獨立性與以媒介邏輯為特征的現代社會運作方式。其中,第一個層面屬于媒介環境學派的“媒介作為環境”的基本觀點,而第二到第五層面屬于媒介化研究對“媒介化”環境的基本觀點,五個層面融合了兩種“媒介環境”觀,形成了對現代社會“媒介環境”的全面認識。

表1 兩種“媒介環境”觀的整合
這一分析視角一方面體現為廣義上對媒介與環境關系的討論,把原有的具有科技生態傾向的媒介環境學派改造成新的現代媒介環境下媒介與人的中介互動和媒介與社會建制互動相結合的新型“媒介環境”,研究取向上既體現為部分差異,又體現為研究對象(媒介環境)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第二個媒介環境學派”彌補了傳統媒介環境學派忽視政治經濟因素和媒體主體能動性的缺陷,將歐洲學者對權力、政經因素的強調與北美媒介環境學者的人文主義學術視野相融合,實現了微觀技術和文化感知與宏觀政經關系和主體能動的統一,在揚長避短的同時又延續了媒介環境學奠定之初將傳播媒介(技術)對文化和社會形式影響作為基本關注的研究命題,有機地將兩種“媒介環境”觀整合起來。
總之,在當下更為廣義的“媒介環境”背景下,筆者認為有必要構建廣義的“媒介環境學”,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媒介”與社會、公眾之間的互動實踐,及時考察變動中的媒介環境因素對輿論生態、主流話語及社會變遷的影響,進而重塑對“媒介環境”及其社會影響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