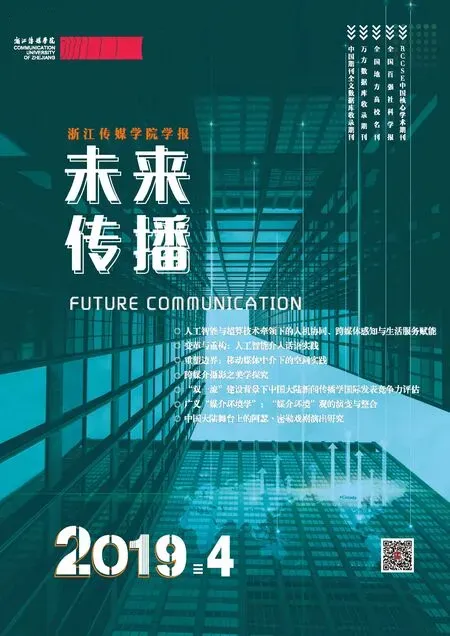關于新聞游戲的冷思考
李泓江
新聞游戲是以電子游戲作為新聞之外在傳播形式上的新興新聞形態。技術變革語境下,似乎不少論述都將新聞游戲視作一種新聞實踐發展的趨勢,“電子游戲正在成為一種重要的傳播媒介,新聞游戲也成為不少媒體新聞實踐創新的重要方向”[1],“‘新聞游戲’逐漸從邊緣走向中心,以常態化的面龐進入專業領地和大眾視域”[2],“在新興可穿戴技術和更便宜虛擬現實設備的刺激下,游戲和虛擬現實技術正在改變新聞生產故事的方式”[3]。這些言之鑿鑿、幾乎以肯定性話語出現的陳述,篤定新聞游戲會在未來之新聞傳播圖景中占據重要位置。但有趣的是,沿著“已然如此”“必然這般”面貌呈現出來的預測性話語,于所在語境上下尋索,卻不曾尋得見經得起推敲的有力論據與邏輯支撐。因此,本文感興趣的研究問題是:為何新聞游戲會被不少人認為是新聞實踐發展的趨勢?從新聞游戲自身潛含的內在邏輯及所處現實位置來看,能否真的像前述話語所傳遞出的那樣,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用以表征新聞的重要方式?
一、技術解釋的泛化
細細揣度,這些學者的表述背后或許暗含了這樣一種似乎不言自明的邏輯:技術是推動新聞實踐創新的根本性力量,技術可以解決新聞所面臨的幾乎所有難題,新聞游戲的出現是以技術方式解決新聞難題的新興傳播形態,所以,新聞游戲會成為未來新聞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這種邏輯,在相關論述中有著較為顯見的、清晰的痕跡,對于技術的樂觀和新聞游戲未來的前景被一些學者強行串聯在一起,“未來我們還會迎來Web4.0、Web5.0甚至更多豐富的信息交流時代VR技術的流行、IP概念的深入、不同行業的融合已讓我看到了今后還會出現更多更為有效的信息解構和重組形式,新聞游戲的未來具有太多的可能性”[4],“由于媒體技術的發展,利用游戲這種方式來講述當下發生的新聞故事,已經變得越來越容易”[5],“新媒體在我國的興起為新聞游戲準備了前所未有的技術條件”,“歷史證明:新聞完全可以通過多種媒體發布。在數碼游戲已經成為深受大眾歡迎的游戲形式下,新聞若與游戲結合,可以創造出新形式”[6]。
如果放在嚴肅學術語境下,這種以技術來佐證信念、以技術來憧憬未來的話語是需要推敲和質疑的。技術毫無疑問在傳播結構改變、新聞樣態轉換方面發揮了革命性的作用,甚至不少技術決定論者將其視為變革發生的根本因素。但上述學者所忽視的一個問題在于,承認技術對新聞傳播形態變換的革命性作用,不代表承認游戲技術的革命性作用。游戲技術僅僅是眾多新興技術的一種,且是一種尚未經過充分的市場考驗、思想論爭的傳播技術形態,從邏輯上不能直接推出其將成為未來新聞業發展重要方向的結論,如果強行推導,勢必違背基本的形式邏輯。
這意味著,當然要承認技術在社會發展、傳播演進中的關鍵作用,但在分析具體問題時,我們卻務必要結合具體語境,結合所關注問題的具體情境進行針對性的解釋和思考,否則很有可能泛化技術的解釋作用,以致陷入片面的、膚淺的境地,甚至會產生一種盲目的技術迷思。進一步來說,這種簡單的、化約式的歸因方式無疑會窄化媒介研究的分析路徑,“研究中技術功效以外的其他重要維度往往被遮蔽”[7],問題背后所蘊含的復雜而豐富的現實性、可能性以及具有深厚意涵的“人”之特性均被技術樂觀主義赤裸裸地剝奪和淹沒。事實上,在我們的現實新聞實踐中,新興新聞活動、新興新聞現象的產生、形成往往是由復雜因素共同型構的,恰如有學者所說,這些新活動、新形態、新現象“通常是由于可感知的需要、競爭和政治壓力,以及社會和技術革新的復雜相互作用引起的”[8]。
前述論述在對新聞游戲做出“從邊緣走向中心”這一預測的背后,事實上便潛含著這樣一種脫離具體語境、忽視其他因素、將技術解釋泛化的思維方式,過去及當下所存在的新聞游戲是電子游戲技術進步的結果,新聞與游戲相糅合而產生的種種問題、矛盾皆可通過技術進步得以解決與克服。這固然描繪出一幅色彩斑斕、令人欣喜的未來圖景,卻掩飾了新聞游戲這一嶄新新聞形態背后所蘊含的否定性力量。而這些否定性力量,或許是羈絆與阻礙技術作用發揮,甚至是促使新聞游戲成為明日黃花的關鍵性因素。
二、自發誕生與被扶持的“試驗品”
前文以相當的筆墨,分析了學者們為什么會認為新聞游戲會成為新聞實踐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不得不承認的是,近年來,的確出現了不少新聞游戲。在提出本文之核心性觀點及論證之前,我認為有必要從根源上說清為何會出現這些新聞游戲。
從本質上來看,新聞游戲是作為內容之新聞與作為呈現形式之游戲的結合體。對于意義之表達、傳遞而言,形式與內容間的關系向來是無法回避的考量要素,“意義產生于形式與內容的交匯之中——亦即傳播的話語、體裁和形式之中”[9]。同文字、圖片、聲音、視頻等其他傳播形式一樣,新聞游戲是新聞信息的另一種呈現方式,一如伊恩·博格斯特(Ian Bogost)和西蒙·費拉里(Simon Ferrari)在其《新聞游戲:游戲中的新聞學》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新聞游戲的本質是一種程序性修辭,一種通過計算機程序組織新聞內容的方式[10]。從這個角度來看,游戲本身即是一種充滿互動性、參與性的意義體系,必然需要由相應的內容進行填充和補足,新聞又可理解為對新近發生之事實的報道,呈現內容、傳遞意義構成了新聞的天然特征,故而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契合性。數字技術發展的語境下,新聞與游戲結合而成的新聞游戲應運而生。
相關研究顯示,最早的新聞游戲源起于烏拉圭游戲設計師岡薩羅·弗拉斯卡,其于2003年創辦了新聞游戲網(NewsGaming.com),并發布了以9·11恐怖襲擊為背景的新聞游戲[5],隨后,其他新聞游戲產品以零星的方式出現。新聞游戲于近年來的增多,雖然具有獨特的時代語境和職業語境,但其更多的是作為一種“試驗品”的面貌出現。新興媒介環境下,人們的新聞收受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新聞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挑戰。這種語境下,技術成了解決新聞業困境的有效路徑,新聞實踐頗有饑不擇食、慌不擇路之感,諸如VR新聞、數據新聞、智能新聞等多種新興新聞實踐猶如雨后春筍,新聞游戲也是在這波潮流中出現的新事物。但這眾多試驗品也有自身的生命特征,有茁壯成長的,如數據新聞、智能新聞等,也有像本文認為的后勁不足的新聞游戲。
當然,上述時代性特征、技術性特征僅僅是新聞游戲重現的表層原因。就像布爾迪厄所指出的那樣,新聞場域是被嚴格限制的文化生產場域的一部分,其會被政治力量和商業性力量所左右,也就是說,新聞場域是具有高度他律性的。[11]從根源上來說,這些年誕生的新聞游戲,是技術邏輯、市場邏輯和政治邏輯等多種力量相互交合的產物。新聞游戲并不像諸如自媒體等其他時代潮流下的傳播活動,可以依賴更為多元化的社會力量進行生產和傳播,游戲的生產與制作往往需要雄厚的財力支撐,新聞游戲亦是如此,例如國外引領近年來新聞游戲潮流的有《紐約時報》、美聯社、CNN,國內引領新聞游戲潮流的主要是網易、財新、《人民日報》,這些新聞游戲生產者或為主流新聞媒體,或為實力雄厚的互聯網公司。
外在力量的卷入,說明新聞游戲從一種自然誕生的“天然產品”轉向為外力所推動與滋養的“試驗品”。這種外在力量的試驗品意味著,若是其能夠產生足夠的效果,便會被外在力量扶持,若是效果不佳,則會為外在力量所拋棄,而決定其效果和影響力的因素,更多地在于新聞游戲這種傳播形態自身生命力的強弱。畢竟,技術只能決定是否會有新興傳播形態出現,而人們是否接受,這種新興傳播形態是否能夠經受得住市場的考驗,才是決定其能否長期存在、能否長期廣泛存在的根本原因。在此意義上,筆者認為新聞游戲的未來,并沒有一些學者所預測的那般樂觀。一如前文所說,近年來,新聞游戲是在包括市場、政治等在內的多種因素作用下出現的。在新聞游戲這一具體語境中,對其未來前景之分析,不能僅僅著眼于技術,還要考慮到其作為一種產品或工具本身的意義和價值,而新聞游戲自身潛在的矛盾和否定性因素,是新聞游戲生命力不足的重要體現,這意味著不能簡單地論斷新聞游戲會成為未來新聞業發展的趨勢和潮流。
三、時效性與高時間、成本間的矛盾
以歷史眼光來審視,不斷會有新事物得以誕生,但誕生是一回事,能否經得起時間考驗、成為未來新聞的常態化表達方式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決定一種新聞呈現形態生命力強弱及其能否經受住時間考驗的,是多種復雜的、綜合性的因素。具體至新聞游戲的分析中,在筆者看來,從新聞生產的角度看,作為形式的游戲與作為內容的新聞具有難以調和的矛盾,盡管已有一些學者就游戲之虛擬性、參與性與新聞之真實性、客觀性之間的矛盾進行了探討和分析(1)較有代表性的探討和觀點可參見:李俊欣.符號敘述學視角下的新聞游戲及其倫理反思[J].新聞界,2018(9);周敏,侯顆.新聞邊界視角下的新聞游戲探究[J].現代傳播,2016(1).,但這些更多涉及倫理、規范性的命題并不構成新聞游戲生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新聞游戲較高的時間制作成本以及其高度可替代性,使得新聞游戲很難走入新聞呈現形式體系的中心地帶。
相較于報紙、廣播、電視以及互聯網等其他新聞呈現形式而言,新聞游戲顯然存在著更長的開發周期和制作時間,這是作為表意方式的游戲與具有極強時效性要求的新聞之間的第一層沖突。對于其他多數新聞傳播方式而言,新聞生產的時間主要可以區分為資料收集時間和文本制作時間兩個部分。例如,以文字為傳播形式的新聞生產主要包括采訪與寫作兩個環節,以視頻為傳播方式的新聞生產包括現場視頻錄制與后期視頻剪輯兩個環節,較為簡潔、少量的生產流程和生產環節使得新聞生產迅速而快捷,從而保證新聞時效性的基本要求。相對而言,新聞游戲的生產環節顯得更為復雜。一款新聞游戲往往是一個內容復雜的意義體系。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相較其他新聞呈現形式而言,新聞游戲的生產和制作流程更為復雜。從邏輯環節上來看,一方面,其所需原始資料、素材往往更為豐富,故而在資料收集上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成本;另一方面,原始的資料、素材只有經過精心、巧妙的構思與設計才能得以構成一個有效的意義系統,新聞游戲存在著大量的構思與設計上的時間成本;除此之外,在構思與設計完成的基礎上,亦即確定過腳本之后,還要進入游戲制作環節,只有以完整的、可供使用的產品形態呈現時,新聞游戲的生產才算完成。在技術樂觀主義者看來,技術能夠大幅縮短新聞游戲的生產時間,但其所謂的“縮短”,更多的是游戲制作環節所需的時間,而資料收集、復雜意義體系的構思與設計等更多需要人力來完成的環節,因多種情況下與技術并無實質性關聯,故而并不會因為技術的進步而產生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改觀。
難以縮減的生產周期,在游戲與具有極高時效性要求的新聞之間制造了難以跨越的溝壑。快速、及時傳播是新聞傳播的時間要求,“所有能夠公開傳播的信息傳播中,及時傳播可以說是新聞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新聞傳播規律的內在要求”[12],而在當前的新聞環境、傳播生態中,高時效性更是成了新聞之基礎的、必備的屬性,“速度(speed)、即時性(immediacy)、同步性(simultaneity)成為新聞的壓倒性時間要求”[13]。長生產周期與高時效性要求之間存在著本質層面的不可調和性,不論是對于新聞生產者而言,抑或是對于新聞消費者而言,這種不可調和性都是難以接受的,因而構成了新聞游戲黯淡前景的根本原因。
與此同時,較長的時間周期,精心巧妙的設計與構思,所伴生的是新聞游戲的高制作成本。眾所周知,游戲是一個要投入較高成本的領域,根據《中國游戲產業發展報告(2017)》調查顯示,游戲產品已經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精品化趨勢,“研發成本越來越高”[14]。恰如學者潘亞楠所說,“新聞游戲的制作周期較長,如《拯救海地》的報道就耗時4個月,花費2.24萬歐元,當游戲制作出來后,這一新聞事件的熱度可能已經冷卻”[15]。對于其他游戲產品而言,高成本更有可能帶來高收益,但對于新聞游戲而言,高成本與高收益之間還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難題,這一難題根植于游戲與新聞之間的內在矛盾——游戲是一種可重復性的意義系統,而新聞則為少頻次乃至一次性的快速消費產品。游戲的可重復性所帶來的是消費者持續地投入時間、金錢、精力,而新興媒介環境下,“受眾對新聞產品的閱讀越來越偏向快餐式閱讀”[16],新聞游戲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消費者的投入是短時期甚至一次性的,故而新聞游戲之高成本所面臨的結果大概率是低投入產出比,甚至極有可能為負投入產出比。這種情形與新聞媒體自身的目標之間存在著南轅北轍般的差異,市場經濟環境下,如何更好地實現盈利是新聞媒體所面臨的最為重要的現實命題,在此意義上,新聞游戲幾乎沒有可能成為作為理性市場主體的新聞媒體的正確選擇。
四、兩種競爭場域與高可替代性
如果以經濟學的視角考慮,新聞游戲之所以前景黯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新聞游戲往往是高度可替代性的產品。在現代經濟學視域中,影響交易達成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消費者的個人偏好,指向市場;另一個則是產品的不可替代性,指向產品本身。而所謂的不可替代性,是指“產品具有的不可被其他產品所替代的性質”,“產品的不可替代性就是一個產品或者說一種類型的產品存在的理由”[17]。“替代”一詞本身潛含著比較之意味,因此,一種產品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要在其與所屬類別、種屬中其他產品的相互比較中才能得以顯示和呈現。新聞游戲是作為內容的新聞與作為形式的游戲結合而成的產品形態,對于新聞游戲之可替代性的考察,一方面要將新聞游戲放置于新聞表達的形式體系之中,另一方面,還要將新聞游戲放在眾多游戲的種類之中,進行具體的分析和比較。換言之,即要將新聞游戲置于由多種呈現形式構成的新聞場域和由多種類別構成的游戲場域,分別進行審視,從而判斷新聞游戲的競爭力和生命力。
在新聞表達的形式體系中,新聞游戲顯然不具備不可替代性。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曾說:“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18]對于麥克盧漢之語,我們亦可做出反向的闡釋與解讀:只有為個人和社會引入新的尺度,才可被承認為一種具有較高價值的媒介(表意系統)。從這個角度來看,作為意義承載形式的游戲,對于人們的新聞收受活動并未帶來新的尺度,換言之,新聞游戲更多的是一種已有表意手段、形式的復合與疊加,其所帶來的更多是體驗上的增量和產品形態上的增量,而無表意形式上的增量、認識論意義上的實質性增量。
這里,筆者想說明的意思主要包括三層:(1)新聞游戲是一種多種意義承載形式的聚合,盡管新聞游戲是一種較為新興的新聞傳播產品形態,但是其傳達意義的方式依然是文字、聲音、視頻、動畫等傳統表意形式和傳播手段,通過游戲來實現的新聞傳播,完全可以借由其他傳統表意方式諸如報紙、廣播、電視得以實現,在此意義上,新聞游戲于表意形式上而言,并未產生新的變量與增量,所以是一種高可替代性的表意形式;(2)人們使用新聞游戲更為重要的目的在于獲取新聞而非進行游戲,在新聞優先而非游戲優先的目的取向下,人們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方式獲知新聞信息,且其他獲取信息的方式更為快速高效,收受和閱讀的時間成本更為低廉;(3)新聞游戲最為關鍵的特征之一在于其參與性和交互性,這對于新聞收受者帶來的僅僅是使用體驗上的增量,而對于新聞活動本身并無實質性的突破,并不像數據新聞那樣拓展了人們認識現實世界的維度,也不像智能新聞那樣帶來了新聞生產與傳播方式的革命性變化,所以,新聞游戲所帶來的更多是產品形態上的改變,而不是認識論意義或傳播關系模式的變革,且這種產品形態上的改變很容易為其他新聞產品所替代。一言以蔽之,以前瞻性的眼光來看,僅僅帶來體驗和產品形態上增量卻又存在著高度可替代性的新聞游戲,恐怕并不能像本文開篇時所列舉的典型觀點所認為的那樣,從邊緣走向中心,成為新聞實踐發展的趨勢和重要方向。
進行視點轉移顯然是必要的。以往研究更多講的是新聞游戲相較于其他新聞呈現方式的優劣勢,某種程度上卻忽略了新聞游戲與游戲、新聞游戲與人之游戲目的間的關系。若是進行視點轉移,將新聞游戲放置于游戲領域進行審視,情況同樣不容樂觀。人們之所以進行電子游戲,主要在于獲取不同于日常生活之或歡樂、或幸福、或刺激的情緒體驗,“游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在空間上與平常生活的脫離”[19],電子游戲通過營造出虛擬性空間和場景,調動人們各種各樣的情緒。新聞游戲作為眾多電子游戲中的子類別,像其他各類電子游戲一樣,其所提供的主要也是情緒體驗,這意味著,人們在進行游戲時,具有多樣化的選擇,新聞游戲僅僅是多種游戲類型中的一種,因此具有非常高的可替代性。更為重要的是,當以娛樂為主的游戲與天然帶有嚴肅性的新聞結合而成新聞游戲時,其所具有的娛樂性往往在無形之中就被中和與削弱了。這種娛樂性的削弱,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新聞游戲在眾多電子游戲中,并不具備迎合消費者的優勢,新聞游戲仿佛戴上了“無形的鐐銬”,在與其他游戲進行市場競爭之時,從一開始便落了下風。
從游戲本身之發展趨勢來看,新聞游戲之前景也十分黯淡。受制于成本、時效性等因素的影響,新聞游戲的最佳類型選擇是輕量級的網頁游戲,以往較為典型的新聞游戲幾乎也都為網頁游戲,國外的例如《殺手資本主義》《刺殺肯尼迪》《預算英雄》等,國內的如《逃跑人的日常》《重走長征路》等。然而,在客戶端游戲、移動端游戲市場的競爭壓力下,“網頁游戲產品的吸引力正在降低,市場逐步萎縮,市場實際銷售收入不斷降低,用戶數量減少”[20],新聞游戲作為一種網頁游戲,它并不符合游戲市場的發展趨勢,在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競爭環境下,具有高度可替代性的新聞游戲并不具備發展成為潮流的特質。
五、結論及余論
需要重申的是,本文想要表達的核心意思,在于新聞游戲并不像一些學者所樂觀估計的那樣,會成為未來新聞實踐的重要方向,相反其自身的內在特征及否定性因素,這些特征與因素或許會致使其依然以零星的、散落化的樣態存在。
盡管技術是以一種革命性的面目出現,但技術遷移、適用往往要與其他社會因素、社會條件以及所應用領域的特征存在深度契合才能得以顯揚,并經得住時間的考驗。脫離具體語境,對技術功用的盲目樂觀解釋并非一種嚴謹認真的思考方式和研究取向。因此,當我們在分析新聞傳播活動時,務必要將其放置在具體的語境之中,充分挖掘其背后更深層次、更為豐富復雜的意涵空間,輔以反思性、批判性的立場,如此方能逐漸占有事物之規律,達成相對立體、準確、合乎實際的判斷與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