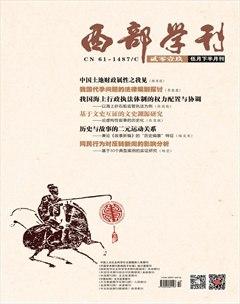民間歌謠中異性關系探究
劉繼輝
摘要:在中國封建禮教的約束下,女性的活動空間被明顯地壓縮在家庭的狹小范圍里,中國大量的歌謠反映了在封建禮教制度下女性心理、生活現狀,并通過與女性關系最為密切的情人、丈夫、兒子三位異性表現出來。通過對這類歌謠進行分析,有助于人們對封建制度統治下生活現狀、女性心理有更深入的認識。
關鍵詞:民間歌謠;異性關系;封建禮教
中圖分類號:J60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CN61-1487-(2019)010-0124-03
在中國封建禮教的約束下,女性的活動空間被明顯地壓縮在家庭的狹小范圍里,繁重的家務勞動幾乎消耗了她們所有的時間;而三從四德、男女授受不親等道德標準讓她們本已狹小的交際人群變得更加狹小。因此,在她們一生中,真正走近她們的男性很少,而能夠成功地占有她們心靈的男性更少。在那些鮮為人知的男性中,與女性關系最為密切的有三類:情人、丈夫和兒子,他們成為女性生活中男性世界的全部。盡管她們對這些男性或許充滿愛、或許充滿恨,或許僅是完成某種使命、或許是承擔某種責任,但是這些男性都從某些方面影響了她們,讓她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在中國民間歌謠資料庫中,大量的歌謠就深刻地反映了這一主題。通過對這類歌謠進行分析,有助于人們對封建制度統治下女性心理、生活現狀的認識。因此,對這類歌謠進行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她”與情人
在中國民間歌謠資料庫中,情歌所占的比重相當大,數量相當多,它是民間歌謠中最具有活力和情趣的一類。中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情歌的出現比較早,相應的搜集整理而成的著作也比較多。因此,情歌的影響也相當的廣泛;相對而言,情歌在藝術形式上相當成熟。從內容方面看,情歌多是以愛情為對象,描繪青年未婚男女相互傾訴愛慕之情和追求美好理想,但也有一部分是已婚少婦思念情郎的歌謠。如著名的《詩經·國風》就是古代情歌的結集,其中許多篇章是描繪青年男女相互之情的。鄭樵曾評價說:“風者,出于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復,故謂之風”。[1]朱熹也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處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2]2“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3]2因此,在她們看來,異性情人是介于哥哥與丈夫之間的男子,他們在某些情況下是女子追求的對象和少婦傾訴的化身,是她們理想的伴侶和精神上的依靠。“連情、送別、求友三種呼聲,都是社會的環境逼迫出來的,被迫而出的呼聲自然有不平的氣息,甚至于帶上放散的志趣和哀厲的長音”。[4]25如反映女子愛慕之情的歌謠:
其一,三根絲帶一線長,做根飄帶送小郎。
郎哥莫嫌飄帶短,短短飄帶仁義長
其二,愛人喲——,一心許你就許你,
玩笑不過我兩個,再再不信別的人。
情郎哥——,好花開在深山溝,
錯承為哥看得上,小妹出自清寒家。
情郎哥——,繡就香豆為哥帶,
冤家才是我兩個,縫就衣裳為哥穿。
如表達婦女的不幸情感經歷的歌謠:
其一,腳蹬板凳手爬墻,兩眼睜睜望情郎;
昨日為情郎挨了打,情愿挨打不丟郎
其二,高山有樹不通天,井中有水不通船,
妹今有話不敢講。妹喊情哥那樣連?
四兩黃金怨命薄,月在天邊手拿摩,
妹今雖好是人婦,千兩黃金不到哥。
從以上所列舉的情歌中可以看出,既有青年未婚女子愛慕、思念情郎的歌,又有已婚少婦哭訴不幸婚姻的歌,以引起青春年少的美好回憶。情人在她們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成為未婚少女追求幸福的目標和已婚婦女精神的寄托。在她們看來,“戀愛是神圣的,愛情是不減的;無論男女,結識了愛人,總要有戀愛的歌——情歌——來表示他們的愛慕之情。這既可以訴自己的心懷,又可以求情人的憐愛,是最快樂不過的事,至情感之發生,多是在兩方情感最興奮、最熱烈的時候自然流露出來的。因其感情真實,所以滿意的戀愛,歌中當然滿含著愉快,失意的戀愛,歌中當然充滿了血淚。所以就文藝而論,歌謠中的情歌,是男女們赤裸裸地把彼此戀愛的心情,真摯的,自然的,放情而歌唱出來的”。[5]132盡管在中國封建舊社會,這種行為有悖于倫理綱常;但生活現實的殘酷,尤其是對女性不幸遭遇的認識,深深地教育了她們,使得她們在無法擺脫封建禮教的約束下通過歌謠表述她們對愛情的追求、對美滿婚姻的向往、對封建舊社會不平等的抗議。徐行曾說:“民間文學中關于非正式夫妻(露水夫妻)戀愛描寫的情歌就特別多,而且很精彩,顯有向著這舊社會舊制度整個生命力量的總示威和總攻擊!民間之所以敢于毫不忌憚赤裸裸地藉情歌表現出自己內中的熱情和刻露的生活描寫,他們決不是如士大夫目光視為淫詞濫曲來謀傷風敗俗那樣而產生的。他們在那樣的社會那樣的經濟制度之下,不容他們不喊出沖破虛偽綱幕真生命源泉的情感來揭示現代社會之黑暗”。[6]
二、婦女與丈夫
從情感上講,丈夫本應是婦女最親近的人、最可靠的人,是她們物質上的保障者和精神上的依托。能夠成為夫妻本應是上天的緣分,是月老努力的結果,所謂“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他們的關系應該是和睦的,所謂“男主外,女主內”。這是一種理想的、美滿姻緣結合,是許多民間情歌中未婚男女執著的追求。如民間山歌中關于夫妻恩愛的歌謠:
其一,小黃盆,伴生菜,小兩口打架自分開:
你分力,我分外;你分枕頭,我分鋪蓋;
到晚上,沒氣沒火的又合起來!
其二,紡花車,是圓的,倆口打架是玩的。
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是仇人。
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是禍害。
這兩首歌謠是描繪年青夫妻恩愛生活的。從中可以看出他們是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姻緣結合,是許多未婚男女的追求。納蘭性德在《飲水詞集》中曾說:“人生得不到愛情的安慰,富貴有什么味兒?苦是得到有情人同居之愛,窮也窮的快活”。[7]所以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當街市酒,傳為佳話,成為后世追求美滿愛情婚姻的楷模。然而,對于下層的勞動婦女而言,這種“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夫妻關系是一種奢侈。徐行在《民歌中的愛情故事》中曾寫道:“納蘭氏和司馬相如再怎么窮,而他前半段的光陰,是泳洄于資產階級之中的。因此,他們的意識,至少亦是小資產階級意識;同時,也是小資產階級對于戀愛的見解。那民間窮夫妻的苦處,他們怎么領略得到?所以,他們的說話,應用于民間是不對的”。[6]下層民眾的夫妻關系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這對于封建社會壓迫下的婦女而言是一種生活的災難。下面幾首歌謠反映了下層民眾的夫妻現狀:
其一,十八嬌嬌三歲郎,夜夜要妹牽入房,
睡到半夜思想起,唔知是兒還是郎?
十八嬌嬌三歲郎,夜夜要妹抱入房,
等到郎大妹又老,等到花開葉又黃。
其二,小二姐走路快如風,走到她娘家的大門庭,
爹呀爹呀叫幾聲。你怎么給你閨女尋婆家,為什么一時不打聽?
前心長個大瘡,后心不住流膿,一臉黑油麻子,坑坑洼洼不平,
一頭羅圈禿瘡,不斷嘗嘗哼哼,前鍋后羅條半腿,實在不像人形。
其三,月奶奶明晃晃,開開后門洗衣裳。
洗又白漿又白,尋個女婿不成才。又擲色又摸牌。
其四,小煙袋樸穗多,打點酒,你去喝,喝醉酒,打老婆。
打死老婆你怎么過?使響器吹喇叭,滴滴答答再娶個。
常言道:“嫁狗隨狗走,嫁雞隨雞飛”。這是中國封建舊社會對女性婚后生活的一種約束,或是婦女對自己的一種心理安慰。現實生活的殘酷性超過了她們的想象。以上這些歌謠是反映畸形婚姻形式下婦女不幸情感經歷,或是描寫丈夫幼小的,或是描繪丈夫丑態的,或是反映丈夫荒淫生活的,或是描寫婦女被丈夫打罵遭遇的。這些歌謠是勞動婦女與其丈夫的感情記錄,是她們生活的真實寫照。造成夫妻關系不平等的原因是由于婦女經濟的不獨立而帶來的社會地位的低下。“經濟是注定男女間的戀愛關系,無論在新的社會或是舊的社會,終要男女兩方面,至少是一方面有錢,總能發生戀愛。兩方面倶有充分的經濟,那是不消說的。至于兩方面倶是無錢,這戀愛是不會成功的。女子拿出錢來倒貼漢子,和男子拿出錢來玩弄女子,這倶是一方面有錢是可以達到戀愛的……從這點社會的真實狀況來觀察社會問題,就明白了戀愛之處處受經濟支配,是一件無可否認的事實”。[6]戀愛如此,婚姻亦如此。建立在金錢基礎上的買賣婚姻無形中成為婦女不幸遭遇的罪魁禍首,而且婦女經濟的不獨立又直接導致她們在丈夫面前的不對等,遭受丈夫的百般刁難和虐待,從而出現了荒年賣妻鬻子的社會現象。
三、母親與兒子
婦女的三從觀念——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在民間歌謠中表現的特別突出。在與父、與夫、與子的三種關系中,婦女,尤其是鄉村的勞動婦女,更看重她們與兒子的關系。這種關系之所以表現的如此緊密,不僅是因為他們之間存在著血緣關系,還在于他們之間的養育之恩、與社會對男性地位的認可。所謂“養兒防老,積谷防饑”成為她們習慣性的認識。除此之外,中國自古以來重孝道的道德標準和歷史“舉孝廉”的道德模范也深深地影響了她們。然而,生活的現實一次又一次擊碎她們的愿望,使得她們成為兒子結婚后的悲劇。劉經庵在《歌謠與婦女》中曾寫道:
婦女的三從——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我們由歌謠中已經看得出從父從夫的實況了,今再試看一看夫死從子如之何。中國自古是重孝道的,當未嫁時,雖會受父母的輕視,既嫁后又受丈夫的打罵,若是養得兒子,總可望之孝養以慰余年的。所以中國的婦女多有青年亡夫,而終身守子不嫁者,此固因禮教使之如此——守節——亦實因將來有所指望而然的。那知含辛茹苦的把兒子熬大成人后,竟至“娶了媳婦忘了娘”呢?我們看以“娶了媳婦忘了娘”為母題的這首歌謠之普遍,足可知中國婦女的“夫死從子”的失敗了。[5]101
“娶了媳婦忘了娘”為母題的歌謠普遍流傳在中國的廣大地區,如河南、山東、安徽、天津、江西、廣西等地區。如河南衛輝的歌謠:
小麻雀,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扔到山溝里,把媳婦擱到炕頭上。
他娘要吃焦燒餅,那有現錢填還你;
他妻要吃五香梨,清晨起來去趕集;
一頭擔哩是小麥,一頭擔里是黃米;
到了集上去換錢,下集買哩五香梨;
手巾包,手巾提,到家里,拿起鋼刀削梨皮;
涼水缸里提三提,怨怕鋼刀鐵銹氣。
雙手捧起叫賢妻,叫聲賢妻你吃吧。
如江西南昌的歌謠:
麻鵲子,尾巴長,娶了老婆不要娘,
娘是路邊草,還是老婆好。
如流傳在廣西的歌謠:
紅公雞,尾巴長,討了老婆不要娘。
娘講話不算數,老婆講話句算句。
娘要吃個糖燒餅,他說無錢懶得理。
老婆要吃甜沙梨,早早起來去趕圩。
以上這些“娶了媳婦忘了娘”為母題的歌謠反映了中國勞動婦女“養兒防老”觀念的失敗,也表現出婦女悲慘遭遇的終結。劉經庵認為,對于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中國重視孝道而不重視夫婦之愛”的結果。他在《歌謠與婦女》一書中寫道:“或有人說:‘歌謠中所詠的‘忤逆子完全是因為中國素重孝親之道,而不重夫婦之愛的緣故。歌謠中所云,若移入西國,就不算一回什么事了。要知孝思與愛情常是沖突的,愿乎此必失乎彼,二者不能得兼。我們受過新思潮的洗禮的人,不能以‘忤逆子加罪于愛妻之人的。此說固為有理,不過我想西人雖重視夫婦之愛,亦并非不顧念其母,自有他敬母之道”。[5]101與此同時,他也認識到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而真正使得婦女老來凄慘的原因是由于她們沒有自己的生活保障或是經濟保障。夫死從子之說不僅是指在道德標準方面的依從,更指出的是婦女在經濟方面的依靠。經濟的不獨立或沒有經濟的保障是婦女老來受欺于兒子兒媳的最根本、最實質的原因。經濟的過分依賴使得她們只能在凄苦中度過余生。因此,婦女老來的凄慘生活與其說是兒媳挑唆兒子的結果,不如說是封建社會“三從”道德標準在物質方面對婦女進行限制的結果。
參考文獻:
[1](宋)鄭樵.詩經奧論·風雅頌辨[M].沈陽:吉林出版集團,2005.
[2](南宋)朱熹.詩集傳·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朱熹.楚辭集注·卷一離騷序末按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羅香林.粵東之風[M].上海:上海北新書局出版,1928.
[5]劉經庵.歌謠與婦女·緒論[M].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
[6]徐行.民歌中的戀愛故事[J].社會月報,1934(2).
[7](清)納蘭性德.飲水詞集[M].謝秋萍編校.上海:上海大光書店印行,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