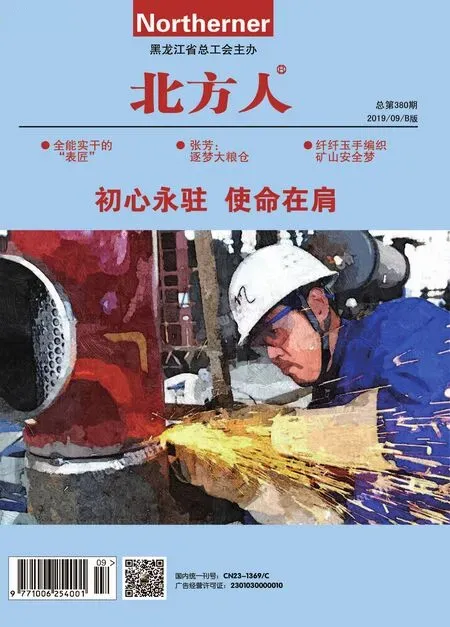女性之光:吳貽芳
文/芝士咸魚

這位極富盛名的民國女性終身未婚。少女時期家逢巨變,被新時代的滾滾浪潮裹挾中一路前行,她從伶仃孤女成長為全中國第一屆女大學生、第二位大學女校長、第一位女副省長。
堅韌與優雅成為她的戰袍,她仿佛以己一身承載了和“女性”相關的所有榮耀。
女性之光
1945年,中國作為反法西斯同盟國家出席聯合國制憲大會。國內派去的各黨派代表包括董必武、宋子文在內一行十人,僅有一名女性代表立于其中——無黨派教育家吳貽芳。
各國代表紛紛發言,輪到中國代表時,吳貽芳身著紫絳紅色絲質旗袍,輕移蓮步,緩緩走上講演臺。她以中國為例,講述維護和平的重要性,語氣不卑不亢毫不怯場,只一身氣度足以令人凝神傾聽。
演說完畢,背后各國國旗迎風飄揚,空氣中充斥著難以言喻的肅穆感。吳貽芳莊重地在《聯合國憲章》中簽下自己的姓名,她是歷史上第一位在《聯合國憲章》中簽名的女性。
她的端莊典雅也迅速征服了羅斯福總統,被冠以“東方智慧女神”之名。
吳貽芳的淡雅氣質不僅征服了美國人。在國內,她也享有相當聲譽。作家冰心見過她多次,直至冰心晚年,仍然難忘吳貽芳當年梳黑色發髻身著優雅合身的旗袍款款走向講臺的姿態。
冰心第一反應竟是訝異:“我驚慕于她端凝和藹的風度,在我們女大的講臺上,從未有過如她這般杰出的演講者。”
時光流逝,上世紀四十年代,吳貽芳與冰心都曾從政,吳貽芳常主持參政會議,冰心是坐在會堂臺下仰望她的參議員。縱使會議進行到最容易導致混亂的辯論環節,吳貽芳也總能不慌不忙地指點先后順序,似乎對參會人員的姓名和背景都了然于心。
間或,老一輩革命家董必武在臺下入座,向冰心低聲感嘆:“像這樣精干的主席,男子中也是少有的。”冰心在一旁聽著,內心激蕩,生出同為女性的自豪感。
70年代末,吳貽芳的母校美國密歇根大學校友會頒布了一項“和平與智慧女神獎”,其中一年頒給了吳貽芳。致辭中,時任校長史密斯十分欣賞她,稱:“這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進步的女政治家”。
此時吳貽芳已至耄耋之年,拖著一副病軀遠赴美國接下這枚銀質獎章。她穿著剪裁得體的旗袍,有一雙飽含風霜的眼睛,銀發如霜仍姿態優雅。吳貽芳張口便是一段流暢英文,咬字精準且有獨特韻味。
她接過獎杯:“這不僅是美國人民給予我個人的榮譽,也是給予我的祖國、我國人民,特別是我們中國婦女的榮譽。”
在座人員全體起立,掌聲雷鳴長達數分鐘之久。
坎坷前行
在存留下來的吳貽芳舊照中,不難發現,吳貽芳體態纖瘦,常穿暗色衣裙,既有舊式女子的端莊,又兼具新女性的斯文雅致。
無法忽略的是,她極少展露笑顏。這或許源于她的身世。
1893年,吳貽芳生于湖北武昌吳家宅,家中行三,出生時恰逢凜冽寒冬,臘梅飄香,父親便以“貽芳”為其命名,以“冬生”作為別號。
吳家屬于舊室官宦家庭,父親是候補知縣,母親是溫婉嫻雅的大家閨秀,在吳貽芳仍處于稚子之齡便為她纏足,作新月狀。
吳貽芳對此并不認同,比起那些閨閣消遣,她更希望如同父兄同樣接受正統教育,在舊社會中浸染多年的吳父不以為然。
吳貽芳與姐姐吳貽芬奮力抗爭,據說是通過兩人以吞金了結生命做脅迫,父母方才無奈妥協。
好景不長,1909年,吳貽芳剛及二八年華,家中突逢變故。坊間對此說法不一:有人稱吳父被上司當作公款挪移的替罪羊,被迫投江自盡;也有人稱吳父是因不適應時下風云變幻,局勢不穩,心灰意冷下了結余生。
舊式家庭中,父親的角色代表著支撐。父親去世三年,兄長也因吳父逝世而無法繼續學業,又無法找到滿意的工作,郁郁不得志下選擇投江自盡。弱柳扶風的吳母接連痛失夫與子,她無法接受此等打擊而撒手人寰。
在為母親守靈的夜晚,當初一同與父親為進學奮力抗爭的姐姐貽芬悲痛之下也選擇懸梁自盡。
對于吳貽芳,當初失去父親的痛楚猶在,又接連失去母親與兄姊,此時,她還是個十幾歲的小姑娘。同齡人正恣意享受年少時光時,她卻需要擔起一個家庭的重量,如果這還能稱上一個“家”。
悲慟與沮喪撕扯著這個年輕姑娘,她在日記中提筆寫下:人生的不幸幾乎全集中到我身上,我真是哀不欲生。
姨夫將她接回家中,吳貽芳也考入金陵女子大學,四年苦讀,她成了金陵女子大學也是中國第一代獲得女子大學學士學位的五名畢業生之一。
一腔悲痛仿佛被寄放在學業上,吳貽芳臉上卻再難出現笑容,寡言少語。
生活本平靜無波,她因口語流暢被推薦去赴美留學,直至時任澳大利亞總理來學校演說,臺下聽眾足四千人,這位總理言行間不乏對中國的歧視色彩:“中國經濟落后且人民無知,政府無能,盜匪遍野……上帝賜給我們的資財,都被那些不開化的野蠻人,白白地浪費掉……”
縱使修養上佳如吳貽芳,聽到此處也勃然大怒,她連熬整夜撰寫出回擊澳大利亞總理的文章,在華人留學生圈看似平靜的生活仿佛投入一粒石子,人人都在為她叫好。
此時適逢母校金陵女大來信,聘請她擔任母校校長。吳貽芳時年35歲毅然回國投身教育,只回復寥寥數語足見決心:“論文已畢,考試及格,定期回國。”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位就任校長一職的女性。就職典禮上,不乏宋美齡在內的數百位來賓,座無虛席。吳貽芳站在演說臺上,仍是以往的溫柔語調,一字一句鏗鏘有力:金陵女子大學的目的只有一個——造就為社會所用的“女界領袖”。
成為校長
1930年代,年輕姑娘之間若是暗暗較量,早已不再攀比自己的家境、容貌等俗物,這些遠比不上就讀金陵女子大學所帶來的榮耀。倘若拿到吳貽芳手簽畢業證書,想去國外知名大學進修也并非難事。
入校新生需要闖五關斬六將,在層層選拔中脫穎而出,還得接受一系列儀表檢查。
章太炎與張治中也曾將愛女送入其中,這本是上流社會的閨秀名媛才能通行之地,可自吳貽芳就職以后,金陵女大開始不分階級,向社會全面招生,若有學子生活捉襟見肘,便在學校為其提供工作機會與獎、助學金。
吳貽芳在此就任校長長達23年。她立下金陵女子大學的校訓:厚生。
吳貽芳用行為作出表率。
執教期間,吳貽芳提倡每位教師帶領近十位學生以小組授課的形式,從而解決學生在成長學業中遇到的困惑。她本人言傳身教,除去測試期間外幾乎不曾離開過課堂。
然而每逢測試,教師們只需為學生發下考卷便可悄然離去。沒有一位教師會留下來監視學生是否作弊,吳貽芳執掌金陵女大的幾十年中,無一例外。
吳貽芳就職期間,她曾定下一條校規:不收已婚學生,在校生若是結婚就得自行離校。在她看來,是否踏入婚姻殿堂雖是個人自由,但結婚以后,尤其是當時家庭關系中處于劣勢的女性群體,在多數情況下只會陷入家庭瑣碎當中,于學業上毫無幫助。
規矩雖定,她卻并非死板而不知變通的人。某天吳貽芳在校園內散步,發現窗戶下有一把椅子,細究之下,原來是有學生鋌而走險,爬窗外出。眼見勢態如此,吳貽芳也不恪守己見,她明白了“禁不如疏”。
她將學校內一間會議室重新裝修,造出一些供情侶相處的半封閉狹小空間。在規定時間內,學生們可以自由接待自己外來的男友進去聊天。為此,金陵女大的學生還造出一新詞“Local”,意為“love+call”縮寫。女學生們也常互相調侃:“你的Local來嘍。”
有位名為曾季肅的已婚女子從朋友當中聽聞吳貽芳此人,提筆給她寫信,信中坦誠自己已有兩位子女,但為擺脫封建婚姻的束縛,她仍想讀書。
雖然校規既定,她卻不想讓任何一位一心追求教育的女性失去機會,吳貽芳思索良久,終是應許。
吳貽芳并不知道自己當初的選擇如同蝴蝶效應般,在中國教育事業上扇動了一下翅膀,曾季肅畢業后也追隨她的步伐,后來創辦了滬上知名的南屏女中。
時下,女子入學機會仍是寥寥,雖然有零星女校興辦,然而就連梁啟超這樣的進步人士也認為其目的在于“讓女性更好地相夫教子”上。
吳貽芳的教育理念全然不同,她實施“人格教育”,將女性放在與男性完全平等的位置上教育。文科生畢業前要選修理科知識,理科生也同樣需要研習文科學類。
如今看來理所應當的事情在當時卻能稱平驚雷,金陵女大的畢業生們在擇業中擁有了不可比擬的優勢。吳貽芳關于教育的一系列措施令周恩來也極為賞識:我們黨內要是有個像吳貽芳這樣的學者該有多好。
在吳貽芳的多年校長生涯中,曾有人提議金陵女大不分性別,男女混招,吳貽芳總是全力反對:“若真如此,女子永遠無法在學校中發揮領袖作用,這樣,我們怎么能培養出女性領袖呢?”
在此理念之下,金陵女子大學為社會輸送了999名畢業生,被譽為“999朵玫瑰”。
赤子之心
民國時期,流傳著一句笑談:若說宋美齡是民國第一夫人,吳貽芳則是民國第一小姐。
二人同屬時下杰出女性,宋美齡毫不掩飾對前者的欣賞,曾多次致電邀請吳貽芳做教育部長。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此職位的重要性不必贅述。然而宋美齡多次致電得到的回應都是“吳校長人不在”這類推辭。在吳貽芳心里,她只專注于想把金陵女子大學辦好。
她從不曾貪慕名利,據學生回憶,吳校長常年住在一間不到15平的小房子里,坐黃包車,穿著打扮也以樸素為主,工資與酬金大多轉贈予一些經濟狀況堪憂的師生。
到了更為動蕩的年代,她的專車也被取消,時常踩著一雙小腳通過擁擠的公交車出行。當時常有人在南京3路公交車中看到一個小腳老太太顫顫巍巍地擠在人群里。
吳貽芳此時已至花甲之年,大可以選擇一語不發明哲保身。可她多次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思考與想法,直呼當時的某些政策與現象簡直“荒謬”。有人擔心她因此惹上禍端,上門勸她。老太太先是溫言謝過對方好意,只答:“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吳貽芳此生都未改初心,堅持自己的教育理念。
待吳貽芳晚年后,曾經的學生們自愿輪流排班來照顧這位老校長,她一生可謂傳奇,桃李滿天下。可照顧過她的學生回憶起老校長的生活瑣碎時,總結成一句:她的生活簡單,從不要求什么。
赴美留學期間,吳貽芳那雙早年纏過的小腳曾令同學們饒有興致,她并不以此為恥,只宛然一笑:這是我母親心血凝成,是上帝送給我的禮物。
1985年11月10日,吳貽芳安詳地閉上了雙眼,這雙被視為陋習的小腳陪伴她輾轉于國內外,陪伴她完成了“厚生”的教育理想。直至去世前一刻,她心心念念的仍是復辦金陵女大。
兩年后,在曾經的校友疾呼下,南京師范大學恢復并成立金陵女子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