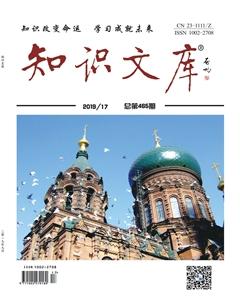我們在讀古詩的時候究竟在讀什么?
楚遵星
引言:高考古詩鑒賞試題是年年必有的,但學生們的得分率卻年年都是很低的,筆者認為,我們此時最需要做的應該是沉下心來,埋下頭來,過分的功利意識淡下來,回歸一名語文人的本心,去探究備課思路的更多可能性,力求從根本上找到提升學生古詩詞鑒賞能力的方法。
從教近十年來,白居易的《琵琶行》已經被翻來覆去講過太多遍,家常課、公開課、比賽課,每次都沿著前人鋪設好的教學思路應對,甚至從來都沒思考過為什么非要如此,有幾次講課居然還得到了聽評課老師的滿堂喝彩,讓正準備伴著下課鈴聲走下講臺的筆者很是局促和茫然。最近一次籌備比賽課時,腦海中卻突然冒出一個大大的問號,并且久久縈繞不去:古詩詞閱讀,我們究竟在讀什么?
高考古詩鑒賞試題是年年必有的,但學生們的得分率卻年年都是很低的,縱然拼勁力氣,使盡渾身解數,甚至將詩歌分門別類,試題訓練精準到題干中的每一處關鍵詞,答題模板具體到每一個專業鑒賞術語,依然無法改變此現狀。于是學生們困頓了,平時講課所講內容與考試答題似乎完全割裂了,于是作答過程東一榔頭,西一棒槌,不著邊際,僅靠運氣和造化求取零星得分。作為普通教師,這是很讓人惆悵的事情,有時甚至會不覺長嘆一聲:這群孩子已經徹底喪掉對傳統古詩詞的感悟能力了。而作為一名有情懷的語文人,則不免心中隱隱作痛,不惜為學生四處尋方問藥,疲于奔走。
筆者認為,我們此時最需要做的應該是沉下心來,埋下頭來,過分的功利意識淡下來,回歸一名語文人的本心,去探究備課思路的更多可能性,力求從根本上找到提升學生古詩詞鑒賞能力的方法。
1 讀懂詩意
古詩詞的內容其實是古代人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理解一首詩的大意,便是讓我們的靈魂透過歷史的迷霧窺探古代社會生活以及古人情感世界的最好方式。《琵琶行》作為一首敘事詩,以人物之間的關系為線索,把握住作者敘事的來龍去脈不甚困難,但仍需在前期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包括字音疏通,字詞含義把握,敘事情節梳理,主要人物關系厘清等等。經過一系列工作做下來,我們發現,該詩歌的內容無非就是一名仕途失意的詩人偶遇一名淪落江湖的歌妓,因彼此命運相似而惺惺相惜頓生感慨的故事,其實在詩歌小序中已經敘述得很是清楚。這樣一來,倘若作者只是為了敘說一段故事而作此詩歌,似乎根本沒有必要,就算作者試圖用更長篇幅充實完善故事的細節,展現生活更多風貌,也大可選擇與小序文體相仿的敘說方式。
由此我們發現,讀一首詩,僅僅讀懂了它的大意,似乎并不能讓我們明白它所存在的更多價值,也不足以讓我們明確詩歌這一文體本身的意義所在。
2 讀懂情志
《尚書》有云:“詩言志,歌詠言”,《毛詩序》中說:“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不足故詠歌之”。這些對于詩歌的理論闡釋,讓我們了解到詩歌存在的根本價值其實不在于敘事本身,也不在于描寫景物和人物本身,而在于通過敘事和描寫寄寓的作者心志。作者心志的表達往往來自于作為人類個體最本真的情愫,他可以有,我們也可以有,于是彼此間感情的碰撞和共鳴便成了一種跨越千年的心靈對話。正如錢穆先生在《談詩》中所言:“我哭,詩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詩中已先代我笑了。讀詩是我們人生中一種無窮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詩中有,讀到他的詩,我心就如跑進另一境界去。”讀一首古詩,作為現代人的我們來說,站在對詩歌大意理解的基礎上,反復吟詠,去感受詩人所營造的情感世界,揣摩作者所寄寓在詩中的濃烈情志,讀詩的趣味性便會增添很多。
《琵琶行》中作者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一句話,揭示了本首詩歌的主旨所在,一位是曾經風光無限的廟堂老爺,一位是曾經風華絕代的教坊歌女,而今,廟堂老爺被發配江湖之遠,教坊歌女也早已是門前冷落,命運起伏的高度相似,讓作者與琵琶女心靈產生無限共鳴,甚至不惜互訴衷腸,將自身經歷和盤倒出,分享給彼此。作為當代人的我們,作為社會中最普通的一員,經歷、學識、感悟能力或許并不足以去理解兩位人生淪落者的悲戚有幾多深,但起碼會讓我們不由聯想起自己人生所遭遇過的相似經歷,換言之,它會觸發我們心中本能的共鳴點,并且帶著這種共鳴的情緒融入到詩歌所創設的情境之中,去感受那種知音難覓的苦楚,知音覓得之后的涕淚橫流。這種情境的融入,即使沒有讓我們跟著聲淚俱下,也會讓我們對于人生的思考更多了一層意義,豈不妙哉!
3 讀懂情境
說到情境的融入,我們不得不把關注焦點轉移到本首詩歌的環境描寫上來。倘希冀讀者能夠融入自己筆下的一種情境,必須先創設一道引入之門,換言之,詩人必須有意借助某些物象(即“意象”),營造一種氛圍,讓讀者書卷一入手便像置身其中。《琵琶行》中一開篇便以江月為背景,創設出一種江頭送別的蒼涼凄清氣氛。讀者反復吟詠,情境便會愈陷愈深,最終將自己完全融入其中。此后,“江月”這一意象幾乎貫穿了整首詩,諸如:“別時茫茫江浸月”“繞船月明江水寒”,“江月”不去,讀者便難以從情境中脫身而去,詩歌情境牢牢抓住了讀者的靈魂,而詩人與琵琶女的惺惺相惜便是和這情境相襯相生的,景為情染,情借景重,這便是好的詩歌魅力所在。
4 讀懂文法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過自己的詩歌創作理論:“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詩歌創作必須以感情為根基,以具有實際意義為目的,它們正像是植物的根和果實;而形式上的語言和聲韻只是苗和花。只有根深,才能葉茂,開出鮮艷的花朵,結出豐碩的果實。這個比喻十分形象地說明詩歌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即內容是詩歌的根本,形式必須為內容服務。
《琵琶行》中歷來被人稱道的便是其中對于音樂描寫的章節,詩人不惜用一連串的比喻來刻畫不同的樂調,同時還運用大量擬聲詞加強模仿的效果,像“大弦嘈嘈,小弦切切”等,非常傳神地將不可視見不可觸摸的音樂具象化了,同時又用樂調的變化暗示出琵琶女甚至詩人自己此時心理情緒的波瀾。這所有的精彩,在讀者看來是耀眼的,是具有高度審美價值的,是文采斐然的,是值得陶醉和驚嘆的,甚至千古以來是無出其右的,是后世學習音樂描寫的最佳摹本。
但在詩人自己看來,這似乎并不值得大肆張揚,因為這并非本首詩的真正內蘊所在。詩人此番苦心,更期望的或許是,后之覽者能夠更投入地因聲求氣,吟詠詩韻,通過感受詩歌語言本身的節奏和文法特點,去領悟詩中彌漫的感傷氣韻。讀而出聲,體會詩文的聲韻之美,通過聲情并茂,韻律和諧地誦讀,去更深層次地領悟詩人所寄托地情志。這或許也是詩人選擇用“歌行”這種節奏流轉自然,可歌可唱的詩歌文體的緣由吧。
5 讀懂詩韻
這是目前教學中落實情況最不理想的方面。很多時候,我們僅僅流于讓學生讀、背,卻忽視了詩歌誦讀時的最佳方式。流行歌曲能夠流行,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是旋律,二是歌詞。古詩詞的存在價值也不僅僅在于它的文字層面。適時引導學生掌握基本的聲律知識和節奏把握技巧后再加以吟誦,能夠更好地還原古詩詞的魅力以及詩人本身的氣度,從而引導學生從情感態度價值觀上得到指導,從語文學科核心素養上得到提升,正如錢穆先生所說,文學是人生最親切的東西,而中國文學又是最真實的人生寫照,所以學詩就是學做人的一條徑直大道。
綜上,我們在講解古詩詞時,務必先引導學生掌握讀詩由淺入深的一般規律,循序漸進,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陶冶學生審美鑒賞水準,而非一味地灌輸式傳達。引導學生學會品讀一首古詩,恰如酒師教給他人品酒,無法替代,無法強迫,唯等口熟心熟爾。
(作者單位:濟寧市實驗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