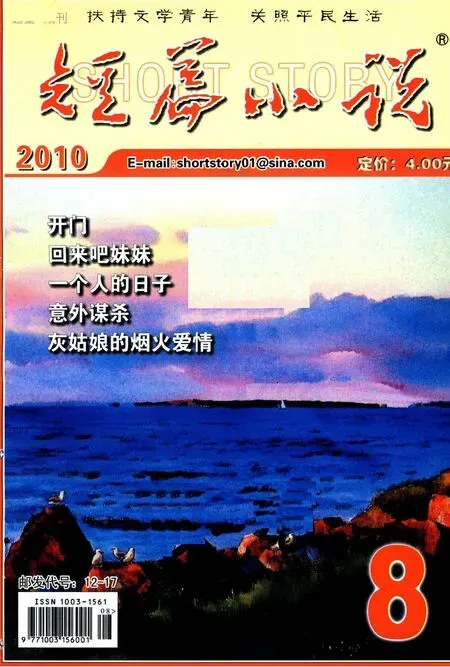太陽和兩個茭瓜
2019-09-21 01:47:20◎徐頗
短篇小說
2019年7期
◎徐 頗
1
昨天,她最后一顆牙掉了。
這顆牙她一直不讓拔,在嘴里悠蕩了很多年,從我記事開始就在那悠蕩。她用左邊的臉貼我,右邊用舌頭把牙往外頂,這樣就能把下巴收緊些。

“小福子,看看‘老爺兒’都鉆云彩里了,別出去跑,就和太姥說話吧。”她說的“老爺兒”就是太陽的意思,從她兜不住風的軟嘴唇里說出來特有意思。她說的小福子也不是我,家里沒別人的時候她總是這么叫我,時間長了我也就不計較了。
開始的時候我總是糾正她:“我不是小福子,我叫衛東,保衛偉大領袖的意思。”我糾正她,是因為她叫的那個小福子顯然是另一個孩子,一個舊社會的孩子。
那時候我能熟練地數到一百個數了,這很重要,明年我要上學去。她應該活不到我上學的時候,因為我媽每天上班前都偷偷叮囑我:“太姥糊涂了,就讓她叨咕吧,別和她吵架。要是她睡著了幾個小時也不醒,你就搖搖她。要是還不醒你就出去找個大人來看看,前院宋奶天天在家。”
“小福子,你咋穿個小褂呀?我給你的棉坎肩呢?”
“你老糊涂了!大夏天的誰穿棉坎肩?你才沒給我棉坎肩呢,我是衛東。”
“還是小啊!我把坎肩給你穿還讓我爸踢了一腳呢。你咋一天就給刮破了呢?下大雪刮大風你可咋整?”她眼睛看著窗外,看出去老遠老遠,我想起了我媽說過別和她吵架,也就不犟了。
“又要開跋了,待得好好的。唉!白凈凈的干啥當兵啊?家里沒地種嗎?這三口大水缸,你一個人得挑啥時候去?有伙計呢,讓他們挑去唄。……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