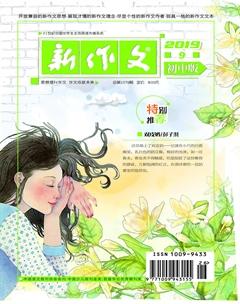北朝 北朝
朱以撒
平時翻看史書,總覺得對北朝的描述不及南朝那么熱烈和幽默。北中國從來都是匈奴、鮮卑、羯、氐、羌等部族混戰廝殺的兵家之地,連年兵燹而致赤地千里。地域和氣候熏陶了馬背民族的尚武精神。他們不像南朝人“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而在沖鋒陷陣上大顯身手。這樣的部族,文化品位又該如何……
坐在龍門石窟對面,從窗口隔著伊水遠望這座石山:石窟靜靜地矗立著,一臉冷峻和硬朗,沒有絲毫的粉飾和張揚。北方雖石質優良,經過千年的霜雪浸洗,多處不免殘破漫漶,顯出一副滄桑之相,但是它的崢嶸氣象和恢宏格局,分明儲滿了永恒。
北朝人似乎對堅硬的石頭有著天生的情緣,他們屬意石頭,并不是即興而發隨意而止。哪兒大寫意,哪兒小精工,都條理清晰工寫分明。南朝文人對石頭也有感情,吟詠石頭的詩章也作了不少,只是他們不愿“動手”。賦詩之余,南朝文人對石頭還有另一種嗜好,即采石煉丹化為腹中之物,企盼藥石空腸過而得長生不朽。北朝人對石頭采取的是最實在的態度。在南朝人隔江清談“般若”“涅槃”時,北朝的偶像崇拜、向往凈土的夢想又一次在石頭上化為現實。在北魏至唐一百五十年間的十萬余尊造像中,北魏造像就不下三萬尊。我凝神微觀這些造像的細部,用手撫摸其中精美的線條時,手眼都有些發潮。
鐫刻在龍門石窟古陽洞頂的北魏《廣川王造像記》,既方樸又靈秀,既縝密又疏朗,雍容銳利又干脆利落,使人驚嘆刻手刀工的簡凈。石頭可不好擺弄,我們可以想見這樣的場景:高高的洞頂,鑿刻者搭架登高,仰臥行事。一手握釬一手執錘,敲擊中火花迸濺,亂石撲面,才鑿出這精致的五十個字,可不像南朝文人飛觴賦詩那么浪漫。冰天雪地里,饑寒交迫中,剔除一方方頑石,磨禿一把把鑿頭,冬去春來雪化冰消,佛陀終于露出了笑靨。
北朝人刻石根本沒有想不朽、想永恒,所以他們面對堅硬的石山會充滿喜悅;他們也不覺艱辛,所以眾多的造像都流露著佛陀慈祥平和的神采。他們造石窟、建寺院,拜佛求福是主旨,而把石窟當作藝術殿堂來審美,那是后世文人的發揮,并非北朝人的本意。
我們在驚嘆北朝石窟的藝術性時,只好為湮沒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唱一支挽歌了。從此岸到彼岸,也許我看清楚了:南派的江左風流,疏放妍妙;北派的中原古法,厚重蒼茫。各極一時之盛,難以論說高下。
(選自《紙上春秋》,同心出版社)
★賞析:
本文運用對比手法表現南北朝文化上巨大的審美差異,南朝風流瀟灑,疏放妍妙,北朝純厚樸質,厚重恢宏,在對比中突出了作者對北朝藝術由衷的贊美之情。結尾反復強調“還是北朝”凸顯了文章主旨——能體現生命本質的藝術最具有生命力,同時照應題目,呼應開頭,首尾圓融。文章具有濃厚的文化氣息,語言典雅富有詩意,形象可感又意蘊豐厚,表達了作者對藝術的獨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