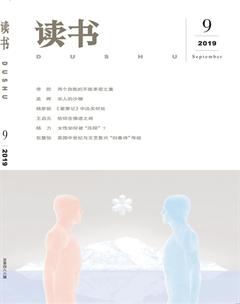宋人的沙糖
孟暉
笑話最能反映一個時代的日常生活狀態。你講笑話的時候,內容必須是目前最普遍的現象,這樣聽笑話的人才能馬上明白(“秒懂”),然后反應出來里面的寓意,被逗笑。如果對宋朝的人講一個涉及汽車的笑話,人家肯定笑不出來,因為根本不懂你在說什么。反之,古人的笑話,由于時過境遷,我們也難以發笑。
北宋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里有一則笑話:
頃有秉政者,深被眷倚,言事無不從。一日御宴,教坊雜劇為小商,自稱姓趙名氏,負以瓦瓿,賣沙糖。道逢故人,喜而拜之。伸足誤踏瓿倒,糖流于地,小商彈指嘆息日:“甜采你即溜也,怎奈何!”左右皆笑。俚語以王姓為“甜采”。我就笑不出來,完全搞不清楚笑點在哪里。但是,這個笑話卻有著重要的史料意義,它告訴我們:在《澠水燕談錄》成書的年代(一0九五),也就是北宋時期,普通人日常使用的糖,習慣稱為“沙糖”,乃是糖漿狀態,可以四處流淌。當時的街市上會有游動的賣糖小販,其形式則是背或擔著瓦罐,罐里盛滿漿液形態的沙糖。那時,這種漿狀的糖是如此普遍,百官熟悉,伶人熟悉,甚至生活在宮廷內的天子都知道,因此會在御前宴會上演出假扮賣糖小販的喜劇小品,并且利用糖漿在地面上亂流的現象制造噱頭,那笑話的意思似乎是,一旦王姓權臣沒打招呼離開——溜走,皇上立刻就六神無主拿不了主意了。
我曾經寫過一篇小文《糖史上的蔗漿時代》,討論唐代以及唐以前的時期,蔗糖的主要形式是“蔗漿”,但是,當時我誤以為進入宋代以后,固體的砂糖便成為主流。直到讀到這則笑話,才意識到,以為宋人消費以固體蔗糖為主,是一個普遍流傳的誤會。
造成這一誤會的主要原因無疑是《糖霜譜》。王灼的《糖霜譜》是一部嚴謹驚人的科學史著作,由之后人知道,在北宋時代,固體的糖已經出現了。但是,很多人望文生義,對這一著作有很多誤解,包括以為“糖霜”指的是我們今天習慣看到的砂糖,即細粒狀的糖粉。其實,王灼講解得非常清楚:糖霜之稱,是指這種產品經歷結晶的過程,近似自然界中的結霜現象。至于糖霜的形態,則是大大小小的不規則團塊,所以宋人亦稱之為“糖冰”或“冰糖”(楊萬里:《冰糖詩》)。
當時甘蔗種植在宋朝的境內非常普遍,質量也很好,然而掌握了糖霜技術的地方卻不多,僅僅局限在福唐(位于福建)、四明(浙江)、番禺(廣東)以及廣漢、遂寧(二者皆在四川),可是前四個地方都產量小,質量也遜色,因此實際上只有遂寧一處為主力。即使在遂寧,也只是集中在傘山周圍,這里制糖霜的家庭作坊稱為“糖霜戶”,其中大致有三百家的出品為優等貨,大戶每年能動用三百多只缸制糖,而小戶不過只有一兩缸。另外還有將近百家制糖作坊,但是只能生產中下等的產品。附近雖然也有很多甘蔗田,那里的農戶們卻沒有掌握做糖霜的技術,只能把甘蔗汁加工成糖水,作為原料賣給傘山前的制糖坊。
這些糖霜戶所掌握的技術相當簡單,無法完全控制生產過程,導致每年的產量不穩定。從耕田到曬霜,歷時長達一年半,但結霜的過程卻難以預測,最終可能一缸出幾十斤乃至上百斤糖霜,也可能完全沒有任何糖霜形成,對于產戶來說帶有運氣的成分。
故而,包括遂寧在內,幾個產地每年生產糖霜的能力非常有限。宣和初年,要求遂寧每年進貢數千斤糖霜,結果給當地造成了極大困擾,將近半數產家破產,到王灼寫《糖霜譜》時還沒有恢復元氣。在最大的生產地遂寧,尚且無法承受一年多出幾千斤固體糖的負擔,那么其他四個地方只會更弱。由此可以推測,全宋境內每年固體糖的產量非常之低,完全不可能覆蓋整個社會的消費需求。另外,據《糖霜譜》介紹,當時邊境以外的很多地區都出產好甘蔗,但卻沒聽說有糖霜的生產,連王灼都覺得奇怪。這就意味著,對于宋代的大多數人來說,如果有能力消費蔗糖,也很難享受到固體糖。
《糖霜譜》記錄了當時糖霜與沙糖的制作工藝。前者的生產過程辛苦漫長,而且出品率很低,大致是把甘蔗榨出的汁在火上熬,熬到類似麥芽餳的黏稠度,然后把若干竹條插在大缸里,再將熬好的蔗漿倒入,以竹藤編的蓋子罩合。接下來,便是等著蔗漿析出結晶,附著在竹條以及缸壁上。到農歷五月,把這些結晶取出,這個程序稱為“瀝缸”。“瀝”出的糖晶再經陽光下暴曬,才得到最終的糖霜。不過,一缸糖漿不會全部結晶成霜,會留下相當比例的“糖水”,也就是余漿。這些糖水有兩種去處,直接賣掉,“或自熬沙糖”。
很清楚,在王灼時代的制糖體系里,沙糖與糖霜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商品,前者絕對不是固體的糖。南宋醫學家寇宗夷《本草衍義》中同樣肯定了這種區別:“甘蔗……石蜜、沙糖、糖霜皆自此出。”并說明沙糖是“紫黑色”。實際上,王灼非常了不起,在卷二清楚地勾勒了中國古人在蔗糖消費上的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蔗漿,乃是甘蔗壓榨成的汁。第二個階段為“蔗餳”,即經過初步簡單加工的甘蔗飴漿,很可能是把甘蔗榨汁在陽光下曬,蒸發掉水分,由此形成濃縮稠漿。
第三個階段,則是加入了把蔗漿汁在火上熬煉的程序。據文獻記載,唐太宗派人從印度的摩接陀國學會了“熬糖法”,很多后代學者誤以為,這次引入的新技術是直接制作固體糖,但事實絕非如此。王灼推測,熬糖法是“熬糖瀋作劑,似是今之沙糖也”,接下來他明確道:“蔗之技盡于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他指出,前三個階段里都沒有提到固體糖的制作工藝,所以糖霜的歷史并不長。同時,他認為,唐初從印度引入的熬糖法,制成的產品就是沙糖。所以,在王灼那里,沙糖不是固體糖,尤其不是今天的砂糖——實際上,當王灼的時代,在整個世界上,砂糖很可能都尚未問世。
《糖霜譜》指出,沙糖是用甘蔗漿熬就,元代官修的《農桑輯要》中,“甘蔗”一節先有云:“其下截肥好者,留熬沙糖。”隨后收編了詳細的“煎熬法”,是將甘蔗“壓擠取汁”之后——
即用銅鍋,內斟酌多寡,以文武火煎熬。其鍋隔墻安置,墻外燒火,無令煙火近鍋。專令一人看視,熬至稠粘,似黑棗合色。用瓦盆一個,底上鉆箸頭大竅眼一個;盆下,用甕承接。將熬成汁用瓢豁于盆內。極好者澄于盆;流于甕內者,止可調渴水飲用。將好者止就用有竅眼盆盛頓;或倒在瓦罌內亦可。以物覆蓋之,食則從便。慎勿置于熱炕上,恐熱開化。大抵煎熬者,止取下截肥好者,有力糖多,若連上截用之,亦得。先說是“其下截肥好者,留熬沙糖”,而在煎熬法中重復道:“大抵煎熬者,止取下截肥好者,有力糖多。”這就說明,煎熬法就是煎熬沙糖的方法。其工藝說來相當簡單:
把甘蔗汁于大鍋內溫火熬煮,熬到變為黑棗合(疑通“褐”)色;在一只大盆的底部鑿一個小眼,然后把大盆架在一只罐子上,將煮好的稠漿倒入盆內,任其從小孔內一點點滴落,用這種方法來進行澄清,分離糖蜜。最終,落入罐底的糖蜜在品質上比較差,只能用于制作“渴水”這類飲料。留在盆內的部分才是質量好的沙糖,貯存起來,供隨時食用。
《農桑輯要》中很明確地展示了“熬沙糖”的技術過程,也清楚地告訴我們,簡單分離過糖蜜的稠漿就是沙糖的最終形態,并沒有進一步曬干等更多步驟,因此成品是流質的膠飴,正與《澠水燕談錄》中笑話透露的信息吻合。賀威、劉偉榮在《宋元時代福建制糖技術的影響》(《莆田學院學報》二0一三年第三期)一文中指出,宋代限于技術條件,主要生產“液態糖”,而福建的液態糖產量極大,“仙游縣田耗于蔗糖,歲運入浙淮者,不知其幾萬壇”,這一繁榮一直持續到元代。從《糖霜譜》可知,不僅福建,同時期的其他蔗糖產地也是如此,這就意味著,宋元人的蔗糖消費量規模不小,但主要是使用液態糖,而非固體糖,如此重要的歷史情況,卻在糖史研究中常受忽略。同樣受到忽略的是,有一個非常漫長的時期,作為糖制品主力的液態糖,擁有一個指定專用名稱一一沙糖。
季羨林先生《蔗糖史》中關于唐代的一章讓我們明白,宋代并非沙糖的起點,唐人對這種形式的蔗糖頗為了解,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各種應用。真正驚人的是,如《演繁錄》指出,早在東漢時,張衡《七辯》里已然提到:“沙餳石蜜,遠國儲珍。”原來,至晚在公元一世紀時,就出現了沙糖(餳)這個專稱,它來自遠方,稀少而昂貴,很顯然只有上層社會才有機會接觸到。沒想到沙糖的歷史如此悠久!賦中與沙糖并列的尚有“石蜜”,這是漢唐時代對異國所產固體糖的叫法,也就是說,在張衡的時代,兩種不同形態的蔗糖制品同時從遠方來到,進入上層社會的視野,也進入中國文化。
季老《蔗糖史》研究揭示,P.3303號敦煌殘卷的背面有一段文字,內容是印度的甘蔗如何可以“造好沙唐(糖)及最上煞割令”,而煞割令就是石蜜,因此,這里抄錄了印度制造兩種不同糖品的工藝。其中沙糖的主要制作程序便是甘蔗汁熬煮后冷卻,但是,相比《農桑輯要》,多了一個用細棍用力攪打的環節,通過攪打催化結晶與糖蜜分離。由此可見,沙糖并非中國文化獨有的現象,不僅歷史長久,而且涉及各個產糖區,也涉及難以厘清的文明交流,是需要開展跨國研究的課題。
沿著歷史上溯之后,讓我們以宋代為坐標,再向下梳理。如前所述,《農桑輯要》顯示,在元代,人們仍然在制造和消費沙糖。關于這一情況,有一條出人意料的佐證資料,那就是《馬可波羅行紀》中的一則記載。這部書有多種版本,其中辣木學本有一段記錄了溫干(Unguem)發達的制糖業,說此地產品運往汗八里城,供應大汗的宮廷。然后是關于該地制糖工藝的講述,亨利·玉爾的輯譯為:
在這座城市歸屬大汗之前,當地人不懂得如何制作精糖,他們只是習慣于把蔗漿熬煮并澄取精華,冷卻后,即變成黑稠糊(black paste)。但在歸屬大汗后,其時正在宮廷中的一些巴比倫(意為埃及,下同)人前往該城,教會他們用某些樹的灰精煉蔗糖。
慕阿德、伯希和輯譯出的段落更為詳細一些:
須知,在經大汗征服之前,那里的人不知道怎樣把糖做得如同巴比倫所產那樣精細、那樣優質,他們無法讓糖凝結并聚成硬塊,只會在熬煮時加以澄取,于是,晾涼后的成品是糊狀物且顏色烏黑(paste&black)。但在成為大汗的臣民后,宮廷中有來自巴比倫的人,他們前往該城,教當地人用某些樹的灰對蔗糖進行精煉。
對于溫干舊有的蔗糖產品,玉爾譯為“black paste”,而其所據辣木學本的意大利原文則為“pal(s)ta(糊狀物)nera(黑色的)”,穆、伯譯本是“paste&black”,總之,是黑色的稠糊。至于辣木學本中所講述的溫干制糖技術,亦與《農桑輯要》一致,是煮過之后加以澄淀。所以,非常驚人地,《馬可波羅行紀》保留了一條中國古老制糖技術的重要消息,由這一記錄,再結合《農桑輯要》,就可以了解到,直到元代,一些重要制糖產地所生產的糖,仍然是黑稠漿,也就是說,是沙糖。
《農桑輯要》讓我們清楚,熬沙糖法僅僅通過滴漏的方式去除糖蜜,手段過于簡單。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制造固體糖的關鍵,一是讓蔗漿里的糖分形成結晶,二是將蔗漿中的糖蜜與結晶分離,并把前者盡可能過濾干凈,只剩下結晶部分,這剩下的結晶部分自然就成了固體糖。然而,熬沙糖法的滴漏方式顯然作用有限,使得相當分量的糖蜜仍然留在蔗漿里。另外,敦煌殘卷所抄印度造沙糖法通過棍攪促進糖結晶與糖蜜分離的技巧,《糖霜譜》和《農桑輯要》均未提到,看起來并未真正傳入唐宋時代的中國制糖業。據鐘廣言先生為《天工開物》所作的注釋,《馬可波羅行紀》提到的加灰法的意義在于:“蔗漿里有許多雜質妨礙糖分結晶,適量加入石灰,可以使雜質沉淀并中和酸性物質。”按照這本游記的說法,這一重要工藝手段要到入元以后才由埃及人傳授給溫干制糖匠,而《糖霜譜》和《農桑輯要》也確實不見言及。由此看來,一直到元代,中國本土制糖業缺乏有效的手段去除雜質、中和酸性物質、催化結晶、分離糖蜜與結晶、去除糖蜜,因此難以低成本、大規模地生產固體糖,也就只能以熬造漿式糖——沙糖為主,于是形成了整個社會依靠漿式糖的局面。
到明代,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完整抄錄了《農桑輯要》里的煎熬法,但在后面評論道:“熬糖法,未盡于此。”他覺得前人記錄的工藝不完全。為什么徐光啟會有這樣的意見呢?因為元明兩朝制糖技術發生了飛躍,固體糖生產變成了主流,不過這是需要另外討論的專題。總之,入明以后,漿式蔗糖被固體糖代替,人們對其的認識也變得模糊,最終徹底忘記其曾經的風光。
拜現代技術所賜,我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發現網絡上有不少關于今日中國各地古法造糖的報道,其中多數都制作固體的紅糖或黑糖。但,神奇的是,有一篇《一門手藝度春秋——古法紅糖熬制技藝走訪紀實》,介紹江西上猶縣的傳統制糖法,竟是將熬好的蔗漿直接舀入一個個小瓶內,加以分裝,待冷卻即為成品,“裝罐師傅們一勺勺把糖漿舀入玻璃瓶罐內,糖漿附著在勺子上,一滴滴往下墜”。這是古沙糖的當代遺存啊!文章插圖中的漿式糖在顏色上介于棗紅色與褐色之間,讓我們看到了《農桑輯要》所言的“黑棗合色”。原來,古老的沙糖一直幸存到如今,如此說來,這一種蔗糖制品已經陪伴中國人兩千年了。
然而,現代學者在研究的時候,往往容易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出發,以今日常用的固體糖甚至砂糖作為標準去裁剪歷史,進而望文生義地把沙糖等同于砂糖。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面對《馬可波羅行紀》中提到的溫干傳統產品,馮承鈞先生翻譯成“黑渣”,而十九世紀的玉爾與當代學者、《中國:糖與中國社會》的作者穆素潔都感到困惑。這種誤區造成的后果,是把糖史的研究刪減為對固體糖甚至砂糖的研究,也就歪曲了傳統中國蔗糖消費的真相。
《中國:糖與中國社會》便忽視了中國歷史上長期消費漿式蔗糖的具體情況,所以在研究南北朝時期時,沒有注意到上層社會流行“糖蟹”,這種用糖漿腌蟹的方法一直流傳到唐代(參見本人《隋唐入貢甜腌蟹》一文)。至于唐代部分,書中談了佛教與宗教儀式中如何用糖,以及“在寺院之外,八世紀阿拉伯和波斯人在各個城市增多,讓這些城市對糖的需求增加”,說得好像蔗糖是外國人的專享一樣。在這位作者的認識里,直到唐末,對本土人來說,糖仍然“并不是日常物品”。她不了解的是,唐朝人習慣的是沙糖,即漿式糖,但文學中總是雅稱其為“蔗漿”(參見本人《蔗漿櫻桃大唐春》一文),如杜甫《進艇》之“茗飲蔗漿攜所有”,宋代文人加以沿襲,如《武林舊事》中南宋宮廷的夏季是“蔗漿金碗,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如果留意唐宋文學中的蔗漿,看到的景觀就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