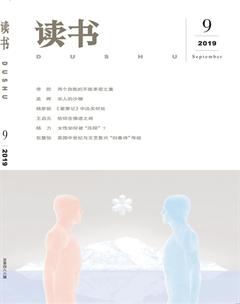“五四”與醫學
王一方
一百年前的“五四”,并非一場醫學領域里的精神暴動,卻是一場與醫學有著諸多關聯,并對近代中國醫學產生深刻影響的思想、價值肉搏戰。如今,中國近代歷史的過山車已經闖過激流險灘,趨于平穩,不再劇烈跌宕,但其精神軌跡給我們的啟迪依然激蕩,反思的誘惑依然不減當年。
二十二年前的一樁殺醫案
人常說沒有“一戰”就沒有“五四”,若深度溯源,應該說沒有“巨野教案”,就沒有德國及日本在膠東的霸凌與特權,也就沒有“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救亡運動,繼而演變成啟蒙、救亡的雙重使命。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發生的巨野教案,導火線是一樁意外的“殺醫案”,死者是兩位德國傳教士,受害者本應是傳教士醫生本人,但因晚上讓床給朋友而導致兇手殺錯了人,偶然事件的背后是當時流行的義和團意識對中西醫學在眼科診療路徑差異的荒唐誤讀(百姓誤傳番國眼科醫生專門摘取兒童的眼珠,實為角膜手術)與莽撞排斥(中醫治療眼病多采取內服藥物的辦法,即使是外治也只是藥浴或敷藥,因此不認同接納手術刀割治的外科治療辦法),夾雜了諸多教士、教民與當地百姓的利益糾葛,這樁血案迅即引發了“膠東事變”。十天后,德國艦隊北上強占膠州灣,次年三月六日,德國強迫清延簽署《膠澳租界條約》,青島淪為德國殖民地。一九一四年,“一戰”爆發,德日在膠東開辟亞洲戰場,展開決戰,日軍在仰口登陸,迂回攻陷青島,德軍投降,日軍取得膠州灣的控制權。“一戰”結束后,巴黎和會上,日本代表欺人太甚,施壓中國政府簽訂屈辱的“二十一條”,同意將德國在膠東的治權轉讓給日本,中國作為“一戰”戰勝國卻繼續喪權辱國,激起國人的憤怒抗爭、決絕思變。
追溯“五四”的前戲,我們可以清醒地認識到,催生殺醫案的義和拳式排外情緒不是什么愛國主義情懷,中西醫之間身體理論,診療路徑的差別只能通過交流互鑒來融通,而不是透過民粹主義情緒宣泄來加劇對立和仇恨。
一個醫學生的毅然抉擇
在當年北京的八所國立高校中,北京醫學專門學校規模較小,加之醫學生學業負擔沉重,對于國運民瘼的關切相對疏離。但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大游行中,走在隊伍前面,高擎“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標語的則是一群北京醫學專門學校的醫學生,召集人是二年級學生梁鐸。梁鐸,字敬宸,一八九五年出生于江蘇江都,一九一八年考入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次年擔任北醫的學生會會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上午,北京十三所高校代表在北京政法專門學校開會商議游行示威事項,梁鐸以北醫學生會代表身份出席,決定當天下午即聚會天安門示威。上午的會議剛結束,梁鐸就趕回北醫,通知同學們下午上街游行,梁鐸高擎標語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成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組織者、親歷者與見證者。在六月的北洋軍閥清算中,梁鐸被捕入獄,經校方保釋才得以出獄。此后他依然斗志不減,一九二一年的高校索薪抗爭中又一次充當召集人,沖在前面,于是,二次被捕。因為是“二進宮”,被列為重犯秘密拘押,險些喪命,后經社會各界聲援及校方擔保才被救出。
一九二二年,梁鐸畢業,因成績優秀而留校任教,不久評定為內科學講師,附屬醫院新購x光機,成立x診斷室,求新好學的梁鐸擔任主任。一九三0年,北醫送梁鐸赴德國柏林大學留學,曾在居里夫人實驗室短暫實習。一九三五年,獲得柏林大學博士的梁鐸回母校任教,擔任附屬醫院放射科主任,將放射學由診斷拓展到治療領域。正當梁鐸事業風生水起之時,“盧溝橋事變”爆發,國民政府安排北平的高校南遷與西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赴長沙,組建長沙臨時大學,后來輾轉到昆明,成為西南聯合大學。北平大學(含醫學院)與北平師范大學、北平工學院、北平研究院赴西安,組建西安臨時大學,后來南下漢中組建西北聯合大學。當時,約80%的員工選擇隨校西遷,但這一次梁鐸沒有站在時代的潮頭,他拒絕了徐誦明校長的西遷指令,選擇留駐北平,加盟了由老校長湯爾和附敵后組建的偽北大醫院。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后,因為這一附敵污點被光復后的北大醫院限期調出,他南下去了廣西桂林,任教于廣西醫學院,新中國成立后才被北醫召回,仍然在北大醫院放射科任教。
一個醫界泰斗的隕落
五四運動爆發的一九一九年,一個顯赫的醫學人物奧斯勒(williamosler)在英倫溘然離世,其實,他本不該那么急切地離去,只因獨子愛德華殞命于“一戰”炮火,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極度憂傷,使他免疫力急劇衰退,無法抵御一次普通的支氣管肺炎。他的死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標志著一個時代的開啟,時代在中不斷重審醫學的性質,價值走向,人性歸宿。
奧斯勒畢業于加拿大的麥吉爾大學,早年服務于賓夕法尼亞大學醫學院,幾番拼搏,成為美國二十世紀初的四大名醫之一,因醫學教育改革成績斐然,受邀參與創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他是床邊醫學(以病人為師)的倡導者與實踐者,學界無人不知,且桃李滿天下。
奧斯勒一方面倡導崇真務實的科學精神,精益求精的技術態度;另一方面,他也是醫學哲學與醫學人文教育大師。他最早洞悉醫學與現代科學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及價值鴻溝,醫學的人道使命與商業理性之間的沖突,反對將醫學規律完全等同理化規律,拒絕將醫學定義為謀生(盈利)的職業。他時時提醒他的學生,醫學是使命,而非商業,要用教化引領教育,德慧點燃智慧,情懷驅動關懷。臨床醫生應該警惕“冷漠、傲慢、貪婪”三宗罪的侵襲,自覺抵制醫界的沙文主義、民族主義、門戶(宗派)主義、地域主義意識。同時,醫學應該在科學與藝術之間找到落腳點,在理性與感性之間找到平衡點,在治療與照顧之間找到交匯點。他的名言“醫學是不確定的科學與可能性的藝術”(“奧斯勒命題”),成為當代醫學思想史的哲學鏡鑒。面對快速推進的醫學科學化、技術化,人文的宏博訴求與技術的專精訴求之間的矛盾,以及舊人文與新科學之間的不匹配,他提出新人文的呼吁,那是融會在技術中的人文,充滿人文化智慧的技術,而非兩張皮,兩臺戲。面對醫界流行的重技術、輕人文的新思潮,他發出預警,沒有人文滋養的醫生是跛腳的。他極力倡導薩頓以科學(思想)史與科學(技術)哲學燭照學術演進的新人文主義,展現了他不凡的胸襟和氣度。新人文主義在中國醫學界的根植則要滯后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了。
從醫學納新到醫界革命
“五四”集聚的思想勢能、思變洪流最早沖刷的河床就是醫學(矛頭主要指向傳統中醫),以及醫療市場。從醫學思想史看,“五四”是分水嶺,是中國人醫學觀的嬗變節點。醫學生態巨變,發生坐標式漂移,醫學徹底投入賽先生懷中,成為科學的醫學,技術的醫學,物象(客觀)化,對象化。“五四”以降,中醫逐漸被知識界質疑、批判,甚至拋棄,中西醫格局大改觀。由中強西弱,演變為中西并茂,繼而步入西強中弱的軌道。
從一九一九年的救亡狂飆,到隨后的啟蒙浪潮,人們在叩問中國向何處去之時,也在叩問如何告別傳統,擁抱科學,如何面對浸泡在傳統儒道文化之中思辨意識濃郁的傳統醫學?甚至,我們該如何看病,看中醫還是看西醫?其實,“五四”前后最早嘩變的還不是新銳人物,而是舊時的冬烘先生,對中醫的質疑聲最初來自經學領域,桐城派末代大師吳汝綸,早年考察過日本,對西洋醫學有所認識。他鄙薄中醫,崇尚西醫,他在給何豹臣的信中稱:“醫學西人精絕,讀過西書,乃知吾國醫家殆自古妄說。”“中醫之不如西醫,若賁育之于童子。故河間、丹溪、東垣、景岳諸書,盡可付之一炬。”他對中醫的偏執態度延續到就醫,晚年身患重病也拒絕中醫。俞樾在治經之余對中醫藥學有所研究,且能處方治病。在《春在堂全書·讀書余錄》一書中,他用考據學方法對中醫經典《黃帝內經》進行探賾索隱、辨訛正誤。基于對中醫這樣的理解,隨后他提出“廢醫存藥”論。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兩篇論著《廢醫論》和《醫藥說》中。基本邏輯是“卜可廢,醫不可廢乎?”《廢醫論》“僅僅從考據角度,從古書到古書,由文獻到文獻,而對古今醫藥的實踐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難免會得出荒謬的結論”。今天看來,《廢醫論》基本上是一篇帶有書生之見的不通之論。俞樾的得意門生章太炎,是俞樾觀點的衣缽傳承者,他精通醫學,留下不少醫學論著。他在《論五臟附五行無定說》中否定五行學說,主張完全廢棄。章太炎沒有強烈的廢醫傾向,但他在日本講學期間影響了一批留日學生,如廢止中醫運動的領軍人物余云岫。余云岫的早期觀點也是廢醫存藥,一九一七年,他在《學藝》第二卷上發表《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第一步》一文:“要曉得陰陽、五行、十二經脈等話都是謊話,是絕對不合事實的,沒有憑據的,……中國的藥品確是有用的。”余云岫斷定中醫立足于陰陽五行的哲學空想,但認可中醫的實際療效,他提出摒棄中醫理論,研究中醫藥理,以科學的實驗的藥物學方法,對中醫的處方做分析研究。他對于中藥的作用,基本秉承了《醫藥說》的觀點。
嚴復、梁啟超雖然沒有留學日本的經歷,但對日本明治維新中廢除漢醫的做法極為認同,他們都曾有否定陰陽五行的論說。嚴復在《原富》中言及五行干支,把中國的醫藥歸為風水、星象、算命一類的方術,缺乏實際觀察和邏輯推理,是純屬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虛玄話語:“中國九流之學,如堪輿、如醫藥、如星卜,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兇之各有主,則雖極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無他,其例立根于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嚴復曾寫信告誡其甥女:“聽中醫之言,十有九誤,切記切記。”早年辦《時務報》而聲名鵲起的梁啟超惡舊趨新,他認為:“陰陽五行說為二千年來迷信之大本營,直至今日在社會上猶有莫大勢力,今當辭而辟之。”對漢代以后的陰陽五行說,梁啟超尤為痛絕,指出醫家經典深受其害,“吾輩生死關系之醫藥,皆此種觀念之產物!”晚年梁啟超的否定中醫、推崇西醫姿態在思想界是出名的,他甚至不惜回避自己的誤治遭遇,強忍委屈在《晨報副刊》發文為西醫辯護。
一九0三年,虞和欽在《理學與漢醫》中視中醫為亡國滅種的“怪物”,進行全面的否定。朱笏云在《中國急宜改良醫學說》一文中更是表達了他對中醫的深惡痛絕:“今世最可痛、最可惡、不能生人適能殺人者,非吾中國之醫乎?吾中國之醫,不知解剖,不辨物性,不諳生理及病理……”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九年,十年間迅速形成一股否定傳統中醫的熱浪。其實,中間有兩次“接力”。一次是一九二四年的科玄之爭,這場論戰以“玄學鬼”被人唾罵,廣大知識分子支持、同情科學派而告終。第二次是一九二八年的全國教育會議上的“廢止中醫案”,提案人汪企張,時任上海公立醫院院長。汪企張是余云岫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更是廢止中醫的急先鋒,鼓噪“用政治手段,仿照日本當時取締漢方醫辦法”,將中醫“拼絕消滅”。他提出的“廢止中醫案”雖遭否決,但實際上成為次年全國衛生會議“廢止中醫案”的先兆。一九二九年二月國民黨政府衛生部第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議上通過余云岫提出的“廢止中醫案”,全稱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議案一公布,立即遭到中醫界的強烈反對,大批中醫藥人士紛紛抗議,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組成請愿團,派代表到南京請愿,要求立即取消議案。壓力之下,國民政府不得不撤銷這一法令。
平心而論,國民政府當年的最初設想是滌舊納新,參照西方模板,建立一套適應現代社會的制度與法令來規范醫療格局與醫學發展路徑,順應世界科學化潮流。恰恰是洶涌澎湃的科學主義思潮與公共知識分子的進化論信仰,救亡圖存輿論的巨大推動力,以及醫者自身的科學主義認知與趨新求變的時代訴求疊加,才臨門“加速”,魯莽“撞車”,鑄就了“廢止中醫”的現實窘境。幾番爭斗,后來達成中西醫雙峰并峙的體制,中醫、西醫都在摸索可行的方案,在中醫改良和中醫革命之間容與徘徊。
余思
“五四”的氛圍與基調都是激進主義,保守主義被打倒,調和主義也基本沒有市場,常常被指責為“騎墻派”“和稀泥”。在“五四”學人看來,“道中庸”本是儒家糟粕,應該堅決剔除。不過,哲學上的基本范型就是“正反合”,人類學也常常秉持文化相對主義,拒絕絕對主義,田野歸來,沒有哪個文化范型絕對優越,哪個文化范型絕對低劣,應該互鑒互學。費孝通老先生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如今已經被廣泛認同,成為文明互鑒的基本原則。其實,中西醫學也罷,東西方道路也罷,左右立場也罷,都有協商、調和的余地。當然,分歧導致的紛爭甚至斗爭都不可避免,但博弈的終點仍然可能是調和,歷史的鐘擺律就是斗爭,調和,再斗爭,再調和,始于左右開弓,終于左右逢源,別的領域不敢妄加預測,中西醫的百年紛爭大戲,未來一定會有一個調和的腳本。
調和主義的一種選擇是在擁抱先鋒之際,同時寬(厚)待傳統,兩者并非水火冰炭,可以在繼承中有所發揮、創新。什么是寬厚?我的理解是積極反思而不輕率反叛,生猛進取而又清火消躁,告別過分強烈的歷史功利心,不求古為今用,但求古慧今悟。在這方面,奧斯勒可謂睿智先生。在他眼里,生命認知需要整合,診療探索也需要整合,整合才會走向和諧。門戶主義與民族主義都不可取。
一九。五年四月,奧斯勒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退休,準備定居英國讀書寫作,在馬里蘭州內科與外科醫師年會上,他做了一個辭別美國醫學界的告別演講,題目叫“整合、平安與和諧”,這篇演講也展示了他的傳統醫學調和觀,他十分誠懇地勸慰新派醫生“要接納順勢療法”(傳統中醫今天在西方仍被歸于順勢療法),雖然他們處在非主流的地位,但這個圈子里集聚了不少優秀的人才,面對醫學(生命)的不確定性(無常),臨床上多一種診療辦法(臨床多樣性)總是有益的。他承認順勢療法與新式醫學之間有著諸多抵觸,順勢與拮抗(抗爭)就是一對矛盾,但順勢療法古往今來對于診療的豐富性多有貢獻,不能輕易就將其毀棄了,他堅信“阿斯克勒匹俄斯(醫神)的白袍”足夠寬大,大可以互相交流,有爭議可以擱置,有問題可以修正,簡單地將其排拒在醫學的視野之外,只會令人遺憾。對于這個演講,那些信奉絕對主義,只會啃讀《歐氏內科學》的新派醫生大概未必知曉,知道了也未必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