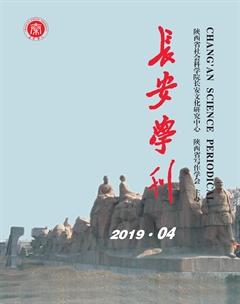《長恨歌》:反諷與暗嘲
趙香
摘 要: 王安憶的《長恨歌》是一部對舊時代具有批判和諷刺意義的小說。作者試圖從新時代的立場來觀察舊時代小資產階級毀滅的原因。小說在語言上,以一種正話反說的形式對王琦瑤式的生活和觀念進行調侃與諷刺;在意象上,弄堂、流言、鴿子都被作者賦予了特殊的含義,弄堂是各色人生的象征,流言則是弄堂中人與人之間的紐帶,而鴿子是這弄堂變遷的觀察者,它們看似親切無害,卻是掩埋事實的幫兇;在人物形象上,以王琦瑤、老克臘、程先生、薩沙、長腳等人為代表,他們的形象與自身的命運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構成了小說中最具有諷刺意味的部分。《長恨歌》中雖含有懷舊風格,但其對舊時代小資產階級的批判與諷刺是毋庸置疑的。
關鍵詞:諷刺;懷舊;語言;意象
文章編號:978-7-80736-771-0(2019)04-077-03
《長恨歌》是王安憶寫于20世紀90年代的一部作品,曾獲得茅盾文學獎,影響深遠。因這部作品出現的時間正處于中國“懷舊熱”的時候,作品中又有大量舊上海的生活細節、事物樣貌等描述,讓這部作品充滿了舊上海的色彩,曾一度被認為是懷舊熱的代表作品。但是王安憶在一次訪談中說過:“《長恨歌》很應時地為懷舊提供了資料,但它其實是個現時的故事,這個故事就是軟弱的布爾喬亞覆滅在無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之中[1]。”由此可見,王安憶的初衷是對舊上海時代小資產階級的諷刺和對彼時“懷舊熱”的批判與嘲諷,而在小說中,語言、意象、人物也處處體現著對舊上海的反諷與暗嘲,字里行間透露出來的是對追求小資產階級那種浮華、偽精致生活的諷刺。王安憶雖然生活于上海,也曾受到過上海舊時代生活環境的熏陶和浸染,但是在這部作品中,她站在一個新的時代,試圖從一種新的角度,一種靠近于無產階級的角度,去審視舊時代的生活和習性。作品中雖情不自禁的流露出對舊上海生活、人情事物的細致刻畫,但并不能掩蓋住作者原本的意圖。作品的語言、意象、人物處處都體現了諷刺意味,下面分別從這三個方面來逐一分析《長恨歌》中的諷刺藝術。
一、語言的諷刺性
《長恨歌》的語言,尤其是在描寫王琦瑤少女時代的時候,語言大多是以戲謔的方式來表達或進行調侃,常常會使用正經的夸獎語氣來表述一件不合情理的事情,或者用非常優美細膩的語言來刻畫一些反面的事物或者人物形象。這些言語往往能夠巧妙的引起讀者的認同感,不會顯得尖銳刻薄而引起讀者厭煩,也不會因為言語太過溫和而達不到諷刺的效果。
比如在刻畫王琦瑤形象的那一章節,說“王琦瑤的父親多半是有些懼內,被收服的很服帖,為王琦瑤樹立女性尊嚴的榜樣[2]。”言語里看似是對這些妻子們的夸贊,實則暗含對她們的諷刺。丈夫的懼內,成為妻子們向外展示自我能力和女性尊嚴的象征,甚至成為下一代的榜樣。雖然成長于這樣扭曲的價值觀中,王琦瑤并沒有成為像她母親那樣可以將丈夫拿捏在手中的妻子,反而形成了另一種同樣扭曲的觀念,她把男性當做生活的依靠和排遣寂寞情愫的渠道,沒有建立起具有尊嚴和獨立的個體,成為依賴男性生存的菟絲花。即便是后來從鄔橋返回上海后獨自生活的時候,她的表面上以為人打針為營生,實際上最大的仰仗和最后的依賴是金條,而金條是從出現在她感情生活中的第二個男性,李主任那里得來的。真正的女性尊嚴應該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礎之上的平等的權利、責任與價值,但顯然,先輩們沒有樹立起一個好榜樣,而后來的王琦瑤也沒有實現那樣的品質。
在王琦瑤的時代,只有緊跟時代潮流,成為摩登小姐,才不會被同伴所拋棄和嘲諷。當感傷成為此時的時尚潮流時,王琦瑤們需要緊緊跟隨,她們“無一不是感傷主義的,也是潮流化的感傷主義,手法都是學著來的[3]”。感傷本應該是一種情感,由心而發,但是在這里卻成為一種流行和手法,是可以追隨和學習的。它是王琦瑤們追隨時尚的一種手段,有了它才能成為摩登小姐,沒有它便是時尚的落伍者。“這地方什么樣的東西都有摹本,都有領路人[4]。”這樣荒謬而可笑的模仿,只是為了緊跟時尚潮流,連情感都可以模仿,還有什么是不能模仿的呢?
作者在調侃幽默的言語之外,暗含了對那個時代所追尋的潮流的諷刺。女性本應該作為社會的獨立個體,卻失去了自我生存的能力,只能依賴于男性而生存,而在時尚潮流的沖擊下,也因盲目從眾迷失了自我。
二、 意象的諷刺性
作者在小說開篇細致的描寫了弄堂和流言這兩樣事物。弄堂是上海特有的地域文化,在作者筆下是帶有色彩和種類的活物,它們都有各自的特點,每一種弄堂都代表著不同人的生活。弄堂是上海這個城市的縮影,作者將故事的發生地放置在弄堂之中,將整個城市都融入其中。弄堂縱橫交錯,復雜纏繞,看似親切,坦誠,實則是藏污納垢的好地方。弄堂表面的景象雖可盡收眼底,內里的東西卻是神秘莫測的,而這神秘之中就蔓延著各色的流言。流言是弄堂里的特色,它雖然是粗俗的、鄙陋的,但是卻無處不在。“它們是上海弄堂的思想,晝里夜里都在傳播[5]。”弄堂里人與人之間的交談,是流言傳播的捷徑。弄堂和流言混為一體,弄堂就是流言的實體。弄堂和流言這兩樣東西可以說是影響了王琦瑤的一生。王琦瑤在弄堂里長大,出走回歸后,又住入弄堂里,她的一生在弄堂中度過,她應是最了解這弄堂文化的藝術。弄堂文化分明無處不在,其內里卻是自私的,弄堂只負責流言的傳播,卻不負責傳播的結果。流言真真假假,沒有人會在意它到底是真是假,在意的只是傳播瞬間的神秘與快感,享受之后便隨它而去,至于流言會去往哪里,會造成什么樣的結果,這不是傳播者所關心的事情。而流言的傳播者之間,看似親密無間,實則冷漠無情,流言是他們維持親密的紐帶,脆弱易斷,稍有涉及自身利益,便可立即斷開,以確保自身安危,給旁人分不出半點關注。這樣的弄堂文化是自私自利毫無人情冷暖可言的,如此一來,小說末尾長腳輕而易舉就能產生殺死王琦瑤的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鴿子是弄堂里最具有自由的東西,它可以自由的飛翔,不受弄堂的拘束,“幾乎是這城里唯一的自然之子了[6]。”它們是時代變遷的見證者,作為自由的個體,它們本該是最具有批判性質的生靈,但在小說里對鴿子的描寫,其實是對人類的反譏[7]。鴿子作為完美的第三視角,它們將這弄堂里的一切都盡收眼底。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鴿子不會說話,它們是沉默的觀看者,弄堂里發生的一切都只是默默發生,然后又默默消亡,并不會因為這樣的第三視角而產生變化。一方面鴿子是弄堂各色事件的見證者,另一方面它也是掩藏各種真相的幫兇。
藏污納垢的弄堂、真真假假的流言、沉默不語的鴿子為王琦瑤之死做足了鋪墊。弄堂容納了形形色色的人與事物,在這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流言為真相附上一層面具,是真是假沒人能夠辨析;鴿子是冷漠無情的見證者,永遠不會為真相開口說話,因此被長腳怒殺的王琦瑤很有可能在這種種事物的掩藏下,讓人不得而知。
三、人物命運的諷刺性
人物是小說的靈魂,在《長恨歌》中,刻畫的多數人物外在形象與其最終的命運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恰恰構成了小說中最具有諷刺意味的一部分。
首先是長相可人,又具有小女兒情調的王琦瑤。小家碧玉,平易近人,不過分耀眼,恰恰是最能得到眾人憐惜的目光,但“上海小姐”的頭銜和皇冠,眾人的吹捧與憐惜,眩花了王琦瑤的眼睛讓她迷失在虛榮之中。王琦瑤一直都想要脫離弄堂的平民生活進入上流社會,甚至在女兒“薇薇的時代”,她即使沒能成為所謂的上流社會人,也隨著時代的變遷成為來自舊時代的傳奇人物,造成一種站在時代潮流前端的假象。但直到她被殺死也沒有成功擺脫弄堂的枷鎖。王琦瑤身上最大的諷刺是,她最終死在了小混混長腳的手里,起因是李主任交給王琦瑤的那個雕花木盒,本來是用來保障她生活的東西,最后卻成為殺死她的導火索,而她一直用來挽留年華的假象成為她死亡的催命符。在王琦瑤生病時,長腳是唯一去照顧她的人,但這份照顧顯然摻雜著利益的誘惑,他真正的目的是得到王琦瑤手里的金條,沒有得到金條還要被王琦瑤威脅時,他毫不猶豫選擇了殺死王琦瑤。他在圍攏王琦瑤的頸脖之后,王琦瑤干枯的皮膚、發根灰白發梢油黑的頭發、綿軟的脖子讓長腳在殺死王琦瑤時產生了快感,加大了手勁,甚至在殺死她之后還意猶未盡。這可怕的結局正是王琦瑤日常留給旁人精致優雅的印象與她真實的樣子所帶來的反差造成的。王琦瑤一生擁有的最不想舍棄的東西最終卻成為殺死她的催化劑。作為“傳奇”人物的王琦瑤,原本應該有一個優雅精致的晚年或者一個轟烈的的退場,卻死于一次意外之中,沒有保留她一生所維持的體面,也沒能夠再一次引起眾人的關注,甚至被草草的結束了生命。
然后是老克臘,他是陪王琦瑤重回歷史的人,但時光已逝,歷史不可重返,他注定只是一個過客。王琦瑤與老克臘的“忘年戀”并不是真正的存有愛情。王琦瑤想要抓住時間,證明自己年華依舊,而年輕的老克臘是一個具有懷舊情結的人,他迷戀舊上海的小資情調,迷戀它的風物人情,兩個人互有所需,于是走到了一起。老克臘對舊上海的好奇與迷戀轉移到了王琦瑤的身上,這個從舊上海遺留下來的“上海小姐”存留了他所追求的東西。但這樣的王琦瑤生活在他的幻想中是最合適的,當他們距離拉近,幻想被打破時,剩下的就只有現實了。年華逝去的“上海小姐”需要染發水來掩蓋她早已生出的白發,并且皮膚松弛褶皺,像覆蓋在骨頭上的枯皮,身上還散發著隔宿的腐氣,這些都是老克臘所不曾想到的,而這些偏偏就掩藏在他所迷戀的事物之下,這讓他意志消沉,甚至喘不過氣來。老克臘對舊上海的情調有多迷戀,此時的打擊就有多大,最終選擇了拋棄王琦瑤而離去。老克臘對舊上海情調葉公好龍式的喜愛,正是作者所批判的。老舊上海的時代已經過去,此時的懷念只是時代巨變時的感傷,或者是年輕人的一場復古游戲,不可能成為新時代真正所追求的東西。這也恰恰證明了王安憶寫這部小說并不是為了迎合懷舊浪潮,而是站在懷舊的對面批判它。
除此以外還有程先生、薩沙、長腳等人,他們的人生和命運也存在巨大的反差。程先生體面而優雅,是舊時代的新貴,卻最終在文革的大浪潮中被迫跳樓而死,死相可謂慘烈,他是小說中出現的幾個主要人物中唯一沒有挺過文革的人。薩沙在女人之中游蕩從而獲取生活依賴,他軟弱而無能,卻貪圖富裕的生活。但是薩沙的父親是一名無產階級工作者,而母親來自于當時共產主義代表國家蘇聯,作為后代,他不但沒能成長為一名真正的無產階級,反倒是游蕩在女人之中,過著小資產階級的生活。長腳將自己偽裝成富豪的后代,整日吹噓自己祖上的闊綽,對朋友出手大方,從不把金錢當回事,暗地里為了躲債不敢回家,為了金錢不擇手段,甚至最后為了得到王琦瑤的金條鋌而走險,下手殺死了王琦瑤。
四、小結
王安憶用大量的筆墨來描寫舊上海的細節與王琦瑤精致而優雅的生活,最后卻選擇讓一個小混混來結束這一切。這個小混混的邋遢與王琦瑤的精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所有的營造出來的體面最終都被輕而易舉的打破。王琦瑤的精致與體面是建立在物質之上的,浮于表層,不堪一擊。
由于舊上海文化和生活對作者的影響,作品中含有大量對舊上海環境及文化的細致描寫,這種文化的根深蒂固是一時磨滅不掉的,“懷舊乃是作品不可避免的呈現出的一種風格特征,它本身并不是為了去寫一個懷舊的東西[8]”,“作者在小說充滿歷史感的基礎上,對上海懷舊熱做出了巨大的反諷[9]”。王琦瑤所象征的舊時代的小資產階級是軟弱無力的,沒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只能依靠外界因素生存,當外界因素不能繼續為它提供保障時,反而很有可能成為毀滅它的兇手。因此作者在小說中寫舊時代精致的生活方式,并不是為了宣揚這種生活,而是通過主人公王琦瑤的死來批判舊時代這種小資產階級及其思想觀念的軟弱性和落后性。同時,作者也沒有忽略遺留在新時代中的“懷舊情結”,那些所謂的復古潮流,在作者看來只是一場年輕人的時代游戲。新時代上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經濟發展迅速,人的思想觀念卻依然滯后。時代的迅速變遷,帶來生活上的壓力和精神上的不適,致使人們開始懷念舊時代的“舒適”,但這些懷念會在時代的進程中和人的逐漸適應中慢慢消退。作為年輕人,以《長恨歌》中的老克臘為代表,他們所喜愛的只是舊上海浮于表面的精致與奢華,在他們看來這才是生活高雅的體現,他們對舊上海的了解是遠遠不夠的,他們所追求的只是一種“偽精致”。聯系當今社會,也存在這樣追求“偽精致”的現象,過分的追求儀式感,追求物質上的奢華和存在于他人眼里的“精致”人生,在看書時發一條朋友圈表現歲月靜好我愛讀書,卻沒有真正看完過一本書;在吃飯時注重擺盤的精細與漂亮,卻忽略了食物內在的營養,把物質和外在的光鮮當做生活的精致與高雅,完全忽略了生活該有的內涵和意義。除此以外,復古潮流也頗為流行,最有代表性的是在年輕人中興起的“漢服熱”。由于漢服樣式的獨特和美麗,吸引了眾多年輕人的目光,但是大部分人的關注只停留在衣服的華麗和精美上面,對漢服背后存在的文化卻一無所知。古代漢服的制式是有規定和要求的,它體現著中國古代的文化,真正能通過漢服去了解古代文化的人少之又少。這樣的“偽精致”和“漢服熱”現象,都需要我們認真的去反思它們能給社會帶來什么。
參考文獻:
[1]《<長恨歌>,不是懷舊》:王安憶、王雪瑛,上海《新民晚報》,2000年10月8日。
[2] 《長恨歌》:王安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19頁。
[3] 《長恨歌》:王安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20頁。
[4] 《長恨歌》:王安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20頁。
[5] 《長恨歌》:王安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8頁。
[6] 《長恨歌》:王安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5月,第16頁。
[7] 《論王安憶<長恨歌>中環境描寫對女主人公命運的暗示》:吳鴻雁,《凱里學院學報》,2013年4月,第31卷第2期。
[8] 《故事、生活、心靈世界:眾聲喧嘩遮蔽的真實——談王安憶<長恨歌>之主旨》:支運波,《文學選刊》,2010年1月。
[9] 《懷舊傳奇與左翼敘事:<長恨歌>》:陳思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第3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