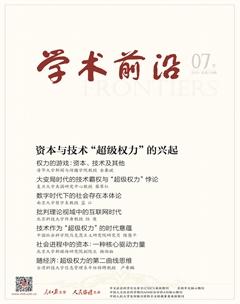資本與技術“超級權力”的興起
“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權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區別了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揭示了資本與經濟權力的關系。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學術界對權力的研究范式也在不斷演進。羅素認為權力具有多種形態;葛蘭西把權力視為一個支配集團獲得人們的普遍承認,丹尼斯·朗把權力定義為“對他人產生預期效果的能力”;韋伯則認為,“資本獲得權力,就是取得人們的普遍信任,使自己支配世界的行為具有合法性”。而在福柯那里,“技術”是這種“權力”背后的支撐物,這一點在互聯網時代表現尤為明顯。有學者指出,在網絡平臺中,平臺的應用者通過平臺服務者提供的技術手段實現多邊互動,用戶基于平臺上的互動必須按照平臺提供者設定的規則完成,這些規則表面上是具體的協議文本,但本質上是以代碼作為技術規則來實現和控制的。平臺服務提供者設定的規則可以直接作用于用戶,且用戶沒有議價權,只能遵守。這種就是技術帶來的權力準則。互聯網的基本通訊協議、過濾軟件、加密程序等技術構造決定了信息如何在互聯網上被傳播。這些技術構造事實上規制了互聯網上的信息流,基于互聯網信息系統的網絡平臺具有相類似的技術能力和權力。
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讓人類進入了一個超聯結階段,掌控幾億消費者的超級網絡平臺全面崛起,為資本提供巨額利潤的同時,又進一步擴大壟斷力量的范圍。資本擴張的歷史是相似的,漢娜·阿倫特在上世紀寫道:“當資本主義傳播到法律尚未健全的地區時,所謂的資本主義法則實際上使得捏造現實成為可能(構建了當地的規則)”。如今網絡空間的發展與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的擴張如出一轍,網絡平臺往往標榜“平臺中立性角色”,聲明不為發布在其上的內容負責。谷歌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與人合著的《新數字時代:重塑國家、商業與人類的未來》(The New Digital Age: Transforming Nations, Businesses, and Our Lives)一書中開篇即表明:“線上世界是不受地球法律約束的(not truly bound by terrestrial laws)”“互聯網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受統治的空間(ungoverned space)。”資本與技術在這個“不受統治”的空間迅速擴散,在大數據與算法無處不在的今天,用戶行為數據可以空前便利地被記錄、統計。哈佛商學院教授肖沙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稱之為“行為盈余”(behavioral surplus),互聯網平臺利用這些“行為盈余”,能夠清晰標記每一個ID身份的喜好、欲求,預測用戶將來的行為,并分析如何從中盈利,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超級權力”。
當今世界很多重大事件都有這些“超級權力”的影子。澳大利亞媒體報道2016年澳大利亞競選最后幾周,Facebook接觸了澳大利亞主要政黨,向對方推薦自定義受眾工具,用于識別搖擺選民,投放定制選舉廣告;2018年,Facebook被曝出將上萬用戶的數據分享給劍橋分析公司,還因此影響了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引起了美國司法部的調查。亞馬遜則被指責通過竊取第三方賣家的銷售數據來研究自有產品線的規劃,對小企業造成了破壞性的傷害。在美國,針對谷歌、Facebook、亞馬遜等網絡巨頭發起反壟斷調查的呼聲日益高漲。在我國某網絡問答社區,“有什么讓你覺得很恐怖的事?”的問題下,“近期瀏覽過的內容會在不同的網絡平臺、軟件上出現,似乎互聯網能‘窺視人的心理”的答案,得到了眾多人贊同。然而現實中,人們卻發現很難離開Facebook、谷歌、亞馬遜,正如我國用戶對微信、百度、淘寶的依賴一樣。不可替代性讓這些互聯網巨頭有恃無恐,而相應治理措施的缺乏更讓其野蠻生長。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5G時代的來臨,人們接入互聯網的方式和工具將更為豐富,產生的海量數據也將繼續被各類超級網絡平臺及其背后的資本所掌握和利用,資本與技術“聯姻”,滲入社會的各個層面,甚至影響和塑造國際秩序,這些都為國家和社會治理帶來挑戰。本期特別策劃,約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深入分析“資本與技術‘超級權力的興起”,敬請讀者垂注!
——《學術前沿》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