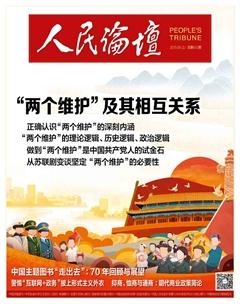打擊污染環境犯罪當用重典
【摘要】依法嚴懲污染環境犯罪是當前我國對待污染環境犯罪的刑事政策。落實依法嚴懲污染環境犯罪的刑事政策,須在了解污染環境犯罪的主要特征的基礎上,全面理解與準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并加強生態環境的行政執法與多元共治。
【關鍵詞】刑事犯罪 依法嚴懲 污染環境 【中圖分類號】D924.11 【文獻標識碼】A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在生態文明建設中,依法嚴懲污染環境犯罪,加強污染環境犯罪的防控與懲治,是生態文明法治建設的應有之義。
刑法修正案中,對污染環境罪有關條例的修訂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要求
1997年頒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該罪名將因污染環境造成重大事故的行為界定為犯罪行為,并配置了三年以下與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兩檔刑期。但因為該罪名需要污染環境造成重大事故才構成犯罪,構成犯罪的門檻相當高,導致該罪名在司法實踐中運用很少,基本上處于空置狀態。
因我國環境保護工作的需要,2011年全國人大在頒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中對《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進行了修正。修改后的條文表述為:“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法律界普遍認為,在修正案中,污染環境構成犯罪的門檻在我國已經大大降低,“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實質上已經不復存在,《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實質上已變動為“污染環境罪”。為配合上述污染環境罪的司法適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頒行了第15號司法解釋,并于2016年對上述司法解釋進行了修正優化。兩個司法解釋的頒行,明確了《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中嚴重污染環境的具體內涵和在司法適用中的一些標準問題,對實踐中污染環境罪的辦理起到了明確的指導作用。
加強行政管理與刑事司法協同,依法嚴懲污染環境犯罪
嚴重污染環境的行為在我國已納入刑法體系。因此,依照《刑法》及其司法解釋,對構成污染環境罪的行為必須進行刑法懲治。但由于當前污染環境犯罪的主體多數為中小型企業,這些企業在當地是安置就業的主要途徑與上繳利稅的重要來源,地方政府對其有一定的依賴。另外,當前個別地方政府對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解不到位,對懲治污染環境犯罪的意義認識還不夠充分,自身環境治理的主體意識還不夠清晰,因此,在部分地區還存在污染環境犯罪“有案不立”“有案不查”的情形,這種觀念與做法是錯誤的。
懲治犯罪必須依據法律,污染環境犯罪的懲治也不例外。當前,在懲治污染環境犯罪領域,個別地區出現了對刑法司法解釋理解不充分、對刑事法律適用不合理的傾向,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污染環境犯罪行為,必須依法懲治。所謂依法,就是要依據刑法原則,正確理解與適用《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一些地方出現的機械理解與適用《刑法》的現象應予以改正。比如,看到環境被污染,“只問客觀,不問主觀”,草草立案;又如,只要看到環境被污染,就以污染環境罪立案,而不考慮實際情況,對污染環境罪與安全責任事故罪、非法經營罪等不作細致區分,等等。
“依法嚴懲”某類犯罪,是我國近年來在對某些犯罪確定刑事政策時使用的表達方式,如“依法嚴懲黑惡勢力犯罪”等。根據《刑法》與刑事司法原則,“依法嚴懲”是指在依法基礎之上,實行較為嚴厲的刑法懲治。所謂比較嚴厲的刑法懲治,是指某種行為構成犯罪后在確定刑事處罰特別是刑罰裁量上,在法定量刑范圍內相比較其他類型犯罪應采取更為嚴厲的判罰。研究表明,過去幾年我國法院對污染環境罪的刑事判罰多以輕刑為主,在少數地區存在嚴重污染環境行為“雖被定罪,但未嚴懲”的情形,這是不利于生態環境的刑法保護的,應予以改進優化。
依法嚴懲污染環境犯罪,須加強行政管理與刑事司法的協同。針對當前污染環境犯罪高發的重金屬超標、非法處置危險廢物等情形,各地生態環境管理部門要加強對企業設立過程中生產工藝科學性的審查,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避免企業在工藝落后、必然造成污染物超標的情形下依然上馬。生態環境管理部門應繼續加強環境監察與執法,繼續保持高壓態勢,并將之常態化。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來,由于較好的行政管控,一些地區的污染環境犯罪呈現下降趨勢,但依據污染環境犯罪的生成機理,若企業環境違法的動力機制依然存在,在放松行政管控后必然會出現犯罪反彈,因此,行政執法力度不可降低。
充分發揮整體法治系統功能,加強多元共治,懲防結合,切實提升生態文明刑法保證的質量
刑法功能的有效發揮,須依托整體法治系統。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在污染防治領域,我國已建成比較嚴密的行政管理體系。企業在設立與運行過程中,接受環境審查與監管已經制度化、體系化、日常化。在以打贏“藍天保衛戰”為主要目標的環境保護行動計劃中,督察、巡查、約談等創新性制度已經開始發揮較大作用。應該說,我國的行政法律、環境法律、經濟法律等部門法已經為污染防治、清潔生產等建立了較為嚴密的制度體系。在打擊污染環境犯罪過程中,須做到“打防”結合,高度重視日常管理的有效性,將防治污染環境犯罪的工作重心前移,盡量減少整體社會資源在污染環境犯罪防控上的配置,以整體法治系統為依托來發揮刑法的懲治功能。
污染環境犯罪在世界范圍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發生機制已得到較為明確的揭示。就我國當前來說,在《刑法》已然作出相應規定、司法機關已經打擊與制裁一大批污染環境犯罪的情勢下,一定數量的企業若仍觸犯刑法相關條文,從而構成污染環境犯罪的,行政與司法機關應嚴格執行國家法律,堅決對其依法嚴懲。例如,我國污染環境犯罪中的較多類型是非法處置危險廢物和非法排放重金屬超標,這兩種類型的犯罪在本質上是行為人為追求經濟利益而減少污染防治費用,從而觸碰法律紅線的違法行為,對其進行依法懲治,具有法律上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因此,對這類犯罪的刑事政策應是長期的,不應隨著生態環境質量的局部好轉而動搖甚至改變。
污染環境犯罪侵害的是公眾的環境利益,對其治理也需要依賴多元主體。近年來,我國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在懲治污染環境犯罪過程中,通過新聞媒體宣傳報道,發布典型案例等方式,達到了增強社會認知、獲得社會理解與認同的目的。在未來的污染環境犯罪防治工作中,應進一步加強對相關社會多元主體參與的支持與鼓勵,通過營造“不敢犯、不能犯”的社會氛圍,斬斷企業觸碰刑法紅線的動力機制與心理機制,筑牢污染環境犯罪防治的社會根基,發揮刑法的一般預防功能,懲防結合,切實提升生態文明刑法保障的質量。
依法嚴懲污染環境刑事犯罪,既需要科學立法、公正司法、嚴格執法、全民守法,也有賴于整體社會資源的供給。我們有理由相信,伴隨著我國公民整體素質的提升、綠色GDP觀念在企業生產與政府管理過程中的貫徹、我國環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惡性污染環境犯罪案件的數量會持續下降,我國的生態環境質量會持續向好,“天藍”“水清”“魚翔淺底”“繁星閃耀”將進一步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與向往。
(作者為天津大學法學院教授,天津大學中國綠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參考文獻】
①焦艷鵬:《生態文明保障的刑法機制》,《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