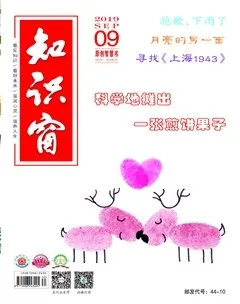阿太拿走的飯團
左蘇
屋已經塌了,黃泥裸露著,苔蘚上閃著雨后還未來得及消散的水珠,瓦礫碎成了大小各異的不規則形狀,高高低低的雜草占地為王。
“回去吧。”母親說。
新房在三百米開外,這里已經久無人來,蚊蟲肆虐,不宜久待。可我想多看看,便對母親說:“再待一會兒吧。”母親知我心有念想,不再言語。
我認出來了,那是廚房,那是飯廳,那是我幼時玩蹺蹺板的地方,那是我趴著寫作業的大石頭。在殘垣斷壁間,往事浮上心頭,穿過萋萋荒草,我在阿太的臥室定住了腳。
柔軟,從心底滋生出來。瘦小的身形,細碎的步子,歲月將故事以皺紋的形式刻在了阿太的臉上。那深深淺淺之間有不舍忘卻的回憶,有我跌跌撞撞的童年光景。
阿太是奶奶的母親,我與弟弟的幼年時光,是牽在阿太手里的。
六歲那年秋天,一對老夫婦拄著拐、背著米袋,顫顫巍巍地站在木門前。他們想要一點米或半碗飯。我正嘟囔著要吃東西,三歲的弟弟也哭鬧著喊餓。
阿太被裹了小腳,步子小,步伐卻快。她走向飯廳,打開飯甑,從那一排團飯中取出兩個,在我和弟弟渴求的眼神中走向了門口,將飯團遞給了門外的兩個老人。看到這,弟弟的哭聲更大了,每一聲嚎啕,都是對自己的吃食被人搶去了的抗訴。
那是20世紀90年代,農家物資匱乏,零食快嘴是奢侈品,家有兩個半大孩子,阿太有她土而有效的辦法。農人家的木桶飯,清早米下大鐵鍋,煮到七成熟,再用撈勺撈到飯甑中,上鍋蒸,一日三餐都在那桶里。撈飯時,阿太會另外做幾個飯團,把七成熟的米抓在手里,加上鹽巴、豬油,左右來回之間,圓圓的飯團就做成了。晌午、半下午,我們的不乖總能被飯團降服。
阿太另外拿了兩個飯團走向我與弟弟,遞過來問道:“阿太餓了,能吃飯團嗎?”弟弟抽泣著,委屈地點點頭。“他們也是別人的阿太,他們也餓。”阿太指了指門口,那里已經沒有人了,但她說的是誰,我們都懂。
“他們家沒飯吃,才出來討,我們有飯吃,分一點給他們,他們就不餓了。”那時,討食的人多,一抓米,半碗飯,一點酸菜,阿太總不吝嗇,我曾偷偷地在心底心疼。可阿太總說,我們家能吃飽,比他們好過。
阿太不曾入過學堂,也不曾識得幾個字,甚至因為裹了小腳,她連走出那四面環山的小村都極少。可她勤勞、善良、寬厚,把自己的口糧勻一點兒給討食者這樣的事情,她做了不知多少次。
她告訴我們,人要有善心。
她告訴我們,人要有底氣。
她告訴我們,人要有度量。
當我從課本上看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時,阿太已經離開了我,但她的善心善行早已將這句話最深的含義烙在我心底。那是我年幼時的啟蒙,是我成長中的一盞燈,是她為我扣上成長路上的第一粒扣子,端端正正,齊齊整整。
我站在那里,往事拂動,那時,光景卻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