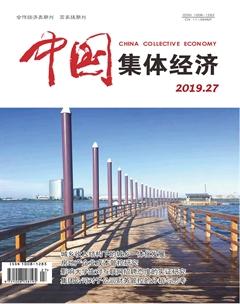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面臨的困境及優化路徑
羅曉蓉
摘要:黨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領導基層治理的堅強戰斗堡壘。基層黨建是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基礎,與基層治理有效性緊密相關。隨著社會深刻轉型和城市化進程加快推進,需要構筑基層黨建工作的新平臺。目前,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發揮在干群關系和服務群眾、工作機制、組織關系、社區治理方面面臨著困境。優化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有效性的路徑以社會資本為視域,從符號建構、空間覆蓋、強化服務、政治引領入手。
關鍵詞:基層黨建;基層治理;治理有效
基層黨建是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基礎,與基層治理有效性緊密相關。隨著社會深刻轉型和城市化進程加快推進,需要構筑基層黨建工作的新平臺。目前,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面臨尚存在一些困境亟需破解。
一、面臨的困境
1. 干群關系上,一些村民埋怨村干部“吃白飯”,對村支“兩委”干部不信任、意見大;服務群眾上,一些城市社區黨組織對服務群眾、加強區域化黨建工作“有心無力”,“滿足于應付、流之于形式”的現象較為普遍。
發展農村經濟,帶領農民致富是農村黨建工作的落腳點。目前,一些村的村支“兩委”干部是由上級政府任命的,或選舉過程只是走走形式而已,甚至有些人通過拉關系走后門當上了村支“兩委”干部;不少村支“兩委”干部辦事不講政策、管理不循章法、工作隨意性大。有的村支“兩委”干部事事先為自己或者家族、親友打算,有的甚至隨意欺壓百姓,拉幫結派,貪贓枉法,為所欲為。村民對村支“兩委”干部不信任、意見大,既指向村干部的工作能力,也指向村干部的工作態度。村“兩委”干部為民辦事能力不強,工作缺乏積極性,一度使村黨支部幾乎陷于癱瘓狀態,村民埋怨干部“吃白飯”,極大的損害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形象。
村(居)黨支部是基層治理的最佳抓手。但是,在城市社區,一些上級黨委和政府職能部門把社區當成自己的派出機構,隨意攤派工作任務。計劃生育、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重點項目建設、棚改征地以及拆除違章建筑等大量事務被交由社區辦理,而且還下達指標任務,進行相應考核和獎懲。社區“責重”而“權少”,“行政化”“衙門化”傾向較為嚴重,變成了“準政府”“傳聲筒”“二傳手”。近年來,隨著縣域經濟跨越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舊城區改造步伐加快,新城區規模日益擴張,縣城居住人口不斷增加,各種類型的黨員也向城區集聚,城市基層黨建工作內涵發生了較大變化。而社區黨組織負責人往往淹沒于繁重的日常事務中,除了做好常規性“中心工作”,還要配合相關職能部門開展一系列的臨時性工作。其中行政化任務繁多,并且征收社會撫養費、拆“兩違”、創衛、征兵等多達近百項。每一項行政任務被提上了高度,僅靠5~7人社區配備的社區工作人員來完成,精力疲乏,難以應對,社區黨建常常流于形式更難有創新。
2. 工作機制上,一些農村基層存在村級重大事項決策不知曉、政務不公開、參與度不高,極大影響村支“兩委”干部威信和信任;而一些城市社區黨建的整體推進力度不夠,整體功能不強,導致“各搭各的臺、各唱各的戲”。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群眾更加關注自己的民主權利,參與決策、管理、監督基層事務和重大問題的要求日益強烈。但是,一些村級組織治權衰弱。例如,在村級自主招商、對外招商等方面,項目資金只是“文件監督”“材料審核”,沒有真正將財政公開真正落于實處。使用過程中,還存在“打包”“捆包”和多用、挪用現象;財務公開無法至始至終的貫穿全過程。村級財務不公開、不透明,干群缺乏溝通交流,導致村民對有業績的村干部甚至也存在懷疑、抵觸心理。雖然城市社區建設經過近20年的發展,但是城市社區黨建的方法、手段和載體有待創新,黨員融入社區服務亟待完善和加強。目前,城市社區建設中,組織、宣傳、統戰、政法、民政、群團組織等參與社區管理的部門眾多,職能交叉但缺乏協調。
3. 組織關系上,協調不夠,出現“相互扯皮”“各自為戰、多頭管理”,甚至社區黨的領導“停在口號上”,政府服務“浮在表面上”,居民自治“留在文件上”。
村“兩委”之間關系缺乏協調性,部分支委與村委之間存在嫌隙,支委對村委的矛盾糾紛等日常業務推諉,極大的降低了矛盾協調的實效性。村“兩委”與村內自發性組織(如理事會等)的關系缺乏協調性,村“兩委”解決村級事務大多數單純依托鎮干部、村委會班子討論事務的方式來決定,村民對村級事務參與度不高,很多項目不了解、不知情,工作的開展難度比較大。
4. 社區治理中,村干部工作積極性不高,存在“工作難溝通,環境難治理,上訪難平息”的“三難”問題;而城市社區治理中,普遍依靠行政力量來推動整合社會資源,社區居民“看客心態”比較普遍,出現“搭便車”的集體行動困境。
干部工作積極性不高,在一些傳統農村村落社區具體表現為:一是逼著干。安于現狀,既沒有村級發展長遠打算,又沒有工作上的短期周密安排,僅僅把工作定位在保證工作正常運轉和村穩定上。二是跟著干。應付日常工作,沒有帶領群眾致富能力,不會抓農村工作。三是瞞著干。重點方向不明,上面安排啥就比劃啥,不善于調動群眾。農村社區治理中面臨“三難”問題,工作難溝通、環境難治理、上訪難平息問題。城市社區治理中,靠行政推動力來整合社會力量的方式很難吸引居民參與。
二、優化路徑
1. 符號建構:以黨支部為核心,結合社區社會資本的總量和分布特點創建黨建引領社區治理的項目和品牌。
目前,各地基層黨建基地建設和基層黨組織建設中,無論是黨建主題文化廣場、樓道黨建宣傳欄及黨員活動室等場所,還是黨建綜合體和黨建聯盟構建,都突顯以黨支部為核心和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在城市社區,黨組織建設和完善調整成為創新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切入點。在農村社區,構建以村黨支部為核心的同心園,以村黨支部為核心,統籌謀劃村級治理結構,需要結合各類型社區社會資本的總量和分布展開。傳統農村村落社區,注重運用傳統的社會資本,如家庭社會資本、家族社會資本、鄰里社會資本。針對“空心村”現象比較普遍問題,村支兩委組織尤其是村支書需要在“黨建+”工作內容上亟需根據適宜發展的農業產業,同時通過產業融合,努力做到“三富”:自己帶頭富、幫助群眾富、堂堂正正富。在村莊治理上需要“用公心來治理,用發展來治理,用撲下身子來治理,用匯聚合力來治理”,做到“沒事要找事”(主動去發現問題,從早了解問題,盡快處理問題)“出事不怕事”(遇到矛盾糾紛要敢于面對。做到不怕、不躲、不推、不拖,及時組織專班化解矛盾糾紛)“處事要了事”(做到“上管好天文地理,下管好雞毛蒜皮”)。在城鄉交融發展而來的村居合一型社區,傳統社會資本鑲嵌在傳統的血緣關系等各種社會關系網絡中,如禮俗、人情、關系等,同時也出現蘊含現代社會資本的組織。對于這類社區,由村級黨組織和村居黨組織聯建聯管,要逐步向社區黨組織轉型,這意味著組織結構、治理對象、管理結構帶來全新的變革;而通過中心村改造后土地適度集中,企業集聚形成的功能拓展型社區,現代社會資本的載體更多出現,則需要在保留村級管理體制的基礎上,升格村級黨組織,下設農村、社區、企業各類黨支部,實行分類管理。
2. 空間覆蓋:依托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初步成形格局,深化區域化黨建工作,創建社區黨建聯建(合)體,“強堡壘、強隊伍、強作為、強引領”。
目前,社區網格化管理已經由特大或大城市管理延伸到中小城市和縣城管理。網格化管理是行政主導的管理模式。依托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初步成形格局,各地社區打造黨建聯盟綜合體,以盤活社區內各資源,形成“資源供應鏈”,將資源與需求有效對接。定期召開黨建聯盟聯席會議,共商黨建工作,共用服務陣地,通過建立區域黨建聯盟,打破社區、企業、學校、社會等各類黨組織之間的“無形藩籬”,同時,黨建聯盟聯席會議通過統籌、協調、聯絡作用,明確成員黨組織職能職責,合力推動責任落實。在黨建聯盟綜合體內,通過“兩代表一委員”工作室,區域黨工委組織在社區工作的、在社區居住的或者掛點社區的省、市、縣、鎮四級“兩代表一委員”輪值坐班,接待群眾,收集問題。由社區黨支部牽頭,匯總收集到的問題,建立問題清單,交辦至各聯盟成員,確保事事有著落,件件有回音。創建黨建聯建體,實現了組織聯建強堡壘,增強了黨建工作載體,有利于克服聯誼式、人情式、援助式運行狀態,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初步形成整體性的黨建聯建體,組織聯建強堡壘,抱團夯實黨建基礎。
3. 強化服務:以居民需求為本,克服“水土不服”;通過建章立制,確保服務規范運行。
強化服務是政治引領的基礎和前提。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服務功能,需要基層黨組織設計服務活動項目以群眾需求為本,否則,黨建服務活動與群眾需求脫節,容易產生“裝點門面”“水土不服”。為此,著力強化社區組織建設,拓展服務載體。一是構建社區區域化黨建新格局。健全基層黨政聯席會議制度和共駐共建制度,大力推廣“樓宇黨建”等新型區域化社區黨建模式。依托區域化黨建平臺,開展社區服務活動,如組織黨員對轄區困難群眾慰問、開展“微心愿”認領等。二是完善社區服務組織。本著從社區廣大居民的客觀需求出發,在規劃的基礎上,出臺優惠政策,加大扶持力度,重點支持為社區老年人、婦女、兒童、殘疾人、失業人員等特殊群體服務的公益性組織。三是培育和發展各類社區自助組織。要按照“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原則,通過挖掘文體骨干、培育文體團隊、組織文體活動等,使社區居民學在社區,樂在社區。在社區活動中,增強居民參與,建立信任關系,提升社區歸屬感,增加社區現代社會資本,為社區善治打下扎實的基礎。
4. 政治引領:嵌入基層協商民主實踐,提升黨的基層組織組織力。
在多元治理格局中,基層黨組織必須突出政治功能和政治作用。目前,城鄉社區正在進行基層協商民主實踐,黨建引領是前提,要突顯基層黨組織必須突出政治功能和政治作用。比如,多地通過運用協商民主的形式,妥善解決了社區業主普遍反映的社區公共事務和社區管理問題。當下,亟需在“黨建+”工作嵌入基層治理的長效機制探索實踐,以“黨建+民主協商作為重要的抓手和發展趨勢。只要“黨建+”工作,融入中心工作,轉變基層組織體系,創新組織設置;在強化服務的基礎和前提下突出政治引領,在多元治理格局中,優化功能實現,突出政治功能和政治作用;持續改進服務方式,以嵌入式服務為突破口,專注于問題的解決與變化,運用社會工作理念與方法,幫助社會成員適應社會環境、融入社會環境,將有利于社區社會資本的提升,極大促進社區治理。
參考文獻:
[1]林尚立.從基層組織中開掘黨建資源[J].探索與爭鳴,2002(07).
[2]馬敏.政治象征符號的工具價值分析[J].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04(04).
[3]龔上華.農村黨建嵌入基層治理——以杭州余杭區丁河村“黨建+”引領議事協商為例[J].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