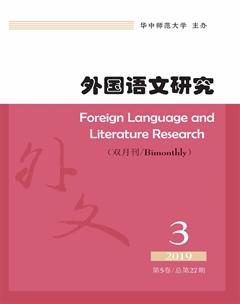從敘事學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胡亞敏教授訪談錄①
萬思敏 丁鈺穎 胡亞敏
內容摘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批評話語應成為文學理論工作者的重要使命。為推進對相關重要理論話題的理解,應華中師范大學“外國文學與比較文學”青年學術創新團隊負責人何衛華教授的邀請,國內文學理論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胡亞敏教授于2019年5月6日做客“華大外國文學論壇”。此次論壇由羅良功教授主持,在論壇期間,胡亞敏教授接受了外國語學院萬思敏和丁鈺穎兩位同學的采訪,訪談圍繞敘事學、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這三個方面展開。在訪談過程中,胡亞敏教授首先回顧了自己從事敘事學研究的初衷,介紹了專著《敘事學》的學術特色及未來敘事研究的方向,接著就自己在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和比較文學領域的學術創新與理論貢獻和大家進行了交流,最后胡老師不僅分享了自己今后的學術研究計劃,還給從事文學研究的師生提出了寶貴建議。
關鍵詞:胡亞敏;敘事學;弗雷德里克·詹姆遜;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比較文學
Abstract: The formul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come a task of utmost importance for scholars working on literary theory under the current historical situ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major theoretical topics, Professor He Weihua, who is now leading the Youth Academic Innovation Team on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vited Professor Hu Yamin,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theory studies, to attend “CCNU Foreign Literature Forum” on May 6, 2019. The forum was chaired by Professor Luo Lianggong, during which Professor Hu accepted an interview with Wan Simin and Ding Yuying, two postgraduates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he interview focused on narratolog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During the interview, Professor Hu Yamin looked back into her motivations of working on narratology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her academic career, introduced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her monograph Narratology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narrat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n talked about her academic innovations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in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finally shared with us her future plans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d offered valuable advice to young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literary studies.
Key words: Hu Yamin; narratology; Fredric Jameson;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一、作為緣起的敘事學研究
萬思敏(以下簡稱萬):胡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讓我們有這樣一次寶貴的學習機會,能夠當面向您請教。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您就一直在高校從事文藝學和比較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至今已有40多年了,并且取得了十分豐厚和令人矚目的學術成就。如果歸納一下您的學術思考和研究成果的話,大致上應該可以分為三個主要方面:首先,您是國內率先介紹和研究敘事學的學者之一;第二,您提出并帶領團隊致力于建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第三,在比較文學領域,您提出了“開放的民族主義”、“差異性研究”等有影響的理論概念和學術命題。今天,主要想請您談談您的治學體會。
胡亞敏(以下簡稱胡):好的,謝謝!很高興來到外國語學院,我跟你們的幾任院長都是很好的朋友,我還有幾位學生現都在外國語學院任教。可以說,我對外國語學院有特殊的感情。長期以來,文學院與外國語學院的交流頻繁,關鍵時刻相互支持。何衛華老師跟我說的時候,我本來還是有點忙,有好多事情,但是我想這個事情義不容辭,就來和我們的老師和同學們一起聊一聊。
萬:謝謝胡老師!您的學術生涯可以說是以敘事學研究為開端的,今天在場的不少青年老師和研究生同學都是從您的《敘事學》開始了解您的,那么我們此次的訪談就從敘事學開始。首先,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敘事學研究大致是一種怎樣的情形?您是如何進入敘事學領域的?
胡:20世紀80年代初,敘事學在國內只有少數幾位學者介紹過。記得有一次,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時碰到一位作家,他問我什么叫自由間接引語,我說只有直接引語、間接引語,哪有什么自由間接引語。我當時就不知道,因為這個概念那時候還沒有進入國內學界,我到圖書館查了很久,一直沒有找到這個說法的來源。后來找到一本書,書名為《雙重聲音》(Double Voice),里面說這個“雙重聲音”就叫自由間接引語。花了一個星期,我就把這本英文書看完了,并做了研究,后來就又把它寫出來了,發表在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②因此,就中國的敘事學研究而言,我應該是中國學界進入敘事學領域的先遣部隊,屬于“醒得早”的那批人。這有點像他們說我們武漢人的性格,就是醒得早,但是有時候又起得晚。
至于為什么要研究敘事學,就不得不稍微說遠一點了。1977年我畢業留校,本來很喜歡外國文學,我讀過不少外國文學作品,從古希臘到19世紀的一些文學名著,特別是巴爾扎克的書,什么《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等等,這些我都讀了,但是留校后被分配到文學理論教研室。在高校工作又得讀研,碩士研究生期間我攻讀的方向是中國古代小說理論。記得報考前,我惡補了郭紹虞和敏澤先生的書,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發展輪廓有了大致的了解。并找老教師借了關于西方形象思維和弗洛伊德等的資料來讀。我當時已經覺得原有的框架過于呆板,用什么樣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特別是古代小說理論就成為一個問題。為撰寫碩士論文,我專門到北京查資料,經周偉民老師介紹,我認識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國外漢學研究室,現在叫比較文學研究室的尹慧珉老師,跟尹老師一見如故,很投緣,她的女兒叫胡康敏,跟我的名字差一個字,她還說我的性格和她很像。她還在武漢工作過,一直把我當她的女兒看,對我幫助很大,在她那里,我了解到西方不少最新的研究資料。當時尹老師給了我一本加拿大學者寫的有關中國近代小說的書作參考,書名為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小說》),我回來認真讀后,被這些漢學家的研究角度吸引,他們都是用敘事學的方法研究中國近代小說,給人一種別開生面的感覺。我和我的同學張方決定把它翻譯出來(該書于1990年在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在翻譯過程中,我查閱了大量資料,發現其中有一位漢學家說中國沒有敘事理論,這一斷言在某種意義上傷害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于是我就想看看中國到底是否有敘事理論,并開始收集明清以來的小說評點史料。后來我把我的碩士論文選題定在明清小說評點,更具體地說,就是金圣嘆的小說評點,研究方法則直接采用了敘事學的框架。
簡單歸納一下,我選擇敘事學原因有二:一是為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理論尋找新的方法和觀照角度;二是回答中國是否有敘事理論這個問題。如果有,又有哪些貢獻?可以說,整個20世紀80年代,除教學外,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從事敘事學的研究。
丁鈺穎(以下簡稱丁):您的專著《敘事學》是國內敘事學領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1994年出版后分別于1998年、2004年兩次印刷,2014年再次由臺灣若水堂書局修訂出版,受到了國內外學界的關注。在2012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圖書學術影響力報告》中,《敘事學》被列為對外國文學研究具有重要學術影響力的54種學術著作之一。與西方經典敘事理論相比,您的《敘事學》有著自己獨特的學術特色和理論貢獻,您能否就此為我們做一些介紹嗎?
胡:我研究《敘事學》首先是學習,要搞清楚敘事學是什么,這就需要讀書。當時,凡是我能夠找到的與敘事學有關的中文和英文書我基本都找來讀了,包括我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學,也主要是在收集材料和閱讀材料。我曾將我的讀書筆記整理提煉后以《結構主義敘事學探討》為題發表在《外國文學研究》1987年第1期上。我現在還記得我閱讀列維·斯特勞斯《野性的思維》時的困狀,說了一句“經典”的話,“失眠了,不用吃安眠藥,讀結構主義吧。”
在撰寫《敘事學》一書時,我覺得如果只是跟在別人后面走,那就沒有什么意思。應該說,《敘事學》這本書中有我的一些思考,有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希望同學們在關注《敘事學》的視角、敘述者和時間的同時,也可以了解一下我在《敘事學》一書中的拓展。
首先是力圖突破結構主義敘事學的封閉性。我認為,敘事理論如果沒有閱讀、沒有讀者的參與將是不完整的,因此在《敘事學》中我增加了“閱讀”這一章,把經典敘事學研究撕開了一個口子,引向了閱讀,強調文本的未完成性和可交流性,強調讀者的自主性、參與性和創造性,由此在形式批評的基礎上加上了意義闡釋。在“閱讀”一章中,我還提出了兩個有意思的概念,“空白”與“矛盾”。我想說的是,在閱讀的時候,讀者不僅要看到敘事文本說了什么,還可以尋找沒有說出的故事,并品出其意義。至于矛盾閱讀,就是不僅要看到作品的完整和統一,還可以去感受敘事作品本身包括人物、情節和話語的矛盾和張力。其次,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理論觀點。一個是對“情節的完整性”的質疑,在《敘事學》中,我專門對非線性情節作了闡述,強調非線性在敘事中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情節的完整性并非敘事的真正特征,如今這些觀點在后現代語境中已成為常識。第二個觀點是強調人物的“未定性”。結構主義敘事學對人物關注不多,且有把人物類型化、固定化的問題,如英雄、壞人、幫助者、施惠者等。我提出“人物是一個過程”的觀點,為小說中的人物向自身對立面轉化提供理論支持。當時只是理論設想,一時未找到恰當的例子,后來我讀了陳忠實的《白鹿原》,發現里面的田小娥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第三,借鑒語言學理論,提出了陳述文本、疑問文本和祈使文本三種類型,作為劃分文本類型的新標準,在《敘事學》中重點闡述了疑問文本。這類文本與陳述文本相反,敘述者不是采用肯定的語氣,而是持詢問或矛盾的口吻,要求讀者思考和回答文本中的問題。我很喜歡疑問文本只提出問題不提供答案的模式。
再則,我還嘗試提出敘事語法程序。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討論文學批評方法論時我就提出文學走進計算機的設想,并主張“未來計算機創作的作品與作家的創作并行不悖,競放異彩”。③記得是1985年開會,我還是助教,當時就老在想文學創作如何走進計算機,并且同一些學術同行進行了交流。此后,為了研究敘事程序,我專門買了好幾本模糊數學的書,并設計了四套程序,④最后我發現計算機無法模擬人的豐富情感和想象力,不得不感嘆,敘事與計算機之間存在著一道深深的壕塹。不過,當今數字技術發展飛快,部分問題已得到解決,人工智能創作的詩歌已經可以達到亂真的程度,不過敘事文還未見獨立的成熟之作。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的《敘事學》,還是有些粗燥和稚嫩,在《敘事學》再版“后記”中,我用了“敝帚自珍”一詞,以紀念自己“初入世的英勇”。
萬:近年來,敘事學研究出現了諸多變化,從研究敘事結構、敘事語法等的經典敘事學研究走向了后經典敘事學,從單數的敘事學擴展為了復數的敘事學,您能否就近些年來敘事學發展的熱點談一談您的看法以及您對于這方面的思考?
胡:這個我進行過一些思考,關于未來的敘事研究,我覺得有兩個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敘事與政治的關系;二是敘事與技術的關系。
就敘事與政治的關系而言,我主要關注意識形態敘事,意識形態敘事主要想運用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方法把形式分析與歷史闡釋、政治批判結合起來。意識形態敘事強調要恢復敘事的歷史維度,關注敘事作品的歷史語境和歷史發展,同時更重要的是揭示敘事作品所體現的主體意識形態建構和被遮蔽的政治無意識。在敘事文本中,你說什么不說什么,什么詳說什么略說,以及故意省略了什么,這背后都會含有政治因素。
關于敘事與技術的問題,2018年,在漳州召開的敘事學會上,我作了一個發言,題目就是“敘事與數字技術”。在發言中,我主要談了在數字技術沖擊下敘事性質被重構的問題,主要包括五點:首先,數字技術將改寫敘述者的定義,敘述者不再是敘述而是對互聯網數據庫進行搜索;其次,超鏈接的功能將使敘事時間成為可疑的概念,文本將成為動畫、圖形、音樂等不同格式的文件的鏈接;第三,在線技術的交互性構成了對情節邏輯結構的沖擊,讀者的主動參與使情節變得不確定,故事流向未來;第四、讀者與作者共同合作中,閱讀也將不再是閱讀(read),而是嬉戲(play);最后,迷失成為新的要素進入人們的審美體驗。數字敘事的發展還需要時間,未來還不確定,存在著很多可能性。
二、詹姆遜與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
丁:在您的學術道路中,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研究應該說是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在20世紀90年代, 您研究的重心從敘事學轉移到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您做出這一學術轉向是基于怎樣的考慮呢?
胡:之所以在20世紀90年代轉向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這一選擇始于責任,或者說是情勢使然。華中師范大學是馬列文論研究會的駐會單位,薪火相傳,需要有人接替和堅守。另外,在當知青時,我就讀過了馬恩列斯的六本書,包括《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和《反杜林論》等。其次是在教學和研究中對形式主義批評產生了一些疑惑。1992年,我在開封河南大學召開的中外文論會議上做了大會發言,主要就是反思形式主義批評,結果發言超時了。我重點討論了結構主義敘事學。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是比較有效的分析手段,但到最后似乎所有作品都成為了“文明與自然”、“盛與衰”、“善與惡”、“聰明與愚蠢”等二元對立,文學作品豐富的肌質沒有了,有時候這確實會讓人感覺有些悲哀。我也不同意俄國形式主義的一些說法,特別是什克洛夫斯基的話“藝術不反映城堡上空旗幟的色彩”。其實,“陌生化”通過創造出一個不同于現實世界的事物本身就具有政治因素。文學作品不可能完全自足,不可能擺脫政治、資本和技術等外界因素的影響,更不可能獨立地立世于世界。
丁:如果一定要找到一個起點的話,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應該是您從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開端”。1997年,您還邀請詹姆遜教授訪問了我校,您能否談一談詹姆遜對您有什么樣的影響和啟發?
胡:轉向詹姆遜研究首先是閱讀了唐小兵翻譯的詹姆遜在北大的講演稿《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1992年認識了王逢振老師,受他委托,參與翻譯“知識分子圖書館”叢書項目中詹姆遜的《快感:文化與政治》。當時翻譯得很苦,但也很受感動,我被詹姆遜對馬克思主義的真誠信仰和關注現實問題的勇氣和熱情所打動,就產生了研究他的愿望。1997年我邀請詹姆遜訪問華師,這成為華師老師們一段美好的記憶。隨即我又承擔了翻譯詹姆遜《文化轉向》一書的任務,對詹姆遜所關注的后現代現象有了更多的了解。后來在美國訪問期間我特地去拜訪了詹姆遜,他家里的每個房間都是書,墻上掛有馬克思和毛澤東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拍的是一位英俊的年青人,像電影明星,我問詹姆遜這個人是誰,他告訴我,是青年時代的馬克思,我們一同在這張照片前合影留念。詹姆遜涉獵廣泛,智力過人,在翻譯了他的《文化轉向》后,我對這一點的感觸十分深刻,詹姆遜研究了包括圖像、建筑乃至房地產等諸多領域。他對科幻電影也有著濃厚的興趣,他說他看了四百多部科幻電影,真是不容易。
丁:您對詹姆遜的理論并不是完全認可,在我們看來,您在很多方面更多的是一位詹姆遜的對話者,您如何看待這種對話的重要性?
胡:對,我佩服詹姆遜,但并不完全贊同他的觀點。在研究詹姆遜期間,我寫了兩篇文章,一篇題目是《不同語境下的后現代——與詹姆遜的對話》,另一篇是《理論仍在途中——詹姆遜批判》,后一篇是2004年5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詹姆遜與中國”的國際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與詹姆遜作了面對面的交流。這里對詹姆遜的“批判”是在康德意義上來講的,有對話和建設之意。當時我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質疑。第一是歷史觀問題。詹姆遜在《政治無意識》中喊了一句口號,“永遠歷史化”,強調歷史的絕對視野,但同時又說人們接觸的只是歷史文本,歷史則是一種“缺席的存在”。我認為這里存在悖論。當然,詹姆遜認為我們沒有虛構歷史的自由,這一觀點我是贊同的。第二是泛政治化的問題。詹姆遜說馬克思主義是不可超越的視野,他的元評論展示了新馬克思主義批評的包容性,但多種視角的并存產生的張力可能導致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泛化,而馬克思主義的泛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弱化。第三,詹姆遜文學批評中的政治性理解有圖解文學的傾向。他把《呼嘯山莊》里希斯克里夫的行為看作是原始資本家向莊園主的復仇,將這種凄厲的故事變成了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爭斗,這種解讀削弱了故事原有的感染力。對于我提出的幾點意見,詹姆遜作了初步的回應,這次對話也加深了詹姆遜對中國學者的認識。他后來還說“希望在中國”。
我個人覺得,面對研究對象,特別是西方理論家,對話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為任何知識必須經過自己學習、質疑和消化后才能夠成為自己的知識,知識的接受必須要以對知識的懷疑為前提。就師生來說,也是這樣。唐朝有個書法家叫李邕,他說過一句話,“似我者俗,學我者死”。亞里士多德同樣有句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說的都是類似的道理。研究問題需要保持理性的思考和獨立性。此外,對西方文學理論的研究還需考慮不同的語境,我論文中說到的“不同語境下的后現代”就是從不同語境入手的。
萬:2018年,您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研究”順利結題,這一重大項目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評審組專家的高度評價,認為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理論價值。在這一重大項目中,您提出并致力于建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您提出這一課題是基于怎樣的學術考量?
胡:建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是我們團隊一直在努力的目標,這一項目從2011年立項到2018年結項,歷時七年。為什么提出這一課題?原因有二:一是我們這里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重鎮,我們應該把這面旗幟繼續舉起來;二是在研究詹姆遜以后,我覺得我們的學術應該面對中國大地。2015年我們開國際會議的時候,有個學者說,他覺得現在的理論生長點在中國。為什么理論生長點在中國?因為中國正處于轉型期,這一時期自然會出現許多的問題,這些問題都可能成為理論的生長面。對這一點,我是贊同的。現在的中國,的確有很多問題有待研究,如資本、價值觀缺失、技術等問題,就其中的很多問題而言,不可能完全從經典馬克思主義那里找到現成答案,也不可能僅靠異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來應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必須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才能有效地回應這各種問題,才可能展開與世界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的對話。作為首席專家,我與課題組成員在七年的時間里,發表了77篇學術論文。其中我自己撰寫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三十年》和《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人民觀》這兩篇文章都在《文學評論》作為“頭條”刊發。專家組成員對我們的項目做了充分肯定。
萬:在您看來,就這一重大項目本身及其成果而言,最為重要的學術創新和理論貢獻在哪一些方面?現在這個時代日新月異,文學越來越受到其他諸多因素的沖擊,面臨著來自于諸多方面的挑戰,請問這一重大項目對當今文學和文化建設會有怎樣的啟示作用?
胡:正如我前面已經指出,這一重大項目是集體的成果,我這里僅談談我個人提出的一些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觀點。首先是為“人民”概念注入了新的內容。人民并非一個抽象的或同質性的概念,而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是由千千萬萬真實的個人組成的。“人民優位”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國形態”的特色,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結晶。其次對“民族”概念作了辨析和新釋。“Nation”應與“中華民族”對應,民族是一個歷史的概念,人們沒有憑空想象民族的自由,民族的核心在于文化,沒有文化,沒有民族記憶,就意味著該民族的消亡;民族與人民同構,人民是民族的主體。三是探討了政治與審美的關系,我認為,審美本身就蘊含了政治,審美范疇和審美形式也蘊含政治因素,如崇高、隱喻、反諷、救贖,這些范疇或明或暗地激蕩著某種意識形態的風云。審美過程中的生命體驗、想象乃至審美所體現的自由和超越均內含對理想的追求,而這種追求往往與政治不謀而合。審美形式也與政治有關,當代藝術家通過創造性變形,沖破日常經驗的束縛,對世界進行重新編碼或重塑,這不一樣的世界中就蘊含著政治的意味。不過,這種政治不是通過激烈的行動,而主要是通過構建新的觀看、思考、交談和存在方式,重新塑造人們的需要、欲望、感覺和想象,并通過改造人的審美意識來改造世界,促進社會變革的可能性。
這一重大項目同樣對同文學和文化建設相關的一些重要議題做了一些創造性的理論探索:首先,對文學與科技的關系作了辯證分析。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著眼于對高科技的警惕和批判不同,我們注意到了高科技對文學的革命性影響和科技的意識形態建構功能;其次,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學性質作了重新闡釋。文學不僅具有審美屬性和意識形態性,而且具有商品屬性,這一觀點有助于更準確地把握當下作為藝術生產的文學的性質和功能;三,針對當今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價值判斷缺失或失范問題,設計出以人的解放為核心的價值重建標準,提出考察作品應以是否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價值判斷的根本準繩等。這些研究為當今中國文化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撐,也是中國學者對當今問題的思考和探索。
三、比較文學與中外文學批評
萬:就您的學術研究而言,中外文學批評研究同樣是不可忽略的組成部分,您在這一領域同樣提出了眾多有影響的理論觀點。在比較文學和中外文學批評領域,近幾年不少學者開始討論“世界主義”與“世界文學”,您曾經也提出過“開放的民族主義”這一概念,您能否就此談一談您的看法?
胡:中外關系一直都是我學術思考的焦點。就研究中西文學關系而言,一定要立足于本土現實,著眼于人類面對的一些共同問題,跟世界對話。2001年4月在北京師范大學與湖南師范大學聯合舉辦的“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學民族性問題”的學術研討會上,我作了“重返民族性”的大會發言,提醒中國學者在追蹤西方文學批評思潮的途中別忘了回家的路。發言稿后來以《開放的民族主義——論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之立場》為題發表,開放是民族發展的動力,民族則是開放的同心圓。“開放的民族主義”需要超越東西方等級秩序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最大限度地向異質文化汲取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因素。總體上來講,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是一個比較開放的民族,但如果自我封閉,必然的結果就是退化。同時,“開放的民族主義”還力圖說明民族性中蘊含著普遍性,沒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是沒有意義的。
丁:在如今全球化的語境之下,作為一個內含悖論的術語,當然更多的是合理性,“開放的民族主義”這一說法的確給我們提供了諸多啟示。事實上,當下的中國文學批評受到了西方的諸多影響,換言之,在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運用西方的理論概念、評判標準和價值觀來審視和分析中國的文學和文化,試圖將西方的標準挪用到中國的語境之中,對此,您曾提出“差異性研究”這一概念,您能否闡釋一下“差異性研究”的具體內涵和運作方式?在中國建設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學批評的道路上,這一概念具有怎樣的操作性?
胡:全球化時代如何避免學術研究的西方化或同質化,是我寫作《論差異性研究》一文的緣由。在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第二屆世界漢學大會上,我作了題為“堅持差異性研究”的發言,后以《論差異性研究》為題發表。差異性研究不同于比較文學的“變異學”概念。一是差異性研究更強調本土立場,強調的是主體性,而不是停留于探尋西方文學和文化在中國的流傳和變異;二是差異性研究更強調建構性,而不是僅僅研究中國文壇對西方的接受、誤讀和吸收。差異性研究的“差異性”是蘊涵普遍性的差異性。
丁:在2014年,您主編的《西方文論關鍵詞與當代中國》⑤一書順利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2015年被中國社科出版社評選為本年度20部好書之一。在《建構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論話語體系的基礎工程》一文中,復旦大學朱立元教授對該書有高度的肯定,您能否談一談這一著作當中有什么樣的學術亮點?您如何看待西方文論關鍵詞與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之間的關系?
胡:概念是理論的基石,關鍵詞研究一方面是做基礎理論的工作,另一方面是方法論方面的探索。這本書是對中西文學批評關系在概念上的學術清理,精心挑選了20世紀后半期即1978年以后出現在中國文壇上的10個西方文論關鍵詞,深入細致地揭示其歷史脈絡和豐富的異質性。在很大程度上,這本書可以被說成是一次非常細致的、深入的、沿途有著各色風景的“理論旅行”。同時,采用歷史和比較的方法,將“歷史場域”細化和拓展為四個相關聯的階段,具體包括初始場域、生成場域、延展場域和本土場域。并將關鍵詞置于當代中國文化語境之中,探尋其在中國的譯介、變異和融合。通過關鍵詞這一紐帶,在中外文學批評碰撞和交匯中構筑中西文學批評交流對話的平臺。我們在完成《西方文論關鍵詞與當代中國》一書時并沒有太大預期,這本書是國家社科基金結題成果,并被鑒定為優秀,后來該書入選《成果文庫》,特別是得知該書入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20本好書中三本文學類書籍之一,非常高興。還有一個好消息,勞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也為我們這本書在國外出版做了預告。
萬:您在學術界辛勤耕耘四十載,在敘事學研究、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和中外文學批評研究等領域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最后您能否談一談您今后的學術計劃和安排?以及對從事文學研究的青年教師和學生,您有什么建議?
胡:對于今后的學術計劃和安排,要做的事情很多,就個人而言,仍會主要立足于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研究。馬克思主義具有強大的闡釋力,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我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是一本剛打開的書,下一步的一個打算就是要重鑄經典,換言之,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研究放在他的整個理論背景乃至整個西方文化背景下研究,我還想審視一下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扭曲,并通過重鑄經典,進一步展開對世界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流派的交流和對話。此外,我還對文學和科技的關系感興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令人驚嘆,科技對文學發展的影響也越來越突出,我希望為文學插上科技的翅膀。在教學改革方面我也有一些新的設想,我將把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和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作為新一輪教學改革的重點。
對在座的青年教師和學生,我想說的是,首先要確立自己的研究領地,這塊領地可能是你的興趣愛好,也可能是工作的需要,但無論哪一種,都必須遵從內心的呼喚。同時,做學問一定要沉靜勿躁、厚積薄發,《敘事學》一書經過“二千多個日子的慘淡經營,四易其稿”(初版后記)。編著的《比較文學》從動筆到2004年出版,時間更是長達二十年之久,一個人的學術水平并不完全在于項目和論文的多少,而在于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有價值的知識和學術思想。但厚積薄發不等于延宕,要趕緊做起來。現在的誘惑和干擾都很多,但時間不等人,放棄了現在就等于放棄了未來。至于是否成功,還是那句老話:“做最好的自己”就是成功。
萬、丁: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
注釋【Notes】
①在本訪談問題的擬定、文稿的修改和完善過程中,何衛華教授提出了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致以謝意。
②參見胡亞敏,論自由間接引語,《外國文學研究》1(1989):81-83。
③參見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86。
④關于這一點的詳細論述,參見胡亞敏《敘事學》之中的“敘事語法”一節中的第168-186頁。
⑤參見胡亞敏,《西方文論關鍵詞與當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宮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