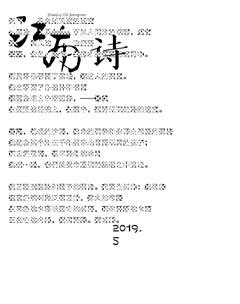只有閱讀使我熱愛生活
西渡
1. 我們不能用定義的網把所有的詩打撈到岸上來。無論多么完美的定義,漏網之魚總是比網中的魚多。詩比我們所有的網遼闊。
2. 在通常情形下,“說”是主動的,“聽”是被動的,在它們之間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權力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滔滔的“說”完全無視“聽”的存在,頂多視為自己的單純容器,其目的則是把“聽”轉化為自身的同義反復。但丁說,“說”比“聽”更富于人性。我的意見正好相反。“聽”首先意味著對他人存在的承認,而在“說”中并不必然包含這種承認。一切人性都是從“聽”出發的。
禱告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說”,它顛覆了“說”和“聽”固有的權力關系,提升了“聽”的地位,把“聽”變成了“說”的出發點和目的地。詩即萌芽于此。
3. 詩是有限對無限的擁抱。詩人們不斷談到詩的神秘。但詩的神秘到底是什么呢?說到底,詩的神秘就源于無限。在詩人的詞典里,無限、永恒是同義語。聞一多在《春江花月夜》里讀出宇宙意識。實際上,這種宇宙意識就是整體或無限對我們的啟示。一首詩如若指示了整體或無限,它便獲得了宇宙的覺識,而世界便在剎那間重新誕生了。
4. 隱喻和象征的區別也就在“宇宙意識”的有無,或者說,能否在有限的語象中指示著無限。
5. 詩反對寓意而擁抱意義。詩以表象吸引我們、愉悅我們。詞語的意義也是詩的表象之一。清陳沆解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以為“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萊宮殿有若夢游,故托天姥以寄意。”更有人以為“天姥山中暗藏一貴妃”,李白筆下“仙之人”就是楊貴妃。這是解夢,不是解詩;在這樣的解讀中,我們得到的是寓意,失去的是詩。古今批評家解詩,多此類。
6. 詩意如水中之魚,不能脫離它的形式——它的水,它的表象——得到合理的理解。我們對意義的渴望——希望獲得某種明確的、概念化的觀念,確實是人類尤其是現代人類不可遏止的欲望之一——卻總是不斷誘惑我們親手去撫弄、把捉那一直陶醉于自身的自由的魚,甚至妄想把它們從河里打撈出來,其結果便是魚的死亡。領悟詩的最好辦法是我們下到水里,與魚一起嬉戲。
7. 詩不是為了表達對世界的意見,但詩人對世界的意見也是詩的表象之一。思想和意見在詩中被形式化,而成為激發詩情的因素之一。
8. 表象和本質的對立,是形式和實踐的對立。詩對讀者只有表象的意義;意義向實踐轉化之時,就是詩向讀者轉身之時。這樣的轉身隨時都在發生。
9. 詞語的意義在詩中總是臨時起意的,它僅僅受制于它的上下文。散文中的意義不僅受制于上下文,也受制于它的歷史語境和歷史積淀。詩是對詞語意義的歷史積淀的爆破。
10. 然而,詩本身就是行動,它悄悄挪動了人性的標尺和底線。在我看來,沒有比這意義更重大的行動。
11. 詩人總是徘徊于詩的真實和現實的真實之間。作為一個詩人,他怡然于文本;作為一個人,他渴望行動。這里的自相矛盾是割裂文本和實踐的結果。實際上,寫作就是實踐,也是改變生活的勇敢的行動。
以上兩條和再上面兩條的矛盾,是我難以解釋,也難以自圓其說的。
12. 有一種詩歌的音樂性是獻給聾子的耳朵的——像貝多芬一樣精通音樂的聾子耳朵。無論多么完美的嗓子也無法傳達這種音樂性內在的豐富、細膩和萬千變化。在這種音樂性的領域內,僅僅一個詞語就包含了豐富的和聲,僅僅一行詩就呈現了豐富的動機。
13. 詩憑著聽力認出世界,散文則是憑著氣味聞出世界。聲音是精神的,氣味則屬于身體。
14. 詩的重要性見于它的復合性,它所喚醒不是某種單一的感官知覺,而是我們的全部身心。詩由此極大地擴展了我們的潛力,并把我們還原為一個完全的人。這一點在一個分析的時代尤顯珍貴。
15. 真正的詩人依靠耳朵判斷詩歌的音樂,而詩律學和不合格的讀者依靠計數。新月派詩人的失敗在于向計數主義的妥協。就此而言,新月派中只有徐志摩沒有完全背棄詩人的直覺。
16. 詩的情感是一種創造,也就是說,不借助詩的形式,此類情感就無以表現自己。即使詩所表現的情感不同于它所起源的情感,但這并不是貶低后者的理由。在詩的寫作中,后者是一團風暴,把各種各樣的形象卷入自身,變成自身的形式。當然,感情也可以是土地,催化孕育萬物,成為自己的表現。
17. 我們稱之為生活的到底是什么呢?它除了是經驗的總和,還可能是別的什么嗎?詩的經驗也是生活的經驗。詩的經驗是一種幻象,生活的經驗最終也是幻象。事實上,幻象正是經驗存在的方式,舍此,經驗還有其他存在方式嗎?所有生活中的事件,當它發生之際,就是它向著幻象轉變之時。經驗正是通過向幻象轉化獲取它存在的意義,這就是那句老話,“只發生一次的事等于沒有發生”。換句話說,詩從來都是現實和幻象的結合,正如經驗也是現實和幻象的融合。詩也許正是保持經驗的現實性的最佳方式。
18. 一個生活中薄情的詩人,卻慣于在詩中表現忠貞的感情,這是否意味著詩是一種謊言?對此,我只想說,詩的情感只要打動我們,就意味著真實。然而,凡經驗都是過程性的,它隨時準備滑向另一種性質相反的經驗。所以,詩的真實、詩的忠貞總是甚于詩人。你要為詩而感動,但要警惕被詩人所欺騙。
19. 生活中的詩人形象常常否定詩中的詩人形象,讓我們對文如其人的信條發生動搖。實際上,詩中的詩人形象是一種“創作”,常常反映著詩人所缺少的一面,這就是文學的補償機制。但是,我寧愿相信詩中的詩人形象正是詩人本來的形象。詩創造詩人,但詩人的野心往往毀掉詩人。
20. 詩人的真摯就是真摯地表達詩。詩既不表達它所由產生的情感狀態,也不表達詩人寫作之際的情感狀態,它只表達詩。
21. 人們在思考詩歌和現實的關系時,總是限于一種二元對立。一些詩人強調詩與現實的對立,聲稱詩與現實毫無關系;某些堅持古典立場的批評家則力圖證明,現實是詩歌唯一的來源,從而必然依附于現實。如果說詩是一種創造,它就不必依附于現實,詩人在現實面前擁有充分的自由和尊嚴。如果說詩是生活的意義,詩也就不是完全獨立的。堅持詩的獨立本身就是對現實的一種態度和干預現實的一種方式。詩的自由在于它對固有意義的不屈從,而不在于它是否與現實發生關系。詩人不必害怕與現實戀愛。詩與現實的婚姻將給詩人帶來一筆不菲的嫁妝。
22. 純詩在我們這里總讓人想起風花雪月。但據瓦萊里的愿意,所謂純詩指的是一種藝術效果,在其中體現了一種與純實踐世界儼然不同的關系世界,其中的每一詞語彷佛都擺脫了其物質屬性,純然指涉自身,而在我們的心靈中引起一種純粹的感動。就其不與純實踐世界相涉之點而言,與這一效果最為接近的是夢。風花雪月本身不能達成這一效果,尤其當它們成為某種特殊情調的固定符號的時候。關鍵是純詩依賴于一種創造的行為,它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感動我們的新的關系,而風花雪月的詩意依賴于一種題材的重復。在這一點上,它與純詩毫無關系。同理,夢的重復也在這一點上顯示了自己的不純。
23. 小詩人比大詩人更純。純的愿望是一種心靈的界限感。
24. 就純粹的程度而言,詩永遠無法與音樂相比,甚至也無法與繪畫相比。語言在其最純粹的時刻,也仍然保留了指涉實踐世界的可能和意向。但恰恰是詩為我們的精神世界中那種最純粹的時刻提供了命名。這一事實難道不發人深省嗎?只有詩激發了我們最全面、最深刻的身心的激動。在詩歌的體驗中,不僅我們的身體,也不僅我們的心靈參與了那種內在的激動,甚至與這一激動格格不入的頭腦也參與并陶醉其中。頭腦或曰理性在詩歌體驗中不僅有其貢獻,而且在這一體驗中實現了奇特的變形——它自身變成了詩歌魔術的一部分。早在戲劇之前,詩歌就已經是一種綜合的藝術,形象、聲音、意義、身體、心靈、理性同時服務于一個目標:從物質向夢幻的變形。
25. 詩永遠是一種間接性的藝術,它首先訴諸我們的理性,而并不直接挑動和刺激我們的感官。當詩人們大談詩的直接性的時候,有必要提醒他們語言符號首先是一種概念。在一首歌中,間接性的歌詞(詩,如果它曾經是詩)被轉變成了直接性的音樂,然而,與此同時,作為詩的一切優越性也就同時失去了。
26. 很容易承認,蜜蜂營巢的行為不同于人的建造行為。因為我們不能說想象參與了蜜蜂的建造行為,反之,在人的建造行為中,想象才是關鍵的。問題是,它們之間也存在某種聯系嗎?顯然有一種深刻的本能引導了蜜蜂的營巢,那么這種本能是否也參與了人的建造行為?在藝術創造中,它也有自己的地位嗎?這些問題的答案也許是肯定的,但這一如此重要的本能迄今還沒有得到研究,甚至連關于它的名字也沒有。所以,藝術的創造到現在還是一樁全憑撞大運的行為。
27.建筑是幾何學的成就,也是物理學的成就,同時也是想象的成就。它是理想和想象孕育的產兒。那么,誰說邏輯是藝術的敵人呢?
28. 偉大的詩也是建筑,有它自己的幾何學和物理學。永遠要占領空間,用詞語的堅實的石料。
29. 一般認為,詩的現代化是一個轉向內心的過程,并把它視為對科學的客體性的反抗。但泰戈爾給了“現代化”另一個定義。他說,“假如現代化有個本質,而那個本質即是非人格的(不受個人感情支配的)”,“不是從個人愛戀感情,而是以永恒的愛戀感情看待世界,這就叫‘現代”,“現代科學是以客觀觀點去分析現實,詩歌也正是以那樣客觀的心情全面地觀察世界,這就是永遠的‘現代”。作為這種“現代”的典范,泰戈爾所舉的例子是中國詩人李白。相反,泰戈爾認為歐洲在科學里得到了那顆“客觀的心”,但在文學里卻沒有得到。以泰戈爾的觀點看,中國當代詩歌所缺乏的正是那種“以永恒的愛戀感情看待世界”的眼光。這部分解釋了“大師”遲遲沒有在我們這里出現的原因。換句話說,我們仍然走在“現代”的歧途上。泰戈爾評論他的時代說,“今天的時代鄙視現實,把毀滅它整個名譽看作自己實踐的主題”。這不正是我們所行的嗎?
30. 自由和格律對于某些詩人都是為了讓寫詩這件事變得容易些。但真正的詩是困難的產物,無論是自由詩還是格律詩。
31. 有唱的詩,有說的詩。唱的詩不一定在音樂性上對說的詩占有優勢。唱的詩試圖以語言模仿純音樂的效果,結果往往連最簡單的(純)音樂也不能達到。說的詩在音樂性上比唱的詩擁有更多的手段,其中最有力的手段是詞的意義。詩歌音樂性的豐富最終取決于意義的豐富。
32. 詩中的經驗是一種韻律學現象。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燈。它講出的不是一個氣象學的事實,而是一個韻律學的事實。八月十五和正月十五是重復,云追月和雪打燈是對仗,云和燈、月和雪是押韻。這個組織原理適用于更大范圍內的詩歌經驗。然而,這種韻律學的經驗并不荒唐,它反映了人類意識和心理深處隱秘的事實。
33. 詩是間接的藝術,它的行進是猶豫的,即使在抒情的時候也帶有反省的意圖;音樂則是直接的,它持續地、不間斷地發生。所以,歌不是詩。詩變成歌,必須通過外科手術把詩中的反省意圖剔除掉,否則它就難以成為第一流的歌——不是因為它缺少了什么,而是因為它多出了什么。實際上,詩歌音樂性只是一個比喻,混同詩歌的音樂性與音樂的音樂曾經給詩帶來災難,卻不曾給音樂帶去任何好處。
34. 一個孤立的形象會變得陳舊,但一首好詩使一個形象不朽。
35. 比喻不是一個事物通向另一個事物的橋梁,而是借助兩個事物的結合而產生第三個事物,并使它們各自獲得對方的特征——這個過程得到了很多幸福的或者不幸的婚姻的證明。詩歌是生殖的藝術。
36. 我夢見我趕火車,我的兄弟在河邊等我,但我必須回到旅館,取回我遺留在那兒的一本書。于是我發動飛翔。路上我又遇到很多的書,怎么也抱不下。只有閱讀使我熱愛生活。
37.將幻想與操作結合起來的想法,是現代詩最重要的發明。成熟時期的戈麥是最嚴格意義上的工程師。因此,他的詩不是個人經驗意義上的抒情詩,而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抒情詩。
38. 《詩經》和《楚辭》分別是中國詩歌的北源和南源。漢詩是北源之干。六朝文和詩是士族南遷以后北源和南源匯流的成果,唐詩則是這一成果的直接受益者。士族南遷改變了士人的生活環境,同時讓士人得以接觸詩學的江南傳統——江南民歌,它顯然是《楚辭》傳統的流亞——由此改變了他們感受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方式,中國詩歌就此幸運地調整了自己的地理學坐標。宋以后,這一坐標又稍稍北轉。詩學上的唐宋之爭,實際上可以視為南北之分的某種變調。但我們所謂南源、北源并非舊詩評中所謂南宗、北宗,那是另一個問題,雖然它與我們所說的問題部分相關。《詩經》是冷峻的現實,《楚辭》是輝煌的夢想;《詩經》是物,《楚辭》是光。可以想象,如果沒有《楚辭》傳統的匯入,中國詩歌傳統將多么單調。羅伯特·勃萊說一個人到四十歲應該走出自我,到青草和樹木中去,到別人中去,進入黑暗,進入宇宙。然而,整個西方文明都要你獻身于強化自我,至死而已。西方當代文學因而是完全產生于自我的文學。基于這一點,他認為,中國古代詩歌是迄今為止最偉大的詩歌。勃萊在某一程度上是對的。中國古代詩歌中最好的部分,在陶淵明、杜甫身上體現最為明顯,確是進入了宇宙的詩歌。
39. 中國古典詩人對于光有特殊的敏感。實際上,古典詩歌的意象都浸透了光,在意象的表面始終閃爍、跳動著光。《西洲曲》《春江花月夜》可為代表,前者的物象表面日光四射(“單衫杏子紅,雙鬢雛鴉色”“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后者的物象表面月光明滅(“滟滟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但古典詩人很少直接寫到光,更少直接表現正午的光。他們偏愛的是晨光、落日之光,尤其偏愛月光。
40. 新詩對舊詩的偏離沿著兩條路線演化:感情→感覺→意識→潛意識→無意識;經驗→虛構的經驗→經驗的虛構→最高虛構。第一條路線的動力是越來越精敏的感覺,第二條路線的動力是越來越自由、越來越無忌的想象。這兩條路線最終在無意識中匯聚。經過這樣的進展,古典詩歌訴諸于常識的感情和經驗,被當代詩歌對無意識領域的掘進所取代。
41. “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這是作者的遺憾;“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月下沉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中稀”,這是讀者的遺憾。作者和讀者似乎很難在同一時空相遇。詩人除了留下作品,還留下了這份遺憾。
42.原創的意象是一個矛盾的概念。意象中的“象”指向外部事物,意象中的“意”指向意義和內涵,也就是說,意象是一個已有明確意指的概念,而不是指某個具體的“象”。首次被使用的“象”只能稱為物象,而不是意象,意象總是已成的、因襲的和繼承的。從意象的這一性質看,它不是一個有效的詩學的概念,而是一個文化心理學的概念。沿用意象來解釋當代詩歌是無效和徒勞的,最典型地表現了批評的無能和缺乏洞見。李心釋說,當代詩歌的創造主要依賴語象的發明,語象是“語言把自身作為對象,通過再度符號化賦予新的意而形成的‘語—象—意符號”。詩歌創造的秘密就在“再度符號化”。詩人們在實踐中對此必有覺悟,否則就無法寫出任何具有當代性的詩。但懂得這一點的批評家屈指可數。
43. 新詩向散文開放是新詩之新的題中之義。在初期白話詩中,散文化曾經是新詩的缺陷,而招致廣泛的指責。然而,到了戴望舒、艾青,詩中的散文成為了新詩的優勢。誰理解這一過程,誰就對新詩的抱負就會有比較切實的理解。
44. 從舊詩到新詩,也是從隱喻的詩到換喻的詩,那意思是從詩向散文推進。但詩中的散文是詩進入散文,而不是散文進入詩。舉例來說,初期白話詩可以說是散文進入詩,卞之琳、艾青的詩是詩進入散文。詩進入散文,是把散文的領地拓展為詩的領地,散文進入詩是把詩的領地拱手出讓。42. 寫作是從永恒消失的時間中拯救出瞬間,以便這一瞬間可以通過閱讀被不斷激活。一首好詩在其內部就制造出這樣的激活機制,使我們可以不斷回到開始。這可以被視為評判詩歌的一條重要標準。也許,它比任何其他標準都更具操作性。神創造時間,作者創造另一種時間。
45. 真正的作者不會把他的同時代人視為競爭對手,他唯一的競爭對手是時間。當一個人從永恒的山巔放眼遠眺時,他的目光自然就越過了那些當代的盆景。
46. 寫一首好詩,在萬紫千紅的詩歌花園里增加一朵無論多么美的花,是無關緊要的。真正詩人的工作是增加花的品種,而不是增加花朵的數量。
47. 身體的智慧是豐饒的,頭腦的智慧是纖薄的。其原因在于,身體包孕了頭腦,頭腦卻無法包孕身體。
48. 感覺比感情更深厚,如果感覺調動了全部的身體。當然,在運氣好的情況下,思想也能調動全部的身體。此時,詩就是宇宙的身體。但是多數寫進詩的思想根本沒有身體。這時候,沒有詩,也沒有思想。
49. 臧棣說,一首《斷章》頂得上半部《啟示錄》,一首《距離的組織》需要十首斯蒂文斯的《冬天的心境》來交換。然而,在我看來,《斷章》仍然是不完美的詩,它太靠近頭腦,而遠離身體。它是頭腦想出來的詩,而不是身體分泌出來的詩,哦,它缺少身體的味道。《距離的組織》雖然也經過了頭腦,但它同時也經過了身體。它還不是身心合一的詩,但幾乎接近了身心合一。《距離的組織》之珍貴在于漢語還沒有像這樣被組織過。
50. 在文青出身的寫作者那里總能聞到一股陳腐的美文氣息,就像文工團出身的男女永遠擺脫不了一種脂粉氣。余光中身上的脂粉氣幾乎是刺鼻的。
51. 人的世界不在詞的一邊,也不在物的一邊,而在兩者之間。人是詞的孩子,也是物的孩子,是詞與物聯姻的產兒。
52. 詩人和詩歌批評家把詩歌的不及物當作詩歌的保留區,但恰恰是這種給予弱勢者的特權剝奪了弱勢者為自己的權利奮斗的權利,從而削弱了他們的生存能力。詩歌的不及物只是表面看來如此。
53. 臧棣說新詩的作者很少能寫出對事物的同情。但海子和戈麥是顯著的例外。不過兩人的情形又不同。海子具有一種童真的眼光,因而把事物看成了人;戈麥則以自己的同情走進了事物的深處,最終把自己變成了事物。在海子和戈麥最后的時期,都有某種癲狂的狀態,海子以他的癲狂傳染了事物,戈麥則是被事物的癲狂所感染。
54. 任何關于詩歌的思考都存在它的反題,這一反題和正題具有同樣的說服力。所以,關于詩的言辭總是自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