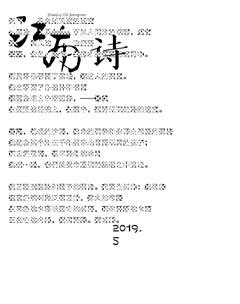1949年,詩人們開始歌唱了
孫昌建
航過這一串黑色的日子
在陽光含笑的國土上
用最人性的歡呼
浮起你金鋼的雕像
——冀汸《唁》
1949年6月1日
杭州《當代日報》
1949年5月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杭州,宣告杭州解放。同年6月1日,《杭州日報》的前身《當代日報》在“新文藝”的副刊上開始發表歡慶杭州解放、歌頌新社會的詩歌,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留下聲名的著名詩人冀汸、阿垅、方然、孫鈿、魯藜、聶紺弩、柳亞子和田間等在這一年都紛紛在杭州亮相,他們有的就生活在杭州,有的是因為杭州文友的約稿而將詩歌發表在杭州,當然版面上出現更多的還是無名的詩歌作者,或者是用了筆名的作者,像杭州詩人阿垅就有數個筆名。70年之后回顧和重讀這些詩作,既是一種紀念,更是為了重新出發。
一、七月派和街頭詩
1949年11月,詩人胡風曾經寫下一首題為《時間開始了》的長詩,宣告了一個劃時代的開始。實際上時間早就開始了,胡風所說的開始是一個時代的開始。今天我們讀一首李白的詩,李白不會覺得奇怪,我也覺得很是尋常,但是今天我們讀一首1949年某位無名氏的詩作,包括閱讀胡風和他的戰友或學生們的詩作,有時突然會覺得很是詫異,并且產生一個疑問:為什么他們會寫出那樣的詩?
這就要從70年前的1949年說起。
1949年的杭州,還沒有《東海》和《西湖》雜志,這兩本文學刊物都是在五十年代創刊的,當然也還沒有后來的《江南》雜志。1949年5月9日,《浙江日報》創刊,創刊號上即有一篇《杭州人民的歡騰》的通訊,它報道了人民解放軍進入杭州城的情形:
五月三日下午一點鐘,“解放軍來了!”“迎接去!”的歡呼聲響遍了杭州市。早寫好的歡迎解放軍的標語、墻頭詩,貼滿了街頭。人們向前望,向前擠,兩輛插青紅色小旗的救護車從人叢中開始去迎接入城的解放軍。數千解放軍行列雄壯,高唱著“解放軍進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歌曲進入了杭州市。當部隊還在錢塘門外,已被歡迎的人群擠得不大好走了……
而且這一天《浙江日報》的創刊號上即有詩歌,其中一首還是著名詩人安娥的,此后的版面上也時常出現詩歌。《杭州日報》當年還沒有創刊,它是從《當代日報》發展而來的,《當代日報》是在1949年6月1日創刊的,當時的副刊有兩個板塊,一個叫“新文藝”,當時是由冀汸在編輯這個版面,不過他的主要身份還是安徽中學的教務長。還有一個版面叫“五月”,后者顯然是為紀念杭州的解放,起初“五月”的刊頭圖是兩個人伸出雙手迎接太陽的剪影,后來改作了斧頭和鐮刀的圖案。
《當代日報》6月1日創刊時,離5月3日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個月,這一天詩人們來了個大亮相,因為巧也是巧,這一天正好是端午節,即中國的詩人節,所以當代日報第三版發了一篇“本報訊”,如下——
今天為農歷五月五日“端午節”,又是中國的“詩人節”,迎著今天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京滬杭地區的偉大勝利,解放后的第一屆“詩人節”,將更有重大意義。詩人,以往被壓制著,簡直沒有歌唱的自由,如今被解放了,廣大的工農快板、秧歌、小調、鼓詞、街頭詩,已流播了全市。秧歌從無線電播唱,街頭詩從學生的壁報上、從報紙的副刊上刊出,像“天上有顆掃帚星,地下有個烏龜精,一心要把內戰起,害得百姓不安寧”,已迅速地流傳在市民們口中。許多工廠里的工人,革命的知識份子,都紛紛在學習寫作快板、街頭詩了。所以今天慶祝“詩人節”的意義特別重大,因為“詩人節”已不是屬文人雅士所專有,而是工農大眾的“詩人節”了。
請注意,如果光是看這一則報道,你是感受不到新中國成立后這第一屆詩人節的特殊含義的。實際上這一則“本報訊”為此后該報的副刊,特別是詩歌定了位導了航,就因為這一句話:“詩人節”已不是屬文人雅士所專有,而是工農大眾的“詩人節”了。言下之意,詩歌不再是文人雅士的專利,它應該就是屬于工農大眾的,寫工農大眾,而且也要由工農大眾來寫,你文人雅人可不可以寫呢,當然也可以,但你得寫我們工農大眾。工農大眾喜歡什么,你就寫什么,這是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精神的主旨所在,即文藝是為什么人服務的問題。
這一天六月一日“五月”副刊版上首先是刊發了杭州本土詩人阿垅的題為《從一首詩看階級性格》的文章,他先是引述了一首叫《貓》的詩,作者馬逢華,原詩非分行排列,為閱讀方便現作分行如下——
我們底大園子空有草色凄迷,
你底蒞止像是碧波千頃中駛來一支 小帆船,
完成畫幅的美,
也為我們載來了歡喜。
有什么東西的飄墜像這樣輕,
軟,落地緩緩?
你的步履是暮春的花朵。
你有大家閨秀的風范。
有時候卻又像淘氣的小姑娘,
你發楞,縐眉,
為了一支蝴蝶底脫逃;
忽然又追繞著自己底尾巴捉迷藏。
注意,為了保留原貌,摘引時還是沿用當年報紙上的寫法,特別是一些譯音字的寫法。
接著阿垅就評論這首詩了:“看起來,就真像一幅美麗的圖畫,就真像一個美麗的世界。看起來,詩人是這樣無邪,這樣柔情,這樣單純,這樣善良,這樣天真,而且,這樣人性。她是,以愛人的赤心在愛小動物,愛著貓啊;人和小動物和平共處,彼此相得,皆大歡喜呢。”
但顯然這不是阿垅的本意,接著阿垅馬上說了:世界是血和火的世界,人是血和肉的人呢。現實并非如此。那么,這樣的人性,——如果這叫做人性的話,不過是“脫離現實,脫離群眾”的東西,即“從觀念出發的,”“超階級的抽象的人性”罷了。
眾所周知,阿垅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詩人,40年代的阿垅是個亦詩亦文的全能型作家,他的古體詩也頗有成就,還寫過南京保衛戰的長篇小說,且一直在發表詩論和詩評,他在1944 年就寫出了“白色花”——
要作一枝白色花,
因為我要這樣宣告,我們無罪,然后 我們凋謝。
同時我們也知道,阿垅是被歸為七月派詩人的,七月派名稱的來由是胡風曾經在1937年9月創辦《七月》雜志并任主編,所以在1955年反“胡風反黨集團”的運動中,包括阿垅在內的一批七月派詩人都鋃鐺入獄,這在此就不展開了,這里要指出的是,杭州曾是七月派的一個重要基地,這個后面會講述到的。
阿垅的意思很明確,或許這首貓詩是一首不錯的詩,特別有點像泰戈爾的風格,但是在那個年代卻是不合適的。我們也知道七月派詩人是特別講究時代性、現實性和戰斗性的,所以阿垅會說:想想吧:蝴蝶在脫逃,而貓在失悔,而人在享樂!蝴蝶在掙扎,而貓在游戲,而人在欣賞!這不是什么博愛,只是一種自私自利罷了。這樣厚此薄彼,這樣有我無你,表面上是溫柔而崇高的,實際上倒很殘酷和虛偽的。——這樣的“人性”,不過是有閑階級底生活性格,表面上異常美好,實際上卻極齷齪,為了粉飾太平,為了歪曲現實。有閑階級者,連“人性”也是可怕和可恥的。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阿垅認為詩歌是要講階級性的,這是時代和現實的需要,而從階級性的標準來看,那一首貓詩就顯然不是好詩了。
同一版還刊登了七月派的另一位詩人方然的文章,題目叫《論新的感覺力》。方然時任杭州安徽中學的校長,曾是個地下工作者,不久就當了杭州文協(市文聯的前身)的秘書長,他在文章中說——
以前,我們所以有那些空洞、叫喊的詩,那是因為有著小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情緒;所以有那些晦澀的、憂郁的詩,那是因為有著小資產階級底說出來是可恥的溫情主義的思想、情緒;所以有那些“黎明”“春天”公式的詩,那是因為有著小資產階級軟弱幻想的思想、情緒;所以有那些七拼八湊的所謂“詩”,那是因為有著小資產階級,小市民底油滑的思想、情緒……
很顯然,作者是要呼吁新的感覺力,他很敏感地提出了下面這個尖銳的問題:“杭州解放還不到一個月,但就在這個短短的日子里,一切生活平面上也不知涌出多少復雜的生活斗爭!我們問一問:在這里面,我們底思想有真實的批判力沒有?我們底情緒有真實的戰斗力沒有?我們展開了思想、情緒底斗爭沒有?有了新鮮的感覺力沒有?”
兩位詩人的兩篇文章,導出了1949年詩人的心聲,即詩歌是要為人民而寫,為時代而寫,為現實而寫。
我曾經看到過一則記述,說阿垅是曾經潛伏在國軍機關里的情報人員,他曾經讓方然傳遞過關于孟良固戰役的情報,因此有標題黨認為,張靈甫之死是跟阿垅的情報直接有關的。不管這個傳聞是否確鑿,但可以肯定,阿垅和方然的這兩篇文章,放在《當代日報》的創刊號上發表,這肯定是有意策劃的結果之一,用今天的話來說也就是把握導向的文章。
詩論是這樣,那么當代日報上的詩作又是怎么樣的呢?這一天是七月派承包了《當代日報》的五月副刊。這一天的阿垅化名“亦門”發表了《街頭詩二首》。第一首叫《保衛文化》,第二首叫《藏不住》。什么叫街頭詩呢,我們就選第一首《保衛文化》——
(一)
反動派
不要文化!
國民黨
沒有文化!
他們
迫害學生
查禁書刊
統制思想!
反動派
摧殘文化!
出賣文化!
還說什么
“五千年文化”
他們把文化
喂狗吃!咦!……
他們把文化
丟在廁所里!嚇!……
他們把文化
踏在鐵蹄之下!轟!
已經變了
炮灰!……
(二)
我們
尊重文化
人民解放軍
擁護文化!
保護
學校
圖書館
博物館
名勝
古跡
體育場
和公共娛樂場所!
我們
需要
精神的食糧,
我們
愛護
歷史的財富;
起來!
為文化而戰!
起來!起來!
保衛文化
保證勝利!
一九四九、五、三
一定要注意它的寫作時間。當一口氣讀完,感覺有點像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詩,但是我們會問,有必要把“學校”“圖書館”“博物館”放在三行而不是一行來說嗎?這莫非就是街頭詩形式上的特點?
同樣是七月派的詩人孫鈿,似乎同樣是街頭詩的形式,他發在同一版上的《漁村小詩》似乎要多了一點藝術性——
捕魚的
人們
都輪班站在崗位上
他們的
手里
拿的不是漁網
拿的
是
實彈的槍
小小的
漁村
一星火光
都不再閃耀了
每個人
都成了
漁網的一個孔
緊密地不能分開
為著
守衛我們自己底土地
同樣道理,“拿的”、“是”、“實彈的槍”完全可以并成一句,為什么要分成三行,特別是這個“是”字也占一行。
但不是所有的七月派詩人在那一歷史時刻都在寫街頭詩,如冀汸在同一版上的《唁》就呈現出了另一種風格——
是這樣堅持了你最初的意志
是這樣建筑了一個輝煌的人格
當生命再不值得保衛了
生命便是你底最后的武器
生命保證勇者底潔白與純真
生命保證堅貞的靈魂底勝利
一個叛徒底信念是一直反叛
到底但永不反任何一次輝煌的死
同志呵
你死得亮麗
你死了
你底希望活著
你底夢想活著
在我們的行程里
你底生命底彩色閃耀著
這大海
這風暴的夜
這燈塔呵
兄弟們記得的——
航過這一串黑色的日子
在陽光含笑的國土上
用最人性的歡呼
浮起你金鋼的雕像
整個風格是低調而沉郁的,跟要表達的意思完全相符,這也是比較符合七月派常見的風格,因為后來我們讀綠原、曾卓等詩,也都感覺有這個特點。
加上后面將要出場的魯藜,我們可以發現,從1949年的6月開始, “七月派”詩人竟同時出現在杭州的一張報紙上,他們中有阿垅、冀汸、方然、魯藜、孫鈿等,他們本來詩風各異,后來卻顯示出了街頭詩的特征。
那么什么是街頭詩?
我理解就是分行的口號,激進的,口語的,或者說詩歌是可以上街的,包括街頭的板報、詩傳單等,因為后來報紙上還專門辟出一個叫“黑板報”的欄目,就是讓大家從那個上面去摘抄文字,用作工廠和學校的黑板報。這說明當時的詩歌主要是起一種鼓動作用,同時也說明以口號入詩是被允許的,雖然后來街頭詩這一形式(包括叫法)漸漸退出了我們的視線,但是在1949年,包括在更早的年代里,我們看到了這一種詩,比如說同樣跟七月派頗有淵源的詩人田間,這是現代文學史上繞不過去的一個詩人,他的詩或者說他的代表作,也具有街頭詩的特點。那么為什么會出現街頭詩,街頭詩又是從哪里來的呢,我們要尋根溯源。
《新文學史料》曾刊登田間的自述,那上面也曾說到街頭詩:“它是一種短小通俗、帶有鼓動性的韻律語言。它一經誕生,與人民群眾相結合,便似乎有了翅膀,可以飛了,它飛往戰地,它飛往敵后,它飛往戰士的心里。” 田間還認為街頭詩跟墻頭畫是一個意思,
著名作家阿英的兒子錢毅說:街頭詩是介于民謠和新詩之間的形式。它大部分吸收了民謠風格,同時又接近新詩。它比新詩更簡潔,好似粗筆畫,幾筆就能說出一個意思,群眾更容易接受。
街頭詩好似粗筆畫,這個說法很形象,也很能說明問題。
錢毅還說;街頭詩就是符合某種特寫形式并書寫在街頭上的短小的政治抒情詩……第一,不超過十行的短小篇幅;第二,參差錯落的句式和排列;第三,基本上不押韻腳;第四,凝練精警的語言表達。
那么為什么會有街頭詩這種形式呢,我們都知道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文學革命,這就包括新詩革命,即用白話詩代替格律體,胡適周作人們就作了嘗試,但五四初期包括二三十年代都沒見這種街頭詩,雖然那時的詩也提倡白話。
據學者劉冬平在《解放區前期詩歌研究》(1936-194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12月版)一書中說,解放區的讀者百分之九十九是文盲,他們只知道口口相傳的民歌和民謠,因此產生了街頭詩。前期由田間、史輪、林山、邵子南、柯仲平等詩人為主,還是具有詩的要素的,后來詩的要素逐漸減少,對時事的一種敏感、及時的快速反應,使街頭詩終于變成了分行而寫的標語口號詩。
即同樣是街頭詩,一開始是文人詩人所寫,后來就成了大眾的順口溜。
而且那個時期,解放區還曾出現過《街頭詩運動宣言》,宣言說到“在今天,因為抗戰的需要,同時因為大城市已失去好幾個,印刷、紙張更困難了,我們展開這一大眾街頭詩歌(包括墻頭詩)的運動,不用說,目的不但在利用詩歌作戰斗的武器,,同時也就是要使詩歌真正走到大眾化的道路上去……”
由此看,街頭詩產生的條件還有缺紙張少印刷的情況,所以一度也是靠口口相傳了,這又跟民歌近似了。
從解放區的前期,到1949年的五六月,怪不得阿垅和孫鈿都會寫作街頭詩,包括后面將要亮相的詩人們,特別是田間,這一年發在《當代日報》上就有三首詩,且都是街頭詩一類的風格。這說明什么呢,說明詩人一直在考慮詩歌的讀者,一直在想積極地反映重大主題,這也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所強調的。所以在杭州的一張地方性報紙上,可以看出當年街頭詩的一個端倪,雖然1949年過去之后,這一種詩歌的形式漸漸少了起來,但后來又起來了民歌體等。
二、頌歌領袖
也可能真的是受胡風的影響,在1949年詩人們的大合唱中,有一聲部就是唱給毛澤東的,在這一年的11月,胡風寫了一首長詩,題目叫《時間開始了》,開頭一段即是——
毛澤東
他站到了主席臺底正中間
他站在飄著四面紅旗的地球面底
中國地形正前面
他屹立著象一尊塑像……
這馬上讓我想起前面引述過的冀汸的詩句:“用最人性的歡呼/浮起你金鋼的雕像”。
毫無疑問,在當年這么多歌頌毛澤東的詩作中,胡風的這一首當屬力作。關鍵是他的題目又是那么巧妙,他似乎想昭示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但如果從寫作的時間上來看,其他詩人寫作歌頌毛澤東的詩則要早于胡風的這一首長詩。
比如在6月2日的副刊上,詩人聶紺弩一連用了十二個比喻,寫下他心目中的毛澤東。
南社的老詩人柳亞子當然不甘落后,6月5日他以一首《滿地紅》來寫他心中的毛澤東——
太陽出來滿地紅
我們有個毛澤東
人民受苦三千年
今日翻身樂無窮
當時報紙上出現歌頌毛澤東主席的詩歌,也是有歷史背景的,新中國成立前夕,先是成立了人民新政協,這在七月一日就召開了大會,會上毛澤東發表了重要講話,且這個講話是被要求要收聽的。《當代日報》6月20日載有這樣一則通知或者說叫簡訊:“今(廿)日下午七時至八時十分,北平新華廣播電臺廣播毛主席在本月十五日新政協會議上之演說錄音片,各地新華電臺及人民電臺一律轉播,希各地人民按時收聽。”
后來生活在天津的詩人魯藜在當代日報7月6日發表了《聽毛主席在新政協籌備會講話的廣播》一首,寫下了他聽對毛主席聲音的一種感受——
他的聲音從北平廣播出
傳到我們這里
傳到千里萬里
傳到高山,傳到海洋
傳到鄉村,傳到城鎮
傳到東方,傳到西方
就是他的聲音
就是他的聲音
跟陽光一樣
傳到全世界
和空氣一樣普及
…………
同樣是寫毛澤東,當時不少的詩歌中出現了較多的敘事的元素,比如這一首發表在8月13日的《我們去看毛主席》(作者戈金),他的一開頭上來就是敘事——
“明天去看毛主席!”
這消息傳出,我們都狂歡起來,
我一夜沒有睡好……
翌日,
我們乘汽車出發,
汽車在平坦的路上飛馳,
我的心急的比飛還快,
恨不能馬上到毛主席面前。
…………
而到了后面,抒情性就增強了,也是那種之后最常見的方式——
迎著雷動的歡呼,鼓掌,
毛主席出現了!
我們蹺起腳,仰起頭,
舞動手臂高呼,
“毛主席萬歲!”
他雄偉的身軀,
放射著光輝。
他出現在我們面前
就像劈開烏云,
照耀大地的燦爛的太陽。
他微笑著,慈祥,滿意的望著我們。
我們高聲歡呼呵!
他向我們年青的中間走過來,
和我們熱烈的握手,
我們大伙擁抱了他。
我把手伸給毛主席,
他龐大的手,緊緊的握著我的手,
我混身的血沸騰起來,
面孔感到在燃燒,
有一個無可比擬的力量
通過我的全身。
我注視著
這世界的巨人
他慈祥、微笑的面孔,
他閃爍著光榮的面孔。
…………
因為敘事有描摹場景的功能,同時又有表現人物心理的作用,這就不是簡單地比喻和排比,不只是街頭詩一種形式,這是一種歌頌的升級版,而且我們要注意的是,這些詩歌都是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完成的,就像詩中出現的“毛主席萬歲”一句也是在開國大典之前。在這之后,這一類詩反而少了起來,我只在12月3日見到了一首田間的詩《跟毛主席走》,眾所周知田間在當年憑《給戰斗者》已經成名,被聞一多稱之為“擂鼓詩人”。
擁護蘇聯的人,
跟毛主席走;
走到蘇聯一邊,
和朋友走一路。
他好比是大海,
我們好比是船,
船在海上流,
大海決不要報酬;
只要船開到海上,
大海和船同到海邊去!
田間應該是口語詩的鼻祖了,這一首詩的不同之處在于這一句:“當大海決不要報酬”,說不上有多少好,但很奇怪他能想到這樣的詩句。
另外我們要注意的是,其實在1949年,在歌頌領袖的詩作中,也并沒有把所有的聚光點都集中毛澤東一個人身上,即其他的領導人也有寫到的,我就注意到在12月16日有一首作者荊玉寫劉伯承的——
劉伯承走到新華書店
街上,揚起了塵煙,
十輪卡停到門前,
幾個解放軍,
下車,看過了招牌,
走進新華書店。(冀魯豫)
同志們迎接到屋里,
斟來茶,拿來香煙,
那個戴眼鏡的說:
“緊著趕路哩、
快預備一點飯!”
同志們,端上炒白菜,
窩窩頭和白湯面,
他們有味地吃喝,
吃完了,付給幾張米票。
一個年青的同志發了怔,
看到那個戴眼鏡的,
好似司令員劉伯承,
同志們偎過來問,
他點了點頭就走。
汽笛鳴叫一聲,
十輪卡開出了朝城,
同志們后悔又歡喜,
沒預備好酒菜,
想不到來了劉司令!
這里比較有意思的是,劉伯承走到新華書店,并不是來看書或買書的,而是匆匆地吃了一口飯馬上就趕路了,所以是特別注明那店是在“冀魯豫”的。其實這樣的詩很難寫,或者本身也不構成詩的要素,但這樣的詩寫出來竟也別具一格。
當年寫毛澤東的詩,杭州這樣一個城市,僅一張報紙上,在這七個月中就有這么一些有代表性的,之所以要談論這個問題,就是要注意時代背景。
事實上謳歌毛澤東的詩,也不是1949年一下子噴涌了出來,據臧克家編的《中國新詩選(1919-1949)》(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就收了詩人蕭三在1945年寫作的《送毛主席飛重慶》,詩中有這樣的句子——
人民感謝他救民于水火的精誠。
人民信任他的大智,大勇,大仁。
人民衷心地祝福他康健!
人民用自己的力量維護他的安全!
這是可以跟方紀的散文《揮手之間》對照起來閱讀的。這詩中的“精誠”、“大智”、“大勇”和“大仁”等,皆是民國時的習慣用法,并沒有注入紅色的元素。而在張志民的長詩《死不著》中有一首叫作《告訴毛主席》,寫作時間是1947年,修改于1953年。
田間在1949年的12月還寫了《遠望莫斯科城——為斯大林七十大壽而作》,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世界上千萬個城鎮,
都住著斯大林。
斯大林的心上,
也住著千萬勞動人。
所以當年的歌頌領袖,還不只是歌頌毛澤東,像郭沫若后來也寫過關于列寧的詩。
臧克家《中國新詩選》前言者說,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解決了文藝上的許多原則性的問題,詩人們從中得到了教育,這不但表現在深入群眾斗爭的生活實踐上,也表現在藝術創作的形式上。為了創造人民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的詩歌,許多詩人承繼了民歌的優秀傳統,寫出了新鮮活潑的民歌體的新詩來,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和阮章競的《漳河水》。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這對詩人來說,就面臨著要如何深入熱火朝天的斗爭生活,如何徹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情感,唱出對新中國的偉大現實的動人的頌歌來。
除了歌頌毛澤東,這一年要歌頌的還有很多。一個十七歲的小學徒梁天壽以《解放軍》為題寫下了一首詩(6月11日)“五月三日天氣晴/解放大軍進入杭州城”,這位小學徒對解放軍用上了最為樸素的比喻:“你好比救苦救難觀世音”。注意之前聶紺弩也用過 “老太婆的觀世音”這樣的比喻,這說明為了通俗易懂,詩人們或者說編輯們是要先要遷就一下百姓的審美觀和接受能力的,要是放在今天,這樣的比喻用在領袖或解放軍身上是會被認為是不準確的。
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從《當代日報》的副刊可以看出,以1949年下半年為例,出現了一批歌頌毛澤東、歌頌新社會、歌頌解放軍的詩歌,而且由此也相對集中出現一些貫穿了我們幾十年詞語,如太陽、紅、北京、天安門、紅旗、東風、北斗、明燈、青松等,即初步形成了一些抒情詩或叫政治抒情詩的固定詞語。這可以說一直延續了70年,特別是遇到重大節慶時,這些固定詞語又會被喚醒,當然是經過了重新的排列組合,后來還出現了一些固定的句式,如“我驕傲,我是……”等。
三、記錄歷史的時刻
1949年的詩人,更多地也還在尋找新的象征和比喻,至少在六月和七月是這樣的,即那種文人氣息的詩還是蠻多的,只是說《當代日報》“五月”副刊從八月份開始,似乎風格有所改變,即更鄉更土更像順口溜了。但是在這之前,還是有一些讓人耳目一新的詩作的,雖然也是在歌頌,但在表現手法上還是頗有新意的,像這一首金津的《新人類的頌歌》(6月29日),它一開頭是這樣的——
有太陽的日子
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新鮮的早晨
像蘋果一樣漸漸紅熟
沒有太陽的日子
亮麗的紅旗
就是我們的太陽了
在這里沒有完全用大詞,而是用了形象,用了蘋果和紅旗來喻太陽。
在1949年,從一張杭州的報紙上可以看出,更多的聲音是歡快的,是樸素的,是來自鄉村和田野的,有一個作者用上了“田多野”的筆名,他用獨特的鄉土氣息唱出了“蛙”的聲音(6月10日)——
春天
蛙第一個醒來
咯咯咯——
它撥出了
比機槍還響亮的聲音
告訴那些租戶們:
今年,你下的種子
收獲的也是你自己的了
之前我們只知道春江水暖鴨先知,但這一首是蛙先知,而且又切合現實,寫出了租戶們的希望,“比機槍還響亮的聲音”又分明帶著戰爭的硝煙。
在這里我還注意到,《當代日報》的前身《當代晚報》,幾乎是不發詩歌的,而一旦人民解放軍接管杭州、新的政權誕生之后,這新創辦的《當代日報》就把詩歌當作副刊的主要武器,這也意味著詩歌最適宜于擔任歌頌的使命,從全國范圍看,那一個時期像何其芳、袁水拍這樣的詩人都一改詩風唱起了頌歌。
這一年的詩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即它對場面的鋪敘非常之多,因為更多的詩歌是從人群中誕生的,是隨著人群的潮流而前行的,這就像舉世聞名的錢塘潮一樣。七月初杭州有一場十萬人的大游行,那是為了慶祝全國新政協會議的舉行,于是叫一名叫“歸家”的作者寫出了《游行》一詩(7月13日)——
在毛主席肖像的后面
從紅旗下
走出了廣大的人民隊伍
有精神飽滿的解放軍
有各式各樣的工人
有誠樸的農夫
有公務員新聞記者
有最起勁的學生
有白發斑斑的老翁
我滿臉皺紋的老媽
有年青的小伙子
有健康的大姑娘
有七八歲的小孩子
一群善良的人群
…………
這些走著走著的人群,不僅走過了杭州的街頭,也走過了天安門城樓,走在歷史的結點上,走在1949年杭州的大街上,一位叫徐冰若的詩人就干脆寫下《十月二日,我走在街上》,他記錄了歷史的時刻,因為杭州慶祝開國大典的游行是在10月2日舉行的,我節選其中三節——
十月二日
一個全中國的好日子
我走在街上
…………
牌樓搭起在每一條大街
紅旗掛滿在每一家門上
人們的臉上洗去了幾千年的憂慮
笑容堆滿在每一個人的臉上
…………
十月二日
我走在街上
是一個全中國的好日子呵
我看到全杭州的人在盡情的唱歌!
我看到全杭州的人在盡情的歡笑!
“全杭州的人在盡情的歡笑”,這就寫出了一種氣氛,更是一種時代的印記。由此可以看出,1949年的杭州,已經儼然是一座詩歌之城,有的自覺用民族形式,嘗試著寫出一批鄉土氣息重、表現新舊變化的詩歌,而且都有著較強的敘事性,這有點類似于《王貴與李香香》的風格。
四、童謠現象
但是如果一定要從抒情性和藝術性上來說,從當代日報1949年6月到來12月這7個月的詩歌來看,反而是童謠給人留有較深的印象,因為它有對傳統童謠的傳承和創新,等于是用了童謠的基本元素,然后加進了“新社會”的內容,因此它首先還是謠,雖然是多少有點成人化的謠了,那是宣傳和時代的需要,但總體看風格還是統一的,并不讓人突兀,比如周文的《童謠四首》(8月16日)的第一首《天上一顆星》——
天上一顆星,
地下一個釘。
釘鈴鈴,掛油瓶;
油瓶油,炒炒豆;
炒豆香,加辣醬;
辣醬辣,掛水獺;
水獺尾巴長,
…………
到此基本是襲用傳統詞句,那后面就是新的了——
送給老鐵匠;
鐵匠整天打鐵忙,
釘釘釘!當當當!
打把鋤頭送哥哥,
加緊耕作支前方。
打把剪刀送大姐,
大姐做起一雙布鞋子:
鞋子送給解放軍,
解放軍,
穿了鞋子去打蔣匪幫;
鞋子穿呀破,
匪幫消滅光。
這里有兩點分寸掌握得較她,一是打鐵并沒有說打出一把槍來,第二做的鞋子也是要穿破的。
第二首《燕子燕》也是這樣——
燕子燕,飛過天;
天門關,飛過山;
山頭白,飛過麥;
麥頭搖,飛過橋。
以下則是新的內容了——
橋上姐姐迎新婦。
橋下弟弟妹妹敲鑼鼓;
鑼聲當當當!
大家擁護共產黨。
鼓聲咚咚咚!
人民心愛毛澤東。
9月18日署名躬耕的童謠《紅鳳仙》也是這種寫法——
紅鳳仙,
白鳳仙,
親娘教我做針線。
先砌底,
后上圈,
做雙鞋子厚甸甸,
送給解放同志陸阿全。
陸阿全,
穿了新鞋上前線,
翻山越嶺快又便。
打得匪軍沒處逃,
哇啦啦,
叫黃天。
黃天叫不應,
只問你匪軍為何反人民?
除了童謠之外,還可以見到一些被稱之為民謠的詩,但因為民謠沒有一個相對統一的模式,特別是在江南地區,所以特點并不明顯。9月19日,發表了因奇、朱觀興的兩首詩,冠之以“農村小唱”的標題,其中一首《做豆腐》是這樣的——
做豆腐,真辛苦,
半夜三更磨豆漿,
天亮還要賣豆腐;
豆腐價錢賤,
錢也賺不多,
不夠買柴和買米,
忙得半夜沒困熟。
做豆腐,真辛苦,
做的非但沒吃腐,
有時還沒飯落肚,
買主還嫌豆腐壞,
又要“便宜”又要秤得“多”。
啞子吃黃蓮,
有誰明白我做豆腐的苦?
至于當時的報紙上為什么要發這么多童謠,我想可能還是跟街頭詩的功能是一樣的吧,主要還是為了宣傳和普及,但因為童謠尚有基礎,所以在這基礎之上再來注入新社會的新內容,似乎還能看到一種傳承,新詩有傳承,這才有詩意。
五、標語口號、兩行詩及國際元素
勿庸諱言,1949年的不少詩歌,標語和口號是常見的,因為之前提到過像阿垅這樣優秀的詩人也在寫街頭詩的,所以這個就一點也不奇怪的,比如有一首叫《上海六大任務》(8月23日),作者丁當,這完全是當作任務來鋪陳了——
(一)
支援大軍南下
解放臺灣福建
對美蔣的封鎖
這是最好答案
(二)
實行疏散人員
學校工廠內遷
人力財力齊下鄉
加緊從事生產
(三)
生產方針改變
企業組織精簡
認真做到合理化
工業大大發展
(四)
進行土地改革
改造鄉村政權
工人學生和黨員
全心全力去辦
(五)
城鄉物資交流
內地交通發展
帝匪封鎖新陰謀
立刻宣布完蛋
(六)
反對奢侈浮華
大家埋首苦干
打敗了一切困難
新的上海出現
8月27日有蔡中岳的《剿匪反霸》——
政府動員把匪剿,
咱們應負起責任立功勞。
軍隊前面打殲滅戰,
咱們帶路送情報。
只有軍民聯合的緊,
保管土匪無路跑。
…………
9月16日有傅清冰的《群眾力量》——
群眾力量大,
暴力全不怕;
趕快組織起,
剿匪和反霸。
是誰造謠來破壞,
是誰搶走了咱的牛馬?
是誰把他的兒子填死坑?
是誰把我們踩在腳底下?
特務造謠來破壞!
土匪搶去了咱的牛馬!
保長把他的兒子填死坑!
惡霸把我們踩在腳底下!
群眾力量大,
暴力全不怕;
要想得翻身!
剿匪除惡霸!
這一切當然都是為了配合運動而作宣傳的,但是不是都用詩歌來配合宣傳,這就屬于一個問題了。不過同樣是宣傳,也有一些詩寫得還是比較有意趣,即我們所說的是有詩意的,我注意到一個叫丁予的作者有兩首詩,一首是刊發于8月4日的《手榴彈和可可》,這個題目就很怪,因為要把這兩者扯在一起寫一首詩是很難的,請看——
玉蜀黍
嘩啦啦響在溪邊的山頭上……
好天氣呵!
又是一次新戰斗的開始
我到后勤站去領手榴彈
一間剛搭起來的草棚
毛竹編成的墻壁還
散發新鮮的氣味
墻角放著
新繳來的七九步槍
一個年輕的廣東同志也從山下爬上 來了
他也是
來領手榴彈的
但不知道從那里
搞來了一罐可可
我們圍著坐下來
沖可可吃
一個梳辮子的女同志
從一只裝藥水的棕色大瓶子里
替我們加上
大塊大塊的白糖
好香好甜呵!
我們喝著噴熱的可可
梳辮子的女同志
弄好了兩付新的榴彈袋
我們背上去
粗黑而發亮的手榴彈
沉甸地掛在胸前
立刻
我們就要趕十幾里山路
回到隊伍里去了哩!
為了
這一段短促而珍貴的時間
我們又坐下來
喝著噴熱的可可
好香,好甜呵!
(四九、三、浙東)
這是很有畫面感的一首詩,如果能用炮彈的殼做杯子喝可可,畫面感可能會更強。
另一首是刊發于9月9日的《雨》,雨當然是詩歌的好朋友,但是這一首1949年的雨,顯然是帶著年代特征的——
悶熱的下午天
農民帶著憂愁的面孔
坐在
鄉臨時工作委員會的辦公室
“天不下雨
怎么辦呢?”
工作同志
苦笑地搖搖頭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
一個瘦長的農民
發出憂郁的嘆息
“如果能叫天下雨
就好了”
突然聲音
一個聲音
爆炸了
“革命成功后
一定有辦法”
說話的是
一個粗黑的漢子
好涼快呀!
心里
下雨了
由此可以看出,這個丁予是個高手,這丁予可能也是個筆名。
1949年,除了創刊號上發表了方然和阿垅關于詩歌的評論性文字之外,后面半年中幾乎是只發詩作不發評論的,但有一篇紀初陽的《詩的民間形式》值得關注,此文說“最近在讀到的一部分詩歌作品里,就形式講兩行兩行的詩很不在少數。我想:把詩寫成兩行兩行的樣式,如果不是故意,或抱著某一種單純的“迎合”心理,是可以的。因為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就是利用了陜北民間的順天游(也稱信天游,筆者注)這一曲調在毛主席文藝思想、方針指導下由實踐而獲得成果之一。”
文章中提到了當時的一個背景,即陸定一同志撰文表揚了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于是乎大家都學這二行體了,而作者認為“民間的形式是很多的,并不止于‘順天游一種,且它大半帶有著地方性,因此,我們如想運用舊形式也不該只止于這一類,尤其是不應當死板的專在這兩行兩行上做形式的追求,使詩失掉了生動活潑而走向定型的栲枷,這傾向是反現實的。事實上從當前工農兵自己的詩創作中來看也并不都是那么兩行兩行,或那么均齊,對稱和程式化的。”
實際上《當代日報》上的兩行體反而是很少見的,6月4日發表過一首圣野的《吉佩佩訴苦》(快板),“快板”是特別注明的,他開頭八句是這樣的——
佩佩同志出身好
從小和窮人住一道
爸爸給鬼子捉得去
活活燙死一根紅鐵條
佩佩為了養母弟
拼死去把單幫跑
后來總算托別人
進了工廠把身靠
圣野后來以兒童詩而著稱于世,但在當年也是鄉土派的。9月13日又發表了阮中一的《剿匪肅特》(孟姜女調),注意這個“孟姜女調”也是特別注明的:
蔣匪幫來壞良心,
造謠破壞又搶劫,
政府為了保人民,
矛頭所指傳勝利,
特務土匪莫糊涂,
要得今后有出路,
…………
綜上所述,1949年的詩歌,僅以當代日報副刊為例,歌頌毛澤東,歌頌解放軍,抒寫正在進行著的種種變化,尤其是解放區和農村的一些變化,但它很少直接寫城市,因此在這一年的詩作中幾乎沒有見到寫西湖、寫湖濱的。這一年到了十月份之后,另一塊內容則開始出現了,即寫蘇聯的十月革命,寫斯大林的詩歌多起來了,而總的傾向是贊蘇批美,后來人們所說的“詩和遠方”變成了詩寫遠方,像前面提到的魯藜就專門有一首《我們歡迎你,法捷耶夫同志》(10月11日),法捷耶夫是蘇聯作家,著有《毀滅》、《青年近衛軍》等作品,當時是一紙風化的。詩人開頭一段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