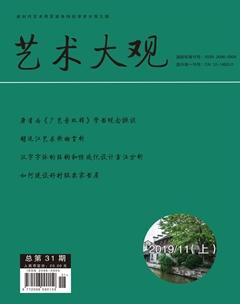山東傳統(tǒng)民俗民間舞蹈“加古通”的儀式文化
張佳益
摘要:山東傳統(tǒng)民間舞蹈與農(nóng)耕文化息息相關(guān),就其民間文化的本質(zhì)來看,大致蘊含了三大主要特性,即“鄉(xiāng)土性”“祭祀性”“自娛性”。人們以其形性推及神之形性,而舞蹈則在儀式的過程中扮演著娛神的重要角色。山東傳統(tǒng)民間舞蹈“加古通”集“鄉(xiāng)土性”“祭祀性”“自娛性”三種特性于一身,本文著重討論并分析舞蹈“加古通”在古時祈雨行為中的文化體現(xiàn)。
關(guān)鍵詞:傳統(tǒng);民間舞蹈;祈雨儀式;文化
“加古通”作為一種從古代傳習(xí)至今的民間藝術(shù)形式,具有豐富的社會文化內(nèi)涵,而這種藝術(shù)行為是從中國古代的祈雨儀式中發(fā)展而來。人們曾以打“加古通”為手段進行祀神祈雨之事,它被作為一種具有指稱、意味、記憶等功能的象征性符號得以呈現(xiàn)。舞蹈作為一種用身體傳達文化、表達情感與思想的藝術(shù)形式,交織于物質(zhì)與精神之中,具有語言文字與非語言文字兩種文化特性。倘若將其置于某一特定的文化環(huán)境或語境中,它便由某種思想觀念,某種情境或情節(jié)所賦予一定的含義,而這種特定的舞蹈形式便成為一種以動作來表情達意的符號象征物。正如社會學(xué)家馬克斯·韋伯所言:“人是懸掛在由他們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wǎng)上的動物。”而人類就是“意義的創(chuàng)造者”。
一、“宋柳溝村”祈雨儀式的構(gòu)成
儀式是一種古老又普遍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它不同于人類日常的行為活動,而是被人類所賦予意義的一種特定的、超常態(tài)的行為模式。這套行為模式由觀念所引導(dǎo),旨在實現(xiàn)某種實際效應(yīng)為目的。“祈雨”作為一種祭祀性儀式,由一系列的象征符號所構(gòu)成,如儀式化的姿態(tài)、行為、動作,以及行為者所表現(xiàn)出的情態(tài)、心態(tài)等特征。查爾斯·皮爾森將人類的文化符號分為了三種類型:“類像”(icon)、“標志”(index)和“象征”(symbol)。儀式中的符號一般是由象征符號所表現(xiàn),因為象征符號具有規(guī)約性原則,它與符號所指的意義之間沒有直觀和本質(zhì)的聯(lián)系,而是依靠事先的約定而代表某種事物的特性。所以“‘象征符號的形式和符號意義之間的關(guān)系只存在于儀式當事人及其特定社會群體約定俗稱的‘文化代碼(cultural coda)中。”正如宋柳溝村古時在天旱時舉行的祈雨儀式一樣,人們遵循著一定規(guī)律的行徑,來完成一場完整的祈雨行為。他們先從廟內(nèi)進行“安壇”,請道士念經(jīng)文,各家各戶要插柳條,寫“龍王牌”,成人一天“跪壇”三次,這個時間一般要為期五天。到第六天,便開始組織祈雨隊伍,到二十里外馬家橋八大泉的觀音廟中去祭菩薩,進行取水活動。在取水的過程中,隊伍的前面要以鑼鼓隊領(lǐng)頭,吹羊角號,鑼鼓隊后面有一個人手握“凈瓶”,作“取水”之用,接著有十幾個人頭戴柳條帽圈,手持長條形的五色彩旗,成雙排行進,之后緊跟著兩名身背銅牌,手扶青紅棍的“開路鬼神”,此后是大紅竿支轎抬著孫大圣的塑像,轎前有“加古通”即“打長板”的舞隊在喧天的鑼鼓聲中邊行進邊表演,而轎后則是盛大的鑾駕隊跟隨。鑾駕隊共由八人組成,其中四男分別手持金瓜、鉞斧、天鐙、華蓋;而四女則依次手持掌扇、提爐、符節(jié)、宮燈。再往后由人們抬著一對“望天犼”,并以鑼鼓隊壓陣,浩浩蕩蕩地行進。這是一項具有特定流程的祈雨儀式,村民們通過各種與目的性(祈雨)相關(guān)的象征符號有規(guī)律的整合成了一套在特定時間、特定環(huán)境中的儀式行為,而這種指向性的行為則通過思維觀念的引導(dǎo)產(chǎn)生一定的目的效應(yīng),這種效應(yīng)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正是人們所愿意進行儀式活動的動機。
二、“加古通”祈雨儀式中的虛擬情境
“加古通”即“打長板”,作為宋柳溝村祈雨儀式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本身就被賦予了“祈雨”的情境內(nèi)涵——對神秘世界的虛擬。既然儀式的主要行為是在虛擬場景下進行的虛擬表演,那么作為儀式的表演者來說,他們將自己置身于這種虛擬的環(huán)境中,從而真正的進行體驗和感受環(huán)境所帶來的氛圍。格爾茲認為,就宗教活動而言,儀式就是一種“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它引發(fā)了兩種不同種類的習(xí)性,即“情緒”和“動機”。“動機由于目的而‘被賦予意義,而情緒則由于情境而‘被賦予意義。”這說明儀式參與者通過自身的需要而產(chǎn)生動機,由動機促成行為方式,即意向情境,最后經(jīng)過身臨其境的體驗而得以感動,并完成一系列指向性行為,以達到他們的某種目的性效應(yīng),而這些都取決于一種強大的思維觀念,即“神靈信仰”。所以,就“加古通”而言,一種為取悅神靈而產(chǎn)生的“以舞祈雨”的形式,從它發(fā)生就注定被籠罩在了“神靈信仰”的思維觀念之中,也被帶入了一種“虛擬性”的祈雨情境之內(nèi)。下面將從三個方面來解析舞蹈“加古通”在“祈雨”語境下所蘊含的虛擬性特征。
第一,從“加古通”文本情境的虛擬性來看,它暗含了“祈雨”這個整體事項的訴說與表達。首先,從主體(人)的心理發(fā)生——“盼雨”的心境開始(動機),將“加古通”的表演者置身于“盼雨”的情境之中,以抒發(fā)人們渴望下雨的“情緒”;其次,用“踩鏊子”的具體行為,作為達成祈雨的目的手段,人們設(shè)置了用“火”燒紅“鏊子”的虛擬情境,通過表演者具體可被感知的動作形態(tài)以及情態(tài)和心態(tài),試圖營造出某種“真實”的環(huán)境氛圍,來親身感受與體驗踩“熱鏊子”的虛擬效果,用以增強急切盼雨的情感性表達;最后,人們利用“踩鏊子”的祈雨行為實現(xiàn)了“降雨”應(yīng)有的成效,至此激發(fā)出“官民同樂”的情感表達。總體來說,從“加古通”的內(nèi)容結(jié)構(gòu)來看,“盼雨”與“官民同樂”這兩部分,都屬于主體在該事件中的心理結(jié)構(gòu),而中間“踩鏊子”部分,則是如何進行祈雨的具體性手段。人們通過“盼雨”的心境(動機)而產(chǎn)生“踩鏊子”的行為(祈雨手段),并借助“踩鏊子”的行為來實現(xiàn)“降雨”之目的,最后以共同的“情緒”宣泄而告終。所以對于“加古通”的文本情境而言,雖具備了一定的關(guān)于“祈雨”事件的敘事性,但最終所尋求的不過是一種強調(diào)“祈雨”情感的抒情性表達而已。
第二,體現(xiàn)在“加古通”表演環(huán)境的虛擬性方面,就整體環(huán)境來說,它處于一種祈雨環(huán)境的氛圍之中,而就其本身的環(huán)境設(shè)置來看,它的祈雨內(nèi)涵的顯現(xiàn)則是由“踩鏊子”的舞蹈形式與音樂伴奏的氛圍共同烘托。縣官“踩鏊子”是舞蹈“加古通”里最重要的構(gòu)成環(huán)節(jié),人們以“火”燒紅了“鏊子”這一物體,使其承載了祈雨的基礎(chǔ)性內(nèi)涵,而這種祈雨內(nèi)涵是由表演者通過“想象”踩到鏊子上的“情境”再經(jīng)其形象生動的表演而得以塑形的。當然,“踩鏊子”這一舞蹈形式本身就是“虛擬性”的,人們通過想象設(shè)定了“踩鏊子”的情境,借由這種“自虐式”的或“理所應(yīng)當”的乞求方式來誘導(dǎo)神靈的關(guān)注,迫使神靈產(chǎn)生同情悲憫之心,或是一種愧疚之情,從而得以心安理得的實現(xiàn)“降雨”的成效。另一方面,是“儀式音樂”的環(huán)境效果。“加古通”作為祈雨儀式中的舞蹈形式,它的祈雨成效離不開音樂伴奏的氛圍營造。為了使“引子”踩鏊子的舉動更加生動,人們以鑼鼓等打擊樂器為基礎(chǔ)的伴奏形式,營造電閃雷鳴的效果從而強化祈雨情境的“真實性”。“雷電”意味著生命之動能,經(jīng)陰陽摩擦后形成氣流,促成風(fēng)雨潤之以萬物,而雷聲出現(xiàn)后一般也會伴隨著大雨的出現(xiàn),所以中國古代對于雷神的崇拜非常普遍。正因為雷電之聲與鑼鼓之聲相似,所以每當遭逢旱災(zāi)之時,人們便遵照“相似律”的交感行為將鑼鼓聲與雷電之聲相聯(lián)系,以模仿雷公電母的施雨行為。后來隨著儀式活動的形成與發(fā)展,人們逐漸對于“鑼、鼓、鈸”等打擊樂的伴奏方式規(guī)律化,形成專有的類型節(jié)奏,以“加古通”的“二十四番”的鑼鼓伴奏為例,目的是為了配合某類儀式活動(祈雨)的舉行效果。而儀式舞蹈與儀式音樂的交相輝映,表面上是人們?yōu)槿偵耢`之用,實則卻激發(fā)了儀式行為者的心理情緒,來滿足他們的情感表達,本身具有一定的自娛與娛人的特點。所以,在宋柳溝村的祈雨儀式中,從開場的羊角號到取雨過程中鑼鼓隊的表現(xiàn),都為整個儀式活動營造了祈雨的氛圍;而從打“加古通”的部分來看,鑼、鼓、鈸等打擊樂器的演奏音響具有一定的威力,既為表演者創(chuàng)造了祈雨氛圍的“真實性”,也被賦予了溝通神靈世界的象征意義。
第三,體現(xiàn)于人物“扮演”的虛擬性方面,舞蹈“加古通”以祈雨的過程為敘事情節(jié),運用一種舞蹈化的動作來表現(xiàn)祈雨的內(nèi)容與主題思想。首先,在宋柳溝村的祈雨儀式里,包含了一個二元對立的主體結(jié)構(gòu)模式,即儀式參與者想象并虛擬出的兩種并列的空間概念——“凡俗閾與超凡閾”。所謂“凡俗閾”是指平凡俗人的人間世界(現(xiàn)實空間);而“超凡閾”則是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鬼世界(意象空間)。舞蹈“加古通”就是一種以“舞蹈化”的肢體語言向神靈傾訴的行為,而擔任溝通神凡兩閾“媒介”作用的就是“加古通”里“引子”的角色。“引子”可以作為“皇帝”也可以作為“縣官”而存在,表演者通過特定的裝扮行頭將自己帶入人物,進入角色后,通過揣摩為民祈雨的人物心理,體驗并感受踩到“鏊子”上的狀態(tài),以表現(xiàn)出“皇帝”或“縣官”對于祈雨事項的情感與決心。隨著時間的推移,“皇帝”或“縣官”則作為一種祈雨的象征符號被當?shù)匕傩账缪荨τ诖迕穸裕挥匈F為“皇帝”或是一方“父母官員”才具備與神靈對話的權(quán)力,他們不但作為溝通人神的“媒介”,還象征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當權(quán)與百姓的關(guān)系。在某種程度上,這就進入了特納所說的“反結(jié)構(gòu)”的儀式狀態(tài)中,即參與儀式的行為者(閾限人),可以顛倒日常狀態(tài)下的社會正常關(guān)系,而得以發(fā)揮真正的人性。因此,老百姓以角色扮演的形式,塑造出“皇帝”“縣官”的形象,用此類身份與神靈作溝通,這不但體現(xiàn)出了強烈的階級觀念,也抒發(fā)了百姓對于當權(quán)者希冀的一份美好欲求,以渴求一份穩(wěn)固的生存狀態(tài)。
三、結(jié)語
“加古通”作為一種“以舞祈雨”的民間舞蹈形式,包含了兩種原始巫術(shù)的祈雨方式:一為“以舞”事神;二為“以火”自虐,意在實現(xiàn)某種交感產(chǎn)生“共情”以通天事,所以它是一種原始祭祀行為的當下遺存。那么作為一種有意指性的舞蹈形式,其形式(身體運動)自然包含了主體(表演者)所賦予的某種“意味”。所以“加古通”,通過表演者之間相互配合及逗樂調(diào)笑的舞蹈行為,來獻媚并溝通于超凡閾的神靈,從而達到人們的欲求祈雨之事。而這種祈雨功能則體現(xiàn)于其舞蹈表達的情態(tài)特征之中。
參考文獻:
[1]薛藝兵.神圣的娛樂——中國民間祭祀儀式及其音樂的人類學(xué)研究[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2][美]克利福德·格爾茲.納日碧力戈譯.文化的解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邵邦森.平陰縣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M].平陰縣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2012.
[4]高啟光.戲劇情境論[M].泰山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