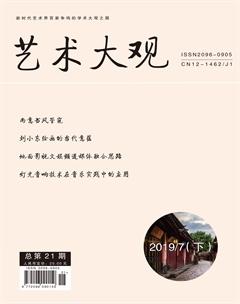尚意書風管窺
摘要:唐宋書法的分水嶺便是對于法度的態度,唐人嚴謹的理性已逐漸轉化為宋人豁達的感性。書法發展至宋代已逐漸朝系統性、專業性發展,已慢慢成為獨立的藝術。
關鍵詞:尚意書風;宋代書法;書如其人;學養人品對書家影響
宋代書家歷史觀念大大增強,其歷史責任感空前。站在歷史文化發展的角度重新審視歷代名家名作,以史家之筆評述書法變遷、考訂書法真偽、敘其流傳淵源。除此之外,注重修養,注重人品,強調書法的終極境界是書家自悟,此種理念深受禪宗思想影響。禪宗強調“以心傳心,不立文字”,故宋代少見長篇累牘的書論巨著,深奧的筆法通過直白淺顯的文字敘述出來。故看似平淡無奇的一段文字往往蘊含極其深刻的道理,書家灑脫品性可見一斑。書家思想理念的進步使書法逐漸朝系統性、專業性發展,慢慢成為獨立的藝術。
一、宋代書法與唐代書法區別
“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語出歐陽修《試筆》,其意為:“本來想著通過寫字來寄托自己的心意,進而消磨時光,何必去計較字的好壞”。由此可見唐宋書法的分水嶺便是對于法度的態度,唐人嚴謹的理性已逐漸轉化為宋人豁達的感性,這種觀念的改變大大促進書法的發展,書家以書法作品傳達生活與人生態度,使得書法藝術朝著人性化發展,大大提升其人文請神。文忠公認為寫字如“賭書消得潑茶香”般的文人消遣時光的高雅之事,應樂在其書寫的過程,不應過多關注糾結寫出字的優劣,只要能寓其心,便達其最初目的。與唐人尚法之時風相比,文忠公的這一理念實為一大突破與創新,將書法作為日常一樂,改變書者書寫之心態乃至其狀態,加以輕松愉悅自由之感,大大提高書寫的趣味性,也正是這種無形與無意之中便可創造出更多意想不到藝術效果。文忠公這一理念應為尚意書風之濫觴。
二、宋代書法家的“尚意書風”
“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語出蘇軾《石蒼舒醉墨堂》“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強調執筆應該是適宜而無一定的規則,要做到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揮灑自如、“無意于佳乃佳”更是提出了書法創作中大象無形的最高境界,這是直指靈性的高層次闡發,蘇子乃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書法家、文學家、政治家,其學識淵博、胸懷廣闊,為儒釋道之集大成者,講究自然,講究心性,講究意趣,暗合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意,間又有“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的禪宗思想。“君子敏于行而訥于言”的儒家思想,“道不可言”的道家思想,將自然、心性、藝術、思想相結合,正是“形而上者謂之道”(語出《易經》)。
米元章有云:“要之皆一戲,不當問工拙。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其認為書法不應過多地去刻意雕飾,自由的心境即為書法最好的書寫狀態。“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語出 米芾《海岳名言》)。熟習各家,吸收眾長,久而久之融會貫通,成為自己的面目,便產生了自己的風格。在此過程中他積累了一套從繼承到創新的經驗。他講究真趣,如上所述,若其無自家面目,一味泥古而無法逃脫藩籬,專與他人形似,那便無真趣可言。他認為學書臨池是愉悅身心的事情,他認為:“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有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
又如黃庭堅在《山谷集》有云:“學書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以圣哲之學,書乃可貴。”他認為書家應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魏晉書家超然塵外,故書中有“韻致”,觀黃山谷之書,其尤重魏晉之風,間得含蓄深邃之美,于筆墨之外別具情致。“凡書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工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多偏得其丑惡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粲然者。”其強調的“拙”與“巧”,“凡書要拙多于巧”黃庭堅的“拙”是建立在“巧”的技法基礎之上的,其個性韻味反對食古不化,強調從精神上對優秀傳統的繼承,而絕非一味泥古,強調個性創造,注重心靈、氣質、心境對書法創作的影響。
三、結語
“尚意書風”的廣泛流行使得北宋書學取得較高成就與發展。及至南宋,書家只知一味片面臨習蘇黃諸家,蘇黃諸家遠宗魏晉,如唐太宗所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蘇黃諸家“取法乎上”可謂得其“中”,南宋書家取法蘇黃,取法“中”故“僅得其下”。“尚意書風”傳至南宋已現頹勢,由此亦警醒書家,“取法應乎上”方可有所得,正如黃魯直所言:“取法要高,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得妙處”。
參考文獻:
[1]俞豐.經典碑帖釋文譯注[M].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
[2]王鏞.中國書法簡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傅如明.中國古代書論選讀[M].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
[4].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5]崔爾平.歷代書法論文選[M].續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
[6]水采田.宋代書論[M].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
作者簡介:招日瑞,嶺南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