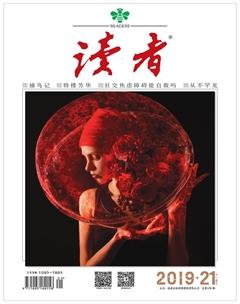一杯看劍氣
2019-10-14 03:14:50朱天文
讀者
2019年21期
朱天文
荷西在門前種樹,種好了,三毛忽然笑起來,道:“荷西,樹是有臉的呢。”種好的樹,又挖出來重新種了。
今天早晨,我把桌上的兩顆椰子放在水龍頭下沖洗,想起三毛的話,將兩顆椰子整了整方向。看看,果然是一臉喜滋滋地迎著人笑哩。
知道三毛,是從“聯(lián)副”刊登的《中國飯店》開始;認識三毛,卻是在《聯(lián)合報》小說獎頒獎典禮上。這期間,1977年,三毛曾寫過一封長信給天心。三毛向來不主動寫信給別人,那次因為讀了《擊壤歌》,晚上睡不著覺,踱來踱去踱了一夜,隔天就寄了十美金來,附上只有一句話的短箋。她原以為天心不過一笑置之,豈知天心亦是喜歡她的。自那時起,只曉得天涯海角有個三毛,隔著千重山萬重山,偶爾才從報章雜志上捎來天邊的一朵白云。一種牽掛,而好像連牽掛也說不上的,便只是兩地閑情,都共在一個日光星辰下吧。
然后就是荷西去世。三毛回來了。
我們也不去信,也不打電話,冷漠得像是連起碼的人情都沒有了。只因為一番痛惜珍重之意,竟連驚動也不敢,便是一句半句安慰的話,都是冒犯了。
在《聯(lián)合報》的頒獎典禮上,出乎意料地遇見三毛,是天心先發(fā)現的。我們趕緊跑到她面前,天心才說一聲“我是天心”,眼淚就嘩嘩地流了滿面。頒獎過程中,三毛隔著一條通道坐在我們斜前方,曉得我們在看她,偶爾回過臉來望一下,我的心口就像給抽了一鞭。她全身穿黑,裙子底下是馬靴,頭發(fā)中分披肩,露出一張蒼白的小臉,脂粉不施,只畫了眼圈,整個人像是只剩下一息意志。……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