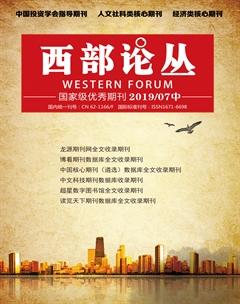李鴻章洋務思想研究綜述
摘 要: 李鴻章洋務思想的研究在文革前后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風格,出現大量的新觀點。隨著研究氣氛的開放與自由,學界對李鴻章洋務思想的研究也涌現出一部分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關于洋務思想的演進過程研究以及洋務思想的內容研究更加的詳細深入,洋務思想研究角度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對于李鴻章洋務思想的評價也有更多不同的觀點。
關鍵詞:李鴻章 洋務思想 綜述
一、李鴻章及其洋務運動的研究概況
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晚晴重臣李鴻章一直以來飽受爭議。而由其主導的洋務運動在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有著重要的意義,故而史學界通常將李鴻章與洋務運動聯系起來作為研究對象。總體來看,國內關于李鴻章與其洋務運動的研究大概經歷了三個階段:新中國成立前、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后。新中國成立之前,對李鴻章及其洋務運動的研究目的多為救國圖存,馮桂芬、鄭觀應、梁啟超等在其著作中均對洋務運動進行總結,也涉及對李鴻章的評價,較為中肯多肯定其軍工否定其外交,這一時期的評價毀譽參半但仍不失公允;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因受政氛圍的影響,研究著作并不多,對洋務運動及李鴻章的評價多為負面評價;改革開放之后,這一時期的學術氛圍寬松,學術研究活躍,1988年的“李鴻章與近代經濟學術研討會”將關于李鴻章級洋務運動的研究推向高潮,在李鴻章的歷史作用方面諸多學者開始采用辯證的審視眼光,一改全盤否定、過激評論的局面,將李鴻章、洋務運動放在變革中的近代中國以及其國際背景中進行研究,是這一階段研究中的突出特點。
綜合分析近年來李鴻章洋務思想研究的成果與不足,可以為接下來的研究提供研究方向,增加研究的深度與廣度。總體來看近年來關于李鴻章洋務思想的研究包括三個方面:洋務思想的演進過程、洋務思想內容、洋務思想的評價。此外圍繞李鴻章洋務思想進行研究的研究角度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二、洋務思想的演進過程研究
學界普遍認為洋務思想萌芽源于李鴻章對當時時局的清醒認識。李鴻章清楚的認識到,當時的中國已經是從華夷隔絕發展到了中外聯屬的狀況,這是李鴻章一系列洋務思想的起點。鄭春奎認為李鴻章的洋務思想經歷了由“戎和”到“變法自強”“求富”再到“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的發展過程,主要強調李鴻章洋務思想發展過程的上下銜接環環相扣的發展特點。彭代璞將李鴻章洋務思想的演變過程分為“從‘經世致用的新儒學思想到‘喜談洋務”、“提出洋務的總綱‘外須和戎,內須變法”、“從‘師其所能,奪其所恃到‘必先富而后能強”、“從‘洋學實有逾于華學者到‘廢制議事”[1]四個部分,重點分析李鴻章在形成洋務思想前與形成洋務思想之后的轉變對比,從前后思想的變化上對李鴻章洋務思想的形成與演化過程進行闡述。
二、洋務思想的內容研究
李鴻章洋務思想以變法為核心所包含的內容涉及軍事、教育、經濟、制度、外交、等多個方面,目前學界多著眼于李鴻章洋務思想中的外交內容研究,對變法的具體內容研究還不透徹。大部分學者認為,“外須和戎,內須變法”是洋務運動的總綱領,“師其所能,奪其所恃”是洋務思想的中心內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洋務運動的理論原則。具體分析洋務思想的內容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羅春喜 聶麗君認為李鴻章洋務思想的基本內容有:軍事自強、經濟自強、文化自強、外交自強。在變法思想的研究上,朱海伍認為,變法自強是李鴻章洋務思想的核心,變法的內容包括變易兵制建立新軍、大治水軍加強海防、講求軍器以與西洋相埒;必先富而后能強為洋務改革提供經濟基礎,主要措施有:大力興辦現代企業、官督商辦、稍分洋商之利、對外通商;教育上向西方學習,改良科舉重建取士標準、發展西學培養現代人才、留學海外直面西方文明;以據理力爭、委曲求全、以夷制夷的方式進行“和戎”外交營造洋務改革的外部條件。鄭春奎認為李鴻章洋務思想中的變法思想主要有:政治上主張改革官制;教育上主張變科舉;經濟上主張發展民族工業;軍事上需要變易兵制。
外交思想的研究中心是李鴻章“外須戎和”的對外主張。對李鴻章“外須戎和”的外交觀的認識經歷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同對李鴻章洋務思想的認知發展相同,文革之前“外須戎和”的外交觀意味著賣國求榮,是一種賣國政策,在研究中也普遍持全盤否定的狀態。文革之后,研究的學風逐漸放開,隨著對李鴻章的認識越來越辯證客觀,學界對“外須戎和”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轉變。學界普遍承認“外須戎和”與“內虛變法”是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是緊密相連的,應聯合起來進行整體分析。鄭春奎認為“外須和戎”是服務于“內須變法”的。“和戎”是條件,“自強”是目的,而要達到自強,就要“變法”。在“和戎”的目的上,他認為“對外非戰,要‘和戎的真正目的,在于希望求得一個和平的環境,以‘變法,徐圖‘自強,增強與洋人抗爭的能力”[2]。楊全順認為,李鴻章“外須和戎”的本意并不是汝求予給,拱手聽命,希冀“保境安民”、“相安無事”,避免中國完全殖民地化。朱海伍認為“和戎”外交為洋務改革提供了外部條件。
三、洋務思想研究角度的多樣化
改革開放后史學界已經開始將李鴻章及與其有關內容的研究放入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進行分析,在研究角度上也更多樣化。以區域劃分,關于李鴻章洋務思想的研究分為國內研究與海外研究,其中國內研究又可分為大陸研究與臺灣研究。解放前的大陸李鴻章洋務思想研究略顯沉悶,帶有明顯的階級色彩,改革開放之后,在研究眼光上逐步全面化辯證化,也產出一部分有影響力的研究專著。
除了對李鴻章本人進行研究之外,有學者還從其幕友思想著手,研究李鴻章幕友對其洋務思想的影響。白雪松、李秋生從分析馮桂芬、郭嵩燾、薛福成者三位李鴻章幕友的思想發展過程入手,進而分析這三位幕友對李鴻章洋務思想的影響,從而更加完整全面的反映影響李鴻章洋務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的因素。白雪松、李秋生認為,幕友的危局意識對李鴻章洋務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推動李鴻章洋務思想萌芽的出現;李鴻章的主和思想和其幕友的主和思想如此類似,其中郭嵩燾對李鴻章避戰主和思想的影響最大,并且郭嵩燾研究歷史和現狀,提出了全新的對外關系理論。
四、李鴻章洋務思想評價研究
對李鴻章洋務思想的評價同樣經歷從全盤否定到客觀評判的發展過程。在李鴻章洋務思想中爭議最大的問題就是“和戎”外交觀的性質。改革開放以前,“和戎”被視為賣國政策,改革開放之后,學界對李鴻章“和戎”觀點的研究有了徹底的轉變,對“和戎”這種外交觀念的評價也有了根本性的轉變。隨著學界對“和戎”目的認識的轉變,以及將“和戎”與“變法”聯系到一起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研究者們對李鴻章“外須和戎,內需變法”的評價有了全盤的改變。楊順全以為,外須和戎”清楚認識到中外的客觀差距,希冀求得和平環境,徐圖“自強”,有其合理的一面,主“和”并不是消極的妥協投降,“和”只是一種備戰手段。“但他把‘外須和戎看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唯一的外交準則,以致于步步誤國,白白喪失了中國許多本來不該失去的權利”[3]實質上違背了“外須和戎”的方針。這種“和戎”名為求和實為備戰的觀點,在學界也有不少學者的支持,普遍認為這種政策的出發點與設置較符合當時的歷史情況,但由于對國情的誤判而導致一步步后退最后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結果。 但若是僅因如此就將李鴻及其“和戎”思想判定為賣國,未免有點太狹隘。“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之下來決定”,對歷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評價應結合其所處的歷史環境,將其放入歷史的長河中綜合考察評價。
評價李鴻章的洋務思想,還有一個問題是具有爭議性的,那就是李鴻章的器物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19世紀60年代之后洋務派向西方學習的指導思想,李鴻章對西方的感知是從器物開始的,向西方進行學習也是從器物開始的。以往研究中,常常把李鴻章中體西用主張中的西用,即向西方學習先進器物技術的觀點看成一種局限性,也有學者認為正是因為關注點在器物方面因而導致了洋務運動的破產。但在近期的研究中有研究者認為,李鴻章的器物觀是制度變法的鋪墊。當時的中國,封建體制根深蒂固,直接進行制度改革不僅遭到權貴階層的阻撓,還會帶來社會的動蕩不安,而先從器物層面進行變革從而影響意識層面的認識,反而能更好的進行體制的變革,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當然這種從器物開始進行變革的方法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但仍應認識到其可取之處,客觀辯證的分析對待。
參考文獻
[1] 彭代璞.李鴻章洋務思想的形成與演進[J].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999,3
[2] 鄭春奎.簡論李鴻章的洋務思想[J].麗水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3,6
[3] 楊全順.李鴻章洋務思想新論[J].棗莊師專學報,2000,1
[4] 朱海伍.李鴻章洋務思想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4
[5] 白雪松 李秋生.李鴻章幕友對其洋務思想的影響[J].廊坊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
[6] 范保國.歷史夾縫中的艱難選擇——評李鴻章的洋務思想[J].邵陽師專學報1997,6
[7] 閻建寧.歷史夾縫中的艱難選擇——也評李鴻章的“洋務”思想[J].博士論壇,2005,5
[8] 戴仕軍.李鴻章研究概述[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
[9] 王秀麗.李鴻章研究綜述[J].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9,2期
[10] 立早.近年來李鴻章研究綜述[J].湘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2
作者簡介:李夢雪(1996-)女,漢族,安徽宿州人,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部,2017級研究生,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