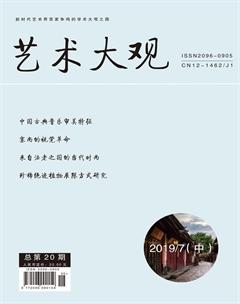模印磚文的藝術價值
摘要:模印作為一種制作工藝,在磚、瓦的制作過程當中普遍存在,是指在磚或者瓦的制作過程中,通過模具進行壓制而出現的文字。
關鍵詞:模印;磚文;篆刻
這里所講的模印文字,僅限于從西漢開始出現的,在磚身、瓦當上出現的文字,不包括用印章戳印的部分。印章戳記和模印雖然有著某些相同之處,但是印章戳記作為一種“物勒工名”的遺存,他的主要作用還是以實用為主,但是在模印文字上,已經和印章戳記有所不同,他有一定的實用性,但是在實用的同時,包含了很多的審美要素,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模印磚文對于篆刻藝術的影響
特別是從丁敬開始,浙派印人,都在進行“印外求印”的探索,他們對于磚文的取法在他們的篆刻作品當中有很多的出現,特別是對磚文中所包含的“金石氣”的模仿。
在趙之謙的印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邊款中有一些記載了明確取法,在這些當中,有一方“鄭齋”,是取法磚文,趙之謙對于磚文的接觸,應該是很早的,他“十七歲就為金石之學”,而“山陰沈霞西布衣復粲第一導師也”,他的第一導師沈復粲,是藏磚大家,有《磚文類聚》二卷傳世,對于磚文的研究、收藏必定豐富,趙之謙在最早“為金石之學”是,和這些磚就應該有較為親密的接觸。
另外,吳昌碩的“既壽”印,同一內容吳昌碩刻過兩次,都是直接將磚文當中的文字截取,通過一系列的藝術加工完成的。這兩方印,所用文字和陸心源《千甓亭古磚圖錄》里面“既壽考宜子孫”磚文的字法是一致的。另外“千石公侯壽貴”一印,是直接將吉語磚中的文字,直接轉移到當中,只是改變文字的排列方法。
在吳昌碩的篆刻當中,表現出一種蒼茫,宏大的氣象,這和他篆刻當中的線條是分不開的。吳昌碩朱文的線條都不是光潔的,這個應該是從他青年時期學印當中遺存下來的,吳昌碩早期的印章,我們可以在《樸巢印存》中找到,這里面又學習漢印、皖派和浙派的印章,并且孕育出了吳昌碩的個人風格。吳昌碩在刻制印章的過程中,用的是沖切相結合的刀法,僅用沖刀,則線條板滯,毫無生氣,僅用切刀,則線條破碎,沒有節奏性,線條一樣沒有生氣。吳昌碩在采用沖切相結合刀法的同時,為了達到自己的藝術目的,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法,使線條產生斑駁感,以達到契合古物“金石氣”的目的。在篆刻當中,對于“金石氣”的追求,我們從沈野《印談》中,可以看到他的記載,“文國博刻石章完,必置之櫝中,令童子盡日搖之;陳太學以石章擲地數次,待其剝落有古色,然后已。”我們可以把吳昌碩篆刻當中的線條和磚文當中的線條進行對比,不難發現磚文的痕跡,磚文在制作過程中,由于是使用模具進行壓制,多為陽文,再加上經過流傳,難免在文字線條上出現一些殘缺,吳昌碩在印章的刻制當中,將這種殘缺的審美觀念,借鑒過來,以達到對“金石氣”的追求。也和他的“守殘抱闕”觀念相契合。
吳昌碩在磚文當中獲益最大的是他在處理邊欄的時候。很多人認為吳昌碩對于封泥的取法大于磚文,但是吳昌碩所見到和收藏的封泥數量并不多,他的這種追求殘破美的審美趨向,應該來自磚文。雖然吳昌碩所收藏的十三品磚文是“吳五晉八”,但是在他的交際圈當中,有很多人是從事古磚的收藏工作的。如陸心源、吳廷康,俞樾等人。尤其是陸心源,富有漢、晉磚文,所以在吳昌碩的交際圈當中,吳昌碩有很多的機會取接觸漢、晉時期的磚文。
二、模印磚文對書法的影響
在書法方面,模印類文字豐富了文字的用法,使得書法家,在進行書法創作的時候,可以有更多的選擇,這對于豐富書法作品的內涵有重大的作用。而且這些從地下直接出土的磚瓦文字,相對于轉刻與木板、石板上的刻帖更加可信,可靠性更高。由于這些文字假與匠人之手,所以,這些文字當中充滿意趣,文字的變化也是更加的奇麗。凌霞在《千甓亭古磚圖釋·序》中這樣說“若夫字跡之瑰奇,尤覺變態不窮,雖間出匠人俗手,其古致亦可喜也。”比如吳昌碩對于磚瓦文字就情有獨鐘,不僅在他的篆刻當中會摻入磚瓦文字,在他的書法作品當中,也出現了對于磚瓦文字的取法,在他的畫當中,也要有磚瓦的參與。如他在80歲的時候書寫的橫批“金石同壽”,在落款的時候就說到是“橅古磚文”。除了吳昌碩之外,其他的如“金石僧”達受、吳廷康、許梿等人都有模仿磚文的作品流傳。
三、模印磚文對繪畫的影響
到清代模印磚文參加到了繪畫當中,成為中國畫的另外一種形式。在清代晚期的中國畫而當中,出現了磚文拓片參加到中國畫的創作當中。這類古物拓片參與的畫作,也稱之為“博古畫”,“博古畫”的產生是基于全形拓而完成的。在道咸時期,全形拓大興,所以在這個時期,“博古圖”也有大量的產生。從清代末期到民國的這段時期,許多的博古圖也應運而生。吳昌碩由于獨愛古磚,所以有很多的古磚博古圖。
除此之外,模印文字更是“隸變”過程當中的重要節點,由于模印文字相對于同時期的文字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保留了“隸變”過程當中的一些特征,對于研究篆書的演化過程有著重要的作用。模印磚文作為一種獨立的體系,不管是對書法藝術,還是對文字的演化來說,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作者簡介:李逸群,曲阜師范大學曲阜校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