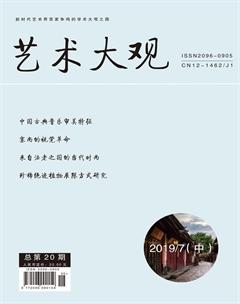河西佛像與壁畫不同時代地域的差異
張倩

摘要:佛教產生于印度,自兩漢時期傳入我國,從此佛教便在中國發展傳播,影響了我國的方方面面。佛教同時也被佛教造像和精美洞窟壁畫這種藝術形式所承載,得以留存,也讓我們可以感受到當時的藝術的發展。魏晉南北朝是佛教傳入我國然后傳播的重要時期,十六國至北魏前期的河西地區有許多石窟,這些石窟里的佛像和壁畫在不同地區不同階段又有著不同的藝術形式。
關鍵詞:河西;石窟;十六國
甘肅省位于祖國的西北,地形狹長如走廊,東西綿延一千四五百公里,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隘和咽喉之地。漢唐這個時期,隨著這個著名的“絲綢之路”的開拓與暢通,古代甘肅作為中西交通的甬道,在溝通我國中原與西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增長。
沿著絲綢之路各個地區和附近都有眾多的石窟,石窟里有令人嘆為觀止的大量精美絕倫的佛教造像和壁畫,這些都是當時經濟文化發展交融留下的重要遺跡和珍貴財富。河西地區的這些石窟因為年代的不同,地區的差別,洞窟內的佛教造像、壁畫也會隨之有不同的變化,以不同的形式出現,體現了時間與地點的差異。這些差異也是我們研究佛教造像和壁畫,研究這一文明所必須要重視的部分。
一、十六國時期總體風格之差異
十六國時期,在中國北方各族劇烈爭斗、政權頻繁更迭的混亂狀態之下,中原和內地傳統的漢文化一儒學遭受到極嚴重的打擊,處于衰敗的境地。而這時的河西地區卻成為中國北方一個漢文化的保留區和發展區,儒學呈現出極為興盛的景象。
佛教從印度經西域傳入河西地區時,某種程度而言,也就進入了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基礎的漢文化區。要在儒家思想流行的河西立足,佛教就必須依附和借助傳統文化進行傳播,而佛教藝術也必須做出相應的改變。以“飛天”為例,敦煌地區的飛天雖然大多還上裸下裙,卻已不再似印度和西域地區的飛天酥胸祖露,而是以扁平的胸肌取而代之。此外,印度和西域地區成對出現的男女飛天在河西地區也難覓行蹤,而以男性或中性的飛天為多。敦煌早期的飛天由于原來粉紅色的硫化汞和碳酸鉛氧化,使暈染層次、線條發生變化,特別是眉目間原來的粉紅肉色褪色后,只留下白色、青灰色,面部變為兩個大黑圈,形成一種“小字臉”白鼻梁、白眼珠的效果。人物的面部特征已較難辨認。鄰近的北涼酒泉文殊山“飛天”雖然不如印度、西域飛天豐滿,但眼大且長眉如彎弓等特征基本保留。
因此,可以推斷,十六國時期,西域、敦煌和酒泉地區飛天總體上呈西域梵相。與敦煌、酒泉地區飛天不同,在金塔寺彩塑及炳靈寺壁畫中飛天的面相、體形呈現出明顯的本地女性特征。張掖金塔寺和武威天梯山石窟中,均有北涼時期的飛天影塑或壁畫,仔細觀察這些塑繪結合、色澤鮮艷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十六國時期隨著地域的向東推進,張掖和武威地區的飛天呈現出與西域、敦煌飛天不同的面貌,人物臉部不再似印度與西域地區的橢圓卵形,代之以方圓豐滿的中國北方人的臉形,眉形稍彎但不似印度與西域的長而彎曲,間距較寬,且有著衣飛天出現,本土化的痕跡明顯。
二、佛像和壁畫的具體差異
在東晉十六國時期,甘肅出現了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天水麥積山,永靖炳靈寺等20多個石窟。
在這一時期石窟造像是三種不同文化融合的結果。第一是外來文化,是印度各地的佛教文化。石窟造像沿著河西長廊傳入中國一開始,這些佛像在造型上含有大量的犍陀羅的藝術成分,造像的形式也非常接近印度及中亞的佛像。這也不奇怪,因為可以學習傳出的也只有這個出處,西域興起傳入自然要學習描摹它們。第二是漢民族傳統文化,主要是指中原地區文化。第三是西北少數民族的文化。這三種文化在這一時期相聚交融,這其中印度的佛教文化最為突出。
敦煌莫高窟中第254窟的交腳佛和第259窟的菩薩像(圖一),這些佛像額頭寬闊,鼻梁高隆,眉毛細細長長,嘴唇很薄,發髻是波紋狀的,體格雄偉,袒胸露肩的特點有印度遺風的影子。
莫高窟第275窟(圖二)是年代最再早的洞窟之一,塑于北涼時期的交腳彌勒菩薩像,高置在洞窟上端的漢式子母闕形龕的頂部、瓦飾和門楣皆用泥塑而成,繪畫與雕塑結合自然,體現了中國傳統藝術繪塑不分的特點。造像保存的完好,眉宇高昂,一種有氣魄的樣子,這座交腳菩薩面相圓潤,它的上身是袒露的下面的衣紋用的是貼泥條的方式做出了衣褶,整個交腳菩薩形象,衣著,彩繪方式都有明顯的西域龜茲的影響。
甘肅永靖的炳靈寺169窟(圖三)主佛像形體健碩,面型方圓,神情非常寧靜。菩薩像近似女童,面相圓潤,服飾仍然是西域的風格,顏色艷麗。這時的技法比早期的莫高窟雕像更加精細一些,它們的面相神采更接近胡人。這就說明了,那是的制作雕像者,沒有直接采用西域的這種風格模式,而是將當時人們的審美要求,現實生活與這種西域風格結合。
在此時,麥積山石窟又不像同期的莫高窟貼壁塑那么古拙,在麥積山第100窟里的造像具有一種挺秀飄逸的神韻,瘦削卻不枯,生動活潑,比同期莫高窟要精彩一些。
炳靈寺的169窟的塑像和壁畫在西秦時期就已經存在了,這個窟內的6龕是在巖壁上用木骨敷泥做的,它的形狀好似三瓣蓮花,龕內主尊為無量壽佛,佛像有高肉髻,面相渾圓,額際有明豪,細眉大眼,鼻直口方,嘴唇上有胡須。雙肩寬厚,腰很細,身體就顯得很粗壯。里面穿著會有龜背紋樣的僧祗支,外面披了袒右式袈裟。佛像左側為大勢至菩薩,右側為觀世音菩薩。菩薩均頭束高髻,長長的發辮垂于肩上,臉龐豐圓面帶微笑,脖子上帶項圈,身體修長。披巾從雙肩搭下,繞著手臂下垂,叉足立于蓮臺上。
從壁畫的技法看,既有西域流行的暈染法,又有中原式的不暈染。這也證明了炳靈寺石窟在受著中原影響的同時,也受到了西域文化和繪畫的影響。
莫高窟第272窟北涼時期菩薩壁畫,這尊菩薩文靜、高雅,兩個眼睛微微看著下面,上半身向左邊輕輕側身,左手做法印。它的右手貼著膝蓋,手指的刻畫十分生動。雙足踏蓮花,頭上戴著三珠寶冠,冠帶飄飄。脖子上掛著項圈,肩上披著彩色的披巾,腰上系著白色的長裙,裙擺下還可以看出它的身體形態。土地是紅色的背景,形成了一種注目的對比色調。
三、魏晉時期總體風格
魏晉南北朝是佛像石窟造像引進后的造像藝術的第一個繁盛期,此時期的石窟造像從藝術風格來看,第一它受到了印度佛教藝術流派中秣菟羅藝術的影響,秣菟羅是吸收了犍陀羅佛教藝術,形成了新的藝術風格,佛像薄衣透體,衣紋細密而勻稱。第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石窟造像以宗教性、理想性為宗旨。石窟造像首先表現出來的是強烈的理想色彩,是超脫于人間的神的形象,具有雕塑的和諧美、靜穆美。第三是繼承了我國的傳統造型藝術如墨陶造型及紋飾的簡潔爽利的風格,從整體藝術效果來看,南北朝著名的畫家楊子華、張僧繇所創造的“疏體”在石窟上有明顯的表現。“疏體”雕塑,大都以十分簡略洗練的線條(隱起顯、陰線)來雕服飾,衣裙用極薄的淺雕或剔雕手法,從而突出了造像整體造型的生動感,豐滿感。
佛教傳入后十六國至北魏前期的麥積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炳靈寺石窟等都留下了珍貴的佛教造像,精美壁畫等等大量的藝術作品,這些藝術作品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以不同的形式展現著佛教這一具有無窮魅力的藝術,找出它們之間的差異,我們更能了解當時的藝術發展歷程,能夠更好地傳承中華之佛教藝術。
參考文獻:
[1]李裕群.山野佛光·中國石窟寺藝術[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2]史敦宇,歐陽琳,史葦湘,金洵瑨.敦煌壁畫復原圖[M].江蘇美術出版社,2013.
[3]歐陽啟名.佛教造像[M].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4]張豫.中國佛教石窟造像藝術探究[D].武漢理工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