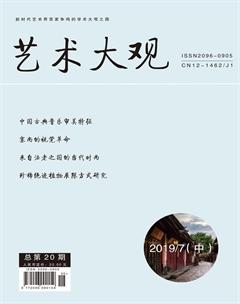從喜龍仁看北京的城墻與其周圍環境的關系
王子晴
摘要:瑞典著名美術史家奧斯瓦爾德 喜龍仁(Osvald Siren)于20世紀初來到中國,在中國多地進行考察,特別是在北京。居住北京期間,他重點研究了北京的城墻與城門。在他的著作《北京的城墻與城門》中,很多地方都體現了建筑與其周圍環境的關系這一概念。本文將會根據喜龍仁的思路來論述北京城墻、城門與其周圍環境的關系。
關鍵詞:喜龍仁;建筑;北京的城墻與城門;周圍環境
從春秋戰國開始,中國就有了建筑環境整體經營的觀念。《周禮》中關于野、都、鄙、鄉、閭、里、邑、丘、甸等的規劃制度,雖然并沒有全部實現,但至少說明在當時人們就已經有了大區域規劃的構思。《管子·乘馬》主張:“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說明城市選址必須考慮環境關系。但實際上,在西方建筑中,建筑設計大都只考慮建筑的外立面,沒有注重建筑與周圍環境和諧的問題,現代建筑也存在這樣的情況,太注重于各座建筑物本身。而作為中國古建筑的代表作品,北京的城墻和城門就完美地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建筑與環境相和諧的思想。喜龍仁在《北京的城墻與城門》中也恰好提到了這一點:“而外城城門則往往是建筑、景觀與自然環境的完美融合”。
一、城墻與自然環境
環境有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之分。首先,城墻周圍的自然環境會對城墻的總體風貌產生影響。“從遠處看,它們呈一條連續不斷的實線,其間點綴著高聳的城樓,在溫暖的季節里,頂部茂盛的樹叢和灌木為城墻添了幾分生機。”我們可以想象到這樣的場景:當北京的天暖和起來的時候,樹叢和灌木爭著長高,它們的那抹深綠為城墻的灰泥添了幾分生機,正如先生所說“這種色彩的遠觀效果頗佳,尤其是當建筑處于繁盛花木的掩映之中時。”這是周圍樹木與內城的城墻一同展現出的藝術魅力。但是中國古代并不會單純出于藝術去設計建筑,因此可以考慮周圍環境為建筑帶來的實用性影響。樹木不僅影響視覺效果,也會影響到建筑物受到的日照強度、采光、通風等因素。眾所周知,北京易受到風沙的影響,一旦北風襲來,城墻旁的樹木就可以成為城墻的屏障,讓它更少地受到歲月的侵襲。除了樹木之外,離城墻最近的就是護城河了,喜龍仁筆下那“絕無僅有的美麗景象”正是護城河與城門一起構成的。“春末夏初是觀賞這座城門的最佳時節,楊柳吐露嫩葉,護城河中的蘆葦充滿新綠,如運河般寬闊的護城河是整個景觀的動脈。”護城河為東城墻上的城門帶來的是撥弄水花的白鴨,是岸邊拱著土壤的黑豬,是生機與活力,是自然環境與建筑的完美融合。
二、城墻與社會環境
“我只想說,城門的美,不僅僅來源于樹木、屋舍、橋梁等景觀,而居民的生活、光影和氛圍也同樣令人陶醉”,確實,有城墻的地方,就有人們的足跡,下面文章就談談城墻與它周圍的社會環境。東便門東邊流過的是運河,這次河邊的身影不是白鴨黑豬,而是運河上橫跨的一座三孔石橋上的孩童,他們喧鬧著,在水中洗著棉紗和新染的藍布,東邊更熱鬧,一群年輕男女乘著游船灑下一路歡聲笑語。城門給人們的印象大多是孤獨的,它在城市最邊角的地方看著無數行人走過,無數故事發生,看日出日落,看世間滄桑,但這些卻與它毫無關系。而在喜龍仁的描述中,城墻毫無孤單之感,它與路過的人們和諧相處,共同為北京城營造一種和美之感。
另一方面,其實在20世紀的北京,已經出現了不少與之前不一樣的新東西。車站、彈藥庫、鐵路車間還有煤市,這些建筑物一出現就占據了南城墻外側壁的大片空間,使得古老的城墻與周圍環境極不協調。“總的來看,我們必須承認,無論從城墻和城門的特征還是美感上,鐵路及其各種附屬建筑對其的破壞要遠大于對這些古跡的忽視和維護不周所造成的殘缺。”凝望如今的西安,西安作為十三朝古都,擁有眾多古建筑遺跡,但是城市管理者不僅沒有好好保護利用這些古建筑,反而跟風建設許多鋼筋混凝土的大樓,遮掩了古城原本的光輝,使得西安少了古樸之意,多了不倫不類之感。而北京城墻的不倫不類感則是中西相克帶來的,南城墻的前門是北京城墻上最大的城門,同時也是城市不同功能區的交匯點。前門以東是使館區,這里有在高度上與城墻抗衡的西洋建筑,它們高傲地揚著頭,與旁邊樸實敦厚地屹立著的城墻沒有絲毫的一致性,只有中西碰撞的不適感。更嚴重的是內城的箭樓,它被重新裝飾,某種程度上它已經成為一座西洋式建筑了。這就不僅僅是造成視覺污染、影響城市的總體風貌了,這更是對傳統建筑的一種扭曲。這是建筑與社會環境不協調所造成的糟糕場面。
三、其他建筑與其周圍環境
不僅是城墻,還有園林也體現著建筑與環境相統一的思想。喜龍仁對北京皇家園林的印象是“因借自然”,也就是說它做到了“雖由人做,宛自天開”。在他探訪禮王府、成王府、七王爺府、僧王府等清朝貴族府邸時,更有此感。這些宅院大都講究規矩,各個院落之間形成了一種巧妙的空間組合關系。這些府邸的花園里滿是高大的樹木和鮮艷的花草,它們與房屋交相輝映,造就了“巧成自然之工”的藝術性質。
在此不得不提到蘇州博物館,它也可以算是建筑物與其周圍環境相協調的又一典范。把博物館置于院落之間,博物館的主庭院等于是北面拙政園建筑風格的延伸和現代版的詮釋,館建筑與創新的園藝相互依托。其實它已經不僅僅是博物館,它儼然是一個創意山水園了。而恰巧建筑造型與所處環境自然融合也正是建筑師貝聿銘的設計風格之一。從古到今,從中國到世界,建筑與周圍環境相和諧一直都是建筑師們努力遵循的規律和法條,西湖與它周圍的孤山、小瀛洲相得益彰;柏林蘇軍紀念碑的蘇軍戰士雕像與周圍的灰塑花圈相互協調;北京天安門城樓與周圍天安門廣場和故宮搭配得渾然一體;緊鄰大海的悉尼歌劇院那既像風帆又像貝殼的屋面與周圍的環境搭配得恰到好處;塞納河畔的埃菲爾鐵塔其周圍的建筑物只有七、八層,以此來襯托它的頂天立地。這些建筑周圍的環境因素都加強了原有的單個建筑物的藝術感染力,正如草木、行人之于城墻,他們是城墻的配景,更是不可或缺的景觀因素。這也正體現著“因地制宜”這一理念,完美詮釋著建筑與環境的相互協調關系。
四、結語
葡萄牙著名建筑師阿爾瓦羅·西扎的作品中體現著“場所精神”,也就是說建筑給人一種像從自然風景和城市環境中生長出來的一樣。荷蘭建筑大師基·考恩尼的想法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認為:“建筑絕不只是單一存在的個體。它與構成自然的許多秩序一樣,也是龐大秩序中的一個。”這些建筑大師的思想都體現了環境之于建筑本身的重要性,建筑設計,歸根結底是設計環境。而北京城墻中體現出的這一經典理念也恰恰體現了北京城墻具有的建筑美學價值。在失去北京城墻的今天,希望有更多的人去關注、研究、傳承它。當不再擁有的時候,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忘記。
參考文獻:
[1][瑞典]喜龍仁.北京的城墻與城門[M].人民日報出版社,1985.
[2]劉臨安,杜彬.20世紀早期喜龍仁在中國建筑考察的回顧[J].建筑師,2017(3):27-32.
[3]張帆影.“采莓者”的探索:喜龍仁的中國繪畫研究之路[J].美術觀察,2017(11):132-133.
[4]李吳.用一本書留住北平——讀《北京的城墻與城門》有感[J].北京規劃建設,2017(4):168-169.
[5]葉公平.喜龍仁在華交游考[J].美術學報,2016(3):6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