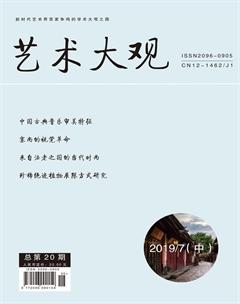生生不息,美美與共
摘要:曾繁仁著《中西對話中的生態美學》一書,圍繞著“如何將生態美學的時代性與本土性相統一,創造出具有足夠闡釋力與民族性的生態美學話語”這一核心問題,打破傳統主客二分的認識論美學,立足于當代存在哲學將生態、審美與人加以統一。通過該著作并結合作者其他論文可以看出曾繁仁力主一種具有中國“中和論哲學”特色的“生態人文主義”,嘗試創造出一種會通中西的新美學話語。
關鍵詞:生態美學;中和論哲學;現象學;生態人文主義
什么是生態美學?從狹義方面來說,是以生態系統的角度來審視自然之美;廣義的角度則是生態文明新時代的美學。曾繁仁正是依托了生態文明新時代的美學這一理解,在中西對話的語境中展開生態美學的研究。
一、生態美學的前提——存在論美學
工業革命時期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人類理性被逐步放大,產生了一系列尖銳的矛盾,越來越嚴重地威脅到人的現實生存狀況。要改變這樣的生存狀況,除了依靠經濟社會的發展、制度的改善,還需要美學關照,這便為當代存在論美學提供了土壤。
曾繁仁正是在這種時代文明、美學動態的轉向中,提出在“生態存在論美學觀”的框架。當代存在論美學觀最重要的理論內涵是以胡塞爾所開創的現象學作為其哲學與方法論指導。使其從傳統的主客二元對立的認識論模式,跨越到“主體間性”的現代哲學。
在以西方論在論美學理論形態下,自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也不能全拿來套用于中國的實際問題,這便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如何將生態美學的時代性與本土性相統一,創造出具有足夠闡釋力與民族性的生態美學話語?”。
二、中西比較視野中的生態美學的突破
在審視中國古代美學思想研究時,長期都是“以西釋中”的方法,但是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國古代是一種“天人合一”的“中和論”哲學,西方則是“天人相分”的“和諧論”的實體哲學。在這兩種哲學的根本觀念的不同上,曾繁仁則是以生態存在論美學觀認為與傳統文學批評和美學相比,當下時代語境下的生態批評和生態美學最大的理論原則轉變是從“人類中心主義”轉向“生態整體主義”;與此相適應的是從“工具理性世界觀”到“生態世界觀”;從“主客二分”的出發點到“有機整體的一元化”的轉變。
具體的學科突破則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美學之哲學基礎的突破,生態美學使得美學的哲學基礎由傳統的認識論過渡到實踐哲學,并由人類中心主義過渡到生態整體主義;
(二)美學對象上的突破,生態美學超越了藝術中心主義,不僅具有自然審美的意蘊,還同時影響了藝術審美與生活審美;
(三)自然審美上的突破,從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看待自然轉變成自然審美屬性與人的審美能力交互作用的結果;
(四)審美屬性的突破,由“實踐美學”轉換為“參與美學”;
(五)美學范式的突破:生態美學是一種人生美學、存在論美學,突破了形式美的種種限定;
(六)中國傳統美學地位的突破:中國豐富的生態審美智慧都對當代西方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產生過重要啟示,是中西會通建設當代生態美學的豐富資源。
三、中西對話的美學話語建設——中和論
中西生態美學對話最后落腳在有中國特色的生態美學話語建設之上。這就是作者尋覓的一種如何將生態美學的時代性與本土性相統一,創造出具有足夠闡釋力與民族性的生態美學話語。
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中,農耕作為中國古代主要生產方式,形成了重農輕商的文化傳統,這就是古代中國“天人合一”的古典生態文化產生的背景。現代生態文化與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原生性文化有著天然的銜接性。而西方古代則是以一種商業和海洋的科技文化,是一種對于物質或精神“實體性”的追求。生態文化對于西方是一種“后生性文化”。
在人類已經進入的“后工業文明”即“生態文明時代”,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和論生生之美”在內的各種哲學和美學思想發揮出了彌補工業革命科技文化弊端的重要作用。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來研究一種會通中西生態美學的話語,是一種對于工業革命時代物質之美的超越。
四、結語
后現代視野下,人類進入生態文明新時代,曾繁仁所著《中西對話中的生態美學》,抓住生態美學的界定,內涵,研究意義以及中西方生態美學哲學觀念的轉變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立足于當代存在哲學以及現象學方法,將生態、審美與人加一統一。是一種包含著人與自然,社會,自身以及生態審美維度的當代存在審美觀,是國內生態美學發展的根本標志。
參考文獻:
[1]曾繁仁.中西對話中的生態美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曾繁仁.生態美學:后現代語境下嶄新的生態存在論美學觀[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03):5-16.
[3]曾繁仁.當代生態美學觀的基本范疇[J].文藝研究,2007(04):15-22+174.
[4]曾繁仁.試論當代存在論美學觀[J].文學評論,2003(3):57-68.
作者簡介:周揚清,陜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