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中國學者講述“平成”3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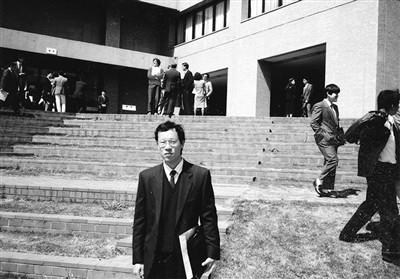

編者的話:日本德仁天皇的即位典禮將于10月22日舉行。30年前,明仁天皇1989年即位時日本年號由“昭和”轉為“平成”,也就是這一年,《環球時報》特約記者、旅日學者岳光當時作為留學生來到“后工業化”的日本,開始他的“平成”之旅。如何評價這30年的日本以及中日之間的變化?在岳光看來,這是見仁見智的話題,他表示,作為留日的“歪果仁”,并“斗膽”自認為是“平成時代”的一個見證人,概括起來就是——這30年日本去掉了頭上的光環由虛向實,而中國正放下心里的包袱全面奮進,中日彼此更加近距離觀察和感受對方的時代已經開啟。
從《日本名列第一》到“第二次戰敗”
我是1979級的大學生,專業是企業管理。當課堂上初次聽到松下、東芝等日本企業及其先進的管理經驗時,真的像打開了一扇天窗。當時美國學者傅高義在《日本名列第一——對美國的教訓》一書中說,日本正在創造“后工業化”社會的樣板。彼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而日本卻進入“后工業化”,這無疑加深了我對日本的好奇心,有了找機會去日本“見識見識”的念頭。
1989年10月19日,當我推著行李箱走出日本成田國際機場大樓時,感覺眼前的現代化建筑和北京的首都機場航站樓隔著一個時代。我操著看得懂、能表達、聽不懂的“單行日語”乘坐機場巴士,從千葉縣向東京進發。一路上一片田園風光,進入市區后,巴士在上下三層的高架路上疾駛,樓群密集得像竹林一樣,樓宇間小汽車川流不息,好像流淌的血液……當時就想:“真是沒有不先進的,日本‘后工業化的感覺原來是這樣的!”
實際生活中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商品的豐富程度:便利店星羅棋布,還有24小時營業的,這是第一次見到。日本人的生活可以持續到深夜。對于初來乍到的留學生來講,晚上去便利店買東西,成為排遣寂寞的方式之一。大型超市商品琳瑯滿目,“沒有買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歐美的進口商品竟然比日本產的還便宜。記得我當時在一家超市里專門找有沒有中國商品,結果只發現三種:天津甘栗、遮陽葦簾、棉布汗衫。
當時來日本的中國人還比較少,我在街上吃的第一頓飯是“廣東面”,店主是位老華僑,他問我:“是來打工的嗎?”我說是留學后,他就不做聲了,但過了會兒用筷子給我添了一大塊叉燒肉。遺憾的是,此后30年,都沒有再去過這家面館,不知道老先生后來如何。
我在日本讀的是經營科學碩士,按規定2年后畢業時需修滿30個學分,但我總計修了45個學分。我的想法很單純,就是學得越多才能越接近于了解日本。當時的日本經濟正處于鼎盛期,日本的目標是和美國“平起平坐”。1989年底的一天,日本各大媒體登出一條驚人的消息:三菱地產公司收購紐約的地標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我問研究室的日本同學怎么看這件事,對方無不自豪地說:“我認為日本在經濟上已打敗美國。”我只能暗自著急,心說:“日本果然爭到第一了,那中國就差得太遠了。”
數字最能說明問題。1989年,中國和日本的GDP分別為3400多億美元和3萬億美元,說明那段時期人家經濟搞得比你好,因此日本“變大”了。這也讓日本的“眼光”更高了。我平時喜歡逛書店,這里比在課堂上更能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想法。那些年,日本右翼學者有關“中國崩潰論”的書很暢銷,整個上世紀90年代這種論調都很有市場。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僵化的制度,抑制人的創造力,因此經濟最終必然破產,蘇聯就是樣板”。我和日本人交流時,話題多是對日本新鮮事物的了解,其實內心里還是生怕中國落后于對方。
1978年,鄧小平訪日期間在乘坐新干線時說:“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記得我第一次坐“子彈頭列車”新干線是1994年底,是就職后從東京到靜岡縣出差的路上。我當時盼著這次出差,就是想體驗一下這樣的速度和現代化。
恰恰是1994年前后,中日兩國都發生了深刻的大事件。日本這邊是經濟泡沫破裂,日經指數從最高的40000點跳崖,此后一路下滑。我認識的一位知名的日本金融學教授,他的講座每次都爆滿,但他的股票也被套了,最后不得不割肉逃出。因一曲《北國之春》而聲名大噪的日本歌手千昌夫,80年代后期搞房地產,被稱為“歌唱的不動產王”,可惜后來負債額達1000億日元。他申請破產后,往日光彩不再,只能每日躬身賣藝,還債度日。到90年代中期,經濟衰退導致地產業不景氣,三菱地產1996年不得不賣掉洛克菲勒中心。日本學界和媒體開始討論“零增長”問題,這個提法頗具政治殺傷力,評論家堺屋太一說,從高速增長一下滑落到“零增長”,世界上絕無僅有,這就是日本的“第二次戰敗”。
回看中國,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在國內外產生巨大影響,激起國人的奮發熱情。我們意識到,其實中國的問題就出在自己身上,發展速度慢的根本原因是思想包袱太重,遇事先將方案考慮周全,然后再去實際操作,這個想法是沒錯的,但問題是態勢變化不等人,你想要一個周全的方案,但這個方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可以說,那一段時間,日本和中國的決策層都面臨同樣處境,解決問題的區別是更看重哪頭:是抓機遇,還是避風險?
日本“變小”,中國變大
地產泡沫破裂后,日本的麻煩接連不斷,但日本普遍采取的是“保守治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日本經濟出現衰退跡象,銀行加大業務收縮速度,客戶的業務中凡沒有短期內盈利的項目一律砍掉。以我當時所在的一家日本公司為例,社長一開始是鼓勵我獨立開拓中國業務,向日本企業和研究機關、政府部門提供有關中國經濟動態的分析報告。這是一個每期16頁的月刊,名字叫《FORECAST(預測)》,是日本國內第一個由企業投資,卻站在第三方立場分析中國動態的出版物。經過幾年努力,該企業初步建立信譽,客戶主動找來談業務合作,項目好不容易由“零”發展到盈虧平衡,但經濟衰退后,該項目因“沒有盈利可能”要被叫停。社長不忍心但又很無奈,《FORE?CAST》只出到1998年底。
相反,中國企業的改革卻是“大刀闊斧”。1996年到1997年期間,我參加了一個中日政府合作項目,利用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的資金,為國內某省編制長期發展規劃提供政策評估和項目支持調研,我作為翻譯及協調員和日本專家一道深入企業調研。當時接觸的地方政府官員、企業負責人和員工都對大膽改革持理解態度,對未來抱以期待。日方專家在私下討論中也感嘆,在日本已感覺不到變革的勇氣。
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都頑強地扛住了,并且抓住加入WTO、舉辦北京奧運會等大好時機,實現連續高速經濟增長,進而吸引更多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理念。到2018年,中國經濟總量為13.6萬億美元,而日本為5萬億美元,日本又“變小”了。
中國不僅變大,也變“快”了,特別是在能源供給、互聯互通、交通運輸領域形成世界最大社會基礎設施網。中國高速鐵路2008年才開通,比日本晚了40年。2008年我帶日本客人到天津考察,初次坐上自己的城際高鐵,舒適和快的感覺就是“理所當然”。只10年的時間,中國高鐵里程已長達3萬公里,超過世界高鐵總里程的2/3。信息和交通的革命性變革,改變了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地理概念。一旦中國人的觀念改變,奇跡必將發生。
從“日本經驗”到“中國道理”
所謂日本“變小”當然是相對的,它的工業和科研實力依然擺在那里,比如日本諾貝爾科學類獎得主已接近30人,中國目前只有屠呦呦一人。那么,中國是否要把超過日本人的諾獎數量當成一個目標呢?我現在不這樣想了。中國的問題永遠比日本多,甚至比美國多,而且更復雜。因為中國是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這個現實決定中國在本質上不同于其他國家。所以,以他國為目標進行追趕,不是自己的出路。現在網絡上經常看到“善意”的提醒,比如說“你的手機中有大量日本元器件,說明技術上日本依然遠比中國強”之類的,這說明他們不了解現實中國的課題,只是將某項技術超越對手視為成就,這就叫“以物累心”。我前年參觀東芝公司時,日本企業負責人說:“我們用的葉片毛坯是江蘇一家民營企業生產的。我們離不開中國企業。現在華為、中車以及中國的大飛機制造企業都在走系統集成這條路,說明中國企業并不落后。”
這些年,工作之余,我總要抽時間到仙臺的魯迅紀念碑看看,靜靜地在魯迅雕像旁的石頭上坐一會,有時心里會有一些糾結:“魯迅當年留學的課題是救亡,他后來找到了目標。而我留學的課題是學知識,現在知識有了,但知識依然是外在的,判斷的標準依然在別人那里,如果這樣下去的話,豈不是白來一趟?”從一個日本朋友的言談中我找到答案。他曾是國會議員的秘書,經常到中國出差,他和我多次談及自己的觀點:“中國政治安定,定下來的事情立刻就做,所以能成大事。而日本前些年首相換的太頻繁,根本沒有穩定的經濟政策出臺,這樣下去日本就完了。”
為什么日本人的抱怨多了起來?我認為,兩相對比,中國的做法是日本人沒有經歷過的,是新鮮事物,這就意味著中國在向世界展示不同的發展路徑。如果能將這一過程的細節把握好,并適當調整,最后將其歸納在一起,這不也是學問嗎?確實,自從我這樣思考問題以后,眼前的“日本經驗”似乎不再那么深奧,可取可舍任我自由。
最近幾年,日本媒體頻繁出現馬云、任正非、李書福等中國新一代企業家的名字,他們的故事在普通日本人心中激起波瀾。一個61歲的日本網民在看了介紹阿里巴巴等中國企業的報道后認為“美國夢已經結束”,并留言說:“這樣的中國企業會不斷出現,今天的世界,每個人都有機會,只要不斷地去嘗試,眼前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當年像我一樣的中國人到日本來長見識,而現在,世界又反過來研究中國的經驗,這說明一個事實,只要自己的立場和方法得當,就會加速發展。當然,學習他國的經驗依然重要。
“生涯現役”,日本的無奈
30年的“平成時代”,日本也在不停地自我調整。傅高義當年書中提到的日本“后工業化社會”特征,其實是在老齡、少子化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近來日本媒體上出現“生涯現役”的提法,意思是“活到老,干到老”,這恐怕是無奈之舉。此外,通過促進消費維持再生產,也是日本的當務之急。2050年前后,日本的人口估計要減少到明治時代的水平。地方的經濟活力會被東京、大阪這樣的超大城市吸收,年輕人可以來大城市,但高工資會被高房價抵消。如何應對各種危機,對日本人來說,也是考驗。應該強調的是,日本的法律制度比較完善,文化、技術上的優勢尚存。
當我結束30年“平成之旅”,回國前和日本朋友告別時,他們很不舍,但也為我的選擇感到高興。有日本朋友說:“認識岳桑后,我改變了對中國人的看法。”在名古屋大學,我還見到當年讀研的中國同學,談話中感覺他們依然非常努力,成績也很不錯,這又讓我想起自己的留學生時代。我很欣慰,我們這一代“見識日本”和“對比中日”的課題已完成,而新留學生們將肩負未來30年的課題。今天,中國又邁上一個大臺階,在日發展的中國人今后的出路肯定也更加寬闊。▲
(作者為旅日學者)
環球時報2019-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