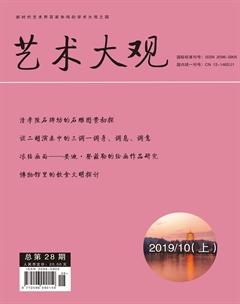淺談山水畫寫生
摘要:自然中,不同的物種在自然法則及其自身生長規律的作用下共同生成了一個既“和而不同”卻又“對立統一”的美妙客觀世界,山水畫的“寫生創作”中自然離不開對物像的吸取與借鑒。自然物像與色彩本身無有思想性,而繪畫者是有思想性的,無思想的對象經過繪畫者的眼和腦,自然便有其思想性。寫生是由眼中之景到心中之情,由情至境,再將境寄托于手中之筆構建畫面的過程。在寫生時要保持興奮狀態,心態沉穩,不急躁,最后呈現的畫面也是自己內心心態的再現。
關鍵詞:山水畫;寫生;自然
宗炳《畫山水序》中講:“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繪畫者為了胸中的丘壑、必須親臨自然、感同身受。認知萬物的結構,了解生長規律,洞悉生命延續的關系,這是繪畫者寫生山水的前提。我們也是在“臨摹,寫生,創作”三位一體的教學體系中,把寫生作為一個環節,重要的是在寫生中對物象忠誠,強調取舍和概括,不尾隨于物象,整體把握,經營畫面。
一、對景寫生
寫生中,最常用的是張仃先生倡導的“對景寫生”。要求繪畫者必須用心觀察并對自然變化有瞬間感知的能力,將情感依附于筆墨,再寫于作品,這樣才能使作品賦有生命力感染力的同時更加個性化,具有獨特的繪畫特點,不千篇一律。寫生最大的問題就是用臨摹過的模本看自然,依附傳統技法寫生,畫面缺失個人情感,個性化的表現與研究。從概念化到程式化,不斷地進行著簡單的重復。 寫生中,景物相同,但個人對自然感知度不同,反映在畫面上也會不相同。想要找尋突破,求得豐富發展,就要對自然物象進行選取,解構,重組,形成一套成熟的繪畫語言。一切來源于對自然的寫生,在似與不似之間仔細揣摩,回味。
“與山對望,心與神游,神遇而跡化”,寫生創作中與自然相交,意理結合,將眼中的自然物象變成符合藝術規律的筆墨語言,窮盡變化,以筆傳情,壯物寫心。自我感情經歷豐富的人,更能一往情深,對寫生的對象有深切的感受,才能把寫生變成思考,深入理解寫生的表意與外延,以獨特的筆墨方式,語言形式,詮釋大自然神秘的生發之道。在教學過程中,高密度扎堆寫生,是十分有效的。學習者能深切感受到教師治藝的嚴謹。也深刻牢記,對景創作要強化感受,賦萬物以情感、以生命,一樹一石,一路一坡,皆要深察其態其情,并學會以畫筆表現這種感受。至于客觀對象如何進入畫面,如何表現,完全在于繪畫者。結構、造型、物象與平時繪畫臨摹,創作習慣決定了繪畫者的風格,營造出來的畫面。
二、我用我法
古人說“我用我法”“出新意與法度之中”,這是繪畫者要做的,要提高自身的修為,需長期積累與實踐。做到什么程度,畫也會畫到什么境地,寫生是一個關鍵的契機,這個契機,可以對臨摹有一個總結。講評作品,繪畫者挖空心思去畫面中找問題找解決辦法,最后呈現出來的畫面雖然有些問題依然存在,簡單的問題重復犯,但每次通過再收拾再修改逐漸的完整畫面,也是對繪畫者成長的一個提升,對藝術的提升,對畫面整體感處理辦法的提升。這個提升不僅僅是繪畫也是自我智慧自我認識的甚至是自我對人生對生命價值的一個提升。
畫不是簡單的一個物,畫如其人,你是什么樣的人就畫什么樣的畫,那怎么體現一點一筆一墨中的感受,那種流淌出來的氣質。古人說畫先觀氣象,氣象就是在一筆一墨中積累出來的。這個氣象就直接對應創作者的氣質生命力量,我有什么樣的生命氣質什么樣的感悟,那我就畫什么樣的畫,甚至于一點一畫,一個線段也是“我”的體現。通過寫生,是一個促進,是一個強硬的提升,同行者都在提升成長,在這個環境中,教師教著改,同學推著走,看到優秀的作品,看到自己的畫面,那怎么去做我自己,怎么把我的認識,我的理解,甚至于我的表現能力能夠再往前推進一步,寫生就是一個很好的環節,一個橋梁的作用,大家在一個地方,全身心地做一件事,摒棄雜念,不受干擾,各方面能力、潛能能夠凝聚起來,調動起來,并且通過寫生作品展現出來。
三、藝術來源于生活
對于寫生這種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完全挖掘繪畫者創作潛能的狀態要在繪畫中一直延續下去,到創作中,到未來的道路中,時刻以這種狀態面對生活,帶有主體創造性的寫生方式可以打破某種限制,不單是客觀地將景物再現,更多的是挖掘繪畫者獨特的認識與對景感受,為繪畫者心中的物象塑造出內在的本質內涵。
山水畫創作是以生活體驗為基礎的,是對現實與社會生活的某種反映,是將對生活的感受提煉為藝術意象,并在作品中得到物化。寫生作為繪畫創作的基礎,最大特定就是它的直觀性,是對客觀對象鮮活的、生動的描繪,它的表現方式往往率真而直接,可以培養繪畫者獨特的感受力,最為直接地鍛煉繪畫技巧,積累審美經驗與豐富的藝術表現力。
作者簡介:李振霞(1994.8.4),女,漢族,籍貫河南濮陽,碩士學位,鄭州大學美術學院18級在讀研究生,專業為美術學,研究方向為中國畫山水藝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