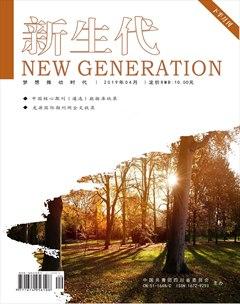針對當今“曹魏服飾研究”斷代的思辨
【摘要】:至今為止,學界對中華服飾的研究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就目前曹魏服飾的研究而言,這方面的成果仍相對空白,學者們通常將曹魏服飾研究統歸于 “漢魏服飾”或者“魏晉南北朝服飾”當中。但是,這種包羅萬象的概括方法需要反思與詰問,東漢服飾如何逐步產生變化的?西晉的服飾風格是如何開啟的?在這個鏈接關系上曹魏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所以,針對曹魏時期服飾文化的斷代現象,給予進一步關注和研究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曹魏 服飾 斷代 思辨
在歷史過程上,曹魏時期是上承東漢下啟西晉的過渡時期。自東漢末年到晉南北朝,中國經歷了長期的分裂割據與連綿不絕的戰爭,社會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不同的文化思想在歷史中川流交錯、分分和和,政權的更迭也異常頻繁,短短三百六十余年間,三十多個王朝交替興滅,而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到咸熙二年(公元265年)的曹魏,正是這段時期內更迭的第一個政權體系,雖然時間非常短暫,但它最直接的承接了漢代末流的文明,又是后世轉折的始端,縱觀中國歷史,晉南北朝的許多思想觀念、政治制度、文學風格等的變化都奠基于曹魏時期,它是對中國文明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服飾文明上,從東漢到晉南北朝的服飾風格產生了諸多變化。晉南北朝一改漢代的端莊禮儀之風,呈現出一派自然放曠的服飾景象,人們不再以漢代嚴謹的服飾傳統為美,而是愈加瀟灑飄逸,男子袒胸露臂、披發跣足,女子雜裾垂髾、褒衣博帶,近年來出土的文物和墓室壁畫,對東漢和晉南北朝的服飾面貌提供了大量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完全不同的服飾風尚,漢代的袍服在晉南北朝時變的越來越寬松;深衣的下擺裁成數個層層相疊、上寬下尖似旌旗的三角形,并在下擺周圍點綴飄帶;襦相較于漢代逐漸變短,衣身變的細瘦,衣袖變的細窄,袒露小部分胸部及頸部,腰部外束絲帶。裙子呈現上儉下豐的喇叭形,裙腰逐漸升高、裙幅和褶裥增加,下擺的長度拖曳在地,整體風格上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與漢代大相徑庭。
然而,由于曹魏的喪葬采取“薄葬”制度,不封不樹、斂以時服、不設明器,致使考古學家所發掘的墓葬十分有限,墓葬出土物也多簡陋、粗糙,無法全面看到當時的服飾面貌,在曹魏的相關史料當中,也沒有明確說明當時的服飾制度。基于這種現實情況,學者們通常認為曹魏時期的服飾與漢代沒有什么變化,常常將曹魏統歸于漢代或者晉南北朝當中。然而,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有載:“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后”,服飾亦如此。我們必須了解,中華服飾文明之所以走向成熟,是由每個歷史時期連綿不斷的貫通而建立起的根系,從漢代到晉南北朝的服飾風格轉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
一、單一的學科無法洞察服飾文化的本質
針對當今曹魏服飾研究斷代的現狀,在研究方法上是存在誤差的,單一的學科無法洞察服飾文化的本質。在現今對學科進行專門性精確分類的潮流中,導致了學術研究者對服飾文化全面性理解上的分歧和迷惑,可以說,這種情況的出現,并沒有真正的促使學科的進步性。例如服飾研究與文獻、考古、哲學、歷史、地理、政治等相關學科,當今已精確分類,而古時實際上是一個整體系統。從“二十五史”中的《輿服制》我們就可以看出,該服飾系統并不是完全獨立存在的學科,而是正史中的一部分,是多元歷史的承載體,是人類意識的反映,亦可以說是對中華文化認知的研究工具。反觀現今學科精細區分的潮流,使得服飾問題的研究只能在專業范圍內加以論證,而無法結合服飾問題背后的意義剖析其演變的內在成因。換言之,服飾文化歷經一代又一代的人們能夠發展到現今,最關鍵的是其背后的意義給予的推動,但這顯然是單一學科沒有辦法準確解決的,只有結合學科交叉的知識和研究方法,才能通過探究得到更全面的研究成果。
二、文獻全面調查下的比較解讀法
在傳統的服飾研究方法中,對文獻調查的解讀大抵是從兩種角度進行展開。其一,通過對古代的相關文獻資料進行調查,搜集更準確、更安全的信息支持,實現對圖像支撐的理論依據;其二,立足當代中外的相關文獻研究成果上予以對照,更具象的獲取今人之認識和總結。這兩種角度超越了時空限制,已經給予我們對服飾文化的大概了解,且在一定程度下奠基、反映史實。然而,這種樸素的手段若僅僅集中在“服飾”領域進行探討是否足以真實呈現歷史的原貌?是否能夠客觀的“去偽存真”?近年來的學科發展,已指出另一條途徑。
在中華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文獻的記錄和思辨都不是憑空而來的,所有的文獻不僅是反應歷史的一把“鑰匙”,也在不同的境遇、不同的角度下相應帶有人們的主觀色彩。例如由西晉史學家陳壽所著的《三國志》,雖然記載嚴謹、取材精審,但因“晉”承“曹魏”而得天下,所以不免對“漢魏”之間的關系稍微有所隱諱,若以《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等與《三國志》進行相互比較,也可見其文獻對政治當權人物的記敘也存在曲筆回護,當然,作者處于特定歷史環境當中,對于改朝換代等實際背景的顧忌是可以理解的。再如南朝宋裴松之為《三國志》做注,引來了史學家楊翼驤、劉知幾、章學誠、陳寅恪、周一良等或褒或貶意見不一的多重評議。
由此可見,“歷史概念”在經由不同時期的演化及不同研究的視角當中,最后又成為相對的“歷史盲區”,這代表了對文獻解讀單一化的、縱向的梳理并不能客觀的展現歷史原貌,這一類“歷史”通過不同的語法表達事件,而不同語法的角度又表達了主觀觀念和理想,總有過程是個“迷”。所以,對研究內容全面的、橫向的比較研究,結合古今不同文獻的相同和差異,可有助于在數據池的研究當中,避免受到文獻主觀意識和思想盲區的制約,也可以得以重新思考曹魏時期服飾文化的“樣”與“態”。
三、 墓葬出土物的形象對照
相對文獻調查法來說,墓葬出土的實物遺存能給學術研究者們提供更直觀的、一手的形象資料,因為這是古代社會人類活動中所存在的最實際的、有形的依據。但是,礙于許多現實因素,墓葬出土物的形象和文化內涵很難解讀,尤其是曹魏時期盛行“薄葬”之風,不僅墓葬發掘較少,出土的器物往往也只是簡陋的、散亂的壁畫、殘片等,可以探究的服飾形象少之又少,那么,如何依靠這些稀少的資料去研究該時期的服飾問題呢?筆者認為,將出土的石刻形象、壁畫、器物與上文提及的文獻調查進行對照,在曹魏服飾研究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價值。
在這個研究方法中,需要厘清幾個概念。其一,通過對《考古》、《考古學報》、《文物》、《考古與文物》、《文物參考資料》等書籍中相關曹魏內容的整理,可以對其遺址方位進行總結,在地理上可推論其來源和使用的大致區域范圍;其二,通過在文獻描寫、博物館資料中的出土物進行分析,可以了解其形態端倪;其三,將史料記載中的社會狀態、人文理想、生活目標與出土資料進行對照,從而可分辨兩者的同異關系。
進一步來說,若僅從史料文獻中進行考究,則曹魏服飾審美不足以直觀,若僅從墓葬出土物來加以研究,則不能對曹魏的社會生活進行復原。自東漢末年開始,曹魏對喪葬的處理方式,地理位置的選擇以及放置的器物給予的明確的規定,如“古之葬者,必居于瘠薄之地”、“無藏金玉珍寶”等,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將墓葬出土物與東漢、西晉的服飾面貌進行對照,與不同的史料文獻進行相互對照,方能更細膩、更精確的得出結論。
四、 在此之外的研究范疇
除了以上的研究線路以外,還需要了解曹魏時期社會的階層結構、社會活動、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核心、士大家族之間的關系、時空范圍下人們的精神信仰、人們的生活理想、各學派的價值觀等問題,因為服飾審美風格的演變就是在這些相關聯的現象中衍生的,換言之,這些關聯內容的變化,影響到服飾審美風格演變的脈絡。如果僅僅局部的關注服飾文化,是無法觸碰曹魏服使研究得本質的,也無法深究服飾文明從“無”到“有”所存在的本質意義,且會造成不同角度之間的矛盾。
綜上所述,曹魏服飾研究與當時的歷史、政治、宗教背景無法分離,也與思潮、審美風格等相互聯系,若僅僅從局部入手,何以將之匯入服飾文化發展的歷史當中?而諸多學者對曹魏這一時期的其它方面早已探討,針對于服飾研究的“斷代”現象,實際上更多的是研究視角及研究方法上的固步自封。單一的學科無法達到洞察服飾文化本質的目的,學術研究者們應關注從學科交叉的角度出發,對多重論據進行縱橫參照,結合不同領域的觀點和多元研究方法進行綜合論述,從而將服飾與其它學科置于互相關聯的學術領域當中全面關照。
【參考文獻】:
【1】(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版。
【2】(宋)范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8月版。
【3】孫機,《中國古輿服論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4】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5】宗白華,《美從何處尋》,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6】宿白,《三國兩晉南北朝考古》,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
作者簡介:姓名:楊舒婷,性別:女 民族:漢 出生年月:1987年10月,學歷:博士在讀研究方向:服裝藝術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