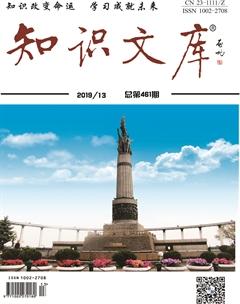山西省家庭結構變化的地域差異及原因分析
張婧
立足于人口地理學及社會學理論,運用山西六普數據,采用數理統計法、地圖法等,利用SPSS、GIS軟件,對山西11個地市家庭結構的地域差異及原因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隨著山西省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家庭規模或類型發生了明顯變化。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有自然地理和社會經濟因素。
正確揭示家庭結構地域差異規律,對理清家庭結構變化與自然環境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相互關系,制定科學合理的人口及經濟發展對策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1 山西家庭結構變化及地域差異
1.1 家庭規模變化及地域差異
家庭規模指每戶家庭包括的人口數。從數量上看,2005年家庭規模最大的臨汾,最小的太原;2010年家庭規模最大的是運城,太原還是最小。綜合五普和六普數據發現,晉北的朔州的家庭規模高于全省戶均人口;晉中的3個地市家庭規模遠少于全省戶均人口;晉南家庭規模較大,除晉城外,臨汾、運城、長治都比全省大。從動態上看,各地市2010年家庭規模降低,呂梁地區降幅最大,太原、晉城、大同、臨汾、和朔州也大幅下降,但運城、長治降幅卻低于全省平均降幅。
1.2 家庭類型變化及地域差異
家庭類型結構指家庭成員的構成。山西一代戶的比重都有所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太原市,最小的是運城市。通過SPSS軟件的層次聚類分析,各地區顯示出明顯的地緣組合規律。太原自成一類,代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大同、朔州和呂梁為一組;晉中、忻州和陽泉為一組;臨汾、晉城、長治為一組;運城的家庭結構較為獨特,另成一組。
2 造成山西家庭結構地域差異的原因
2.1 城鎮化發展不平衡是重要原因
2010年太原城鎮化率高達82.5%,陽泉達到60%,家庭規模小,一代戶比重大。城鎮化率最低的是呂梁和運城,家庭規模大。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大批青年人到城市就業,農村“養兒防老”“多生貴子”的觀念弱化,這部分人建立起獨立的小家庭,“不再需要親屬關系,越變越小,富有流動性,越來越適應新技術領域的需要”。
2.2 產業結構是深層原因
從事農業的家庭需較多的勞動力,趨于生育兩個或以上的孩子,加上要贍養喪失勞動力的父母,家庭規模較大。運城地勢平坦,氣候溫和,土壤肥沃,光照充足,農業生產條件優越。三代戶比重是全省最高,一代戶比重為全省最低。而第二、三產業比重較大的地區,人們靠工資生活,職位晉升靠個人能力,不再依賴家庭幫助。還要四處奔波尋找更好的職業市場。親屬關系逐漸松弛,脫離原來的親屬關系網,去建立夫妻共同生活的小家庭。
2.3 人均GDP是物質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年輕一代的觀念已發生改變,傳統的“養兒防老”逐漸淡化。2010年山西人均GDP值26385元,“貨幣防老”正慢慢替代“養兒防老”。人均GDP持續居高的太原家庭規模最小,一代戶比重最大;常年居中的陽泉、晉中、晉城次之;而臨汾、忻州、呂梁、運城的人均GDP久居低位,一代戶比重較小。
2.4 人口流動是部分原因
托達羅的預期收入理論認為,人口城市化可看作是人口流動的問題。當勞動力估計他在城市收益高于農村時,將會離開農村。其實是個人對高品質生活的追求,這也是社會經濟發展所導致的。按照山西省目前不斷增長的人口流動趨勢和非家庭化的人口流動模式,家庭部分成員的流動使完整家庭成為分離的家庭,使家庭結構發生變異。
2.5 生育率降低是直接原因
一方面生育觀念發生了變化,許多人減輕家庭負擔,提高生活水平,一代戶家庭比重上升。獨生子女成年后離家轉變為一代戶。另一方面是實行計劃生育的結果。70年代,像太原、大同已嚴格執行了計劃生育政策,而運城、臨汾、呂梁等小城鎮,很多夫婦依然生兩個,甚至三個孩子。
2.6 地理環境是制約因素
自然地理環境制約著當地居民文化水平及思想觀念的變化。在山西中部的汾河平原地區,交通發達,電子網絡密集,信息通暢。人們易于接受新思想、新觀念,與社會發展的主流意識接軌。而東、西兩側的山區,交通閉塞,科學文化技術發展緩慢,較難接受到新的思想觀念,甚至當地居民沒有發現和傳播新思想的欲望,這就阻礙了人們的思想發展。
3 結論
目前山西的家庭規模以二代戶為主流;一代戶和一人戶有較大增加;三代戶家庭比重降低,四代戶家庭在一些地區已經不存在。全省11個地市家庭結構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受自然地理和社會經濟因素綜合影響,后者占重要地位。平原、城鎮化率較高、第二三產業比例大、人均GDP高以及人口流動規模大、生育率低的地區呈現家庭規模小,一代戶比重較大的普遍特征。
(作者單位:忻州市第一中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