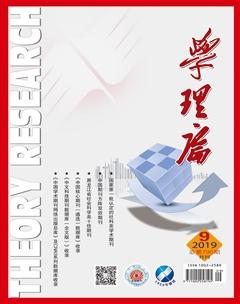人類文明構建的兩種向度
于晴 邵鵬
摘 要:從歷史哲學的視角,唯物史觀和文明形態史觀這兩種解釋、構建人類文明的宏偉敘事,在理論上具有諸多相近之處。然而,這兩種理論在本質上存在著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思想的截然對立,在一些具體觀點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著極大的不同。因此,比較兩者的理論異同,對于社會主義文明形態的構建具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文明形態史觀;唯物史觀;人類文明;歷史哲學;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B0-0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09-0059-02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文明形態史觀逐漸興起,對于唯物史觀的解釋框架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認識文明形態史觀的理論實質,才能夠更加深刻理解唯物史觀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一、文明形態史觀的實質及其影響
文化抑或文明究竟是什么?古往今來眾說紛紜,各種理論層出不窮。20世紀文明理論中影響最大的當屬“文明形態史觀”。作為思辨歷史哲學的集大成者,文明形態史觀肇端于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成熟于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他們從文明的角度來解釋人類歷史的發展演變,試圖尋找到文明演變背后的規律性,理論研究的“興趣不在個別的具體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圖案。”[1]172
文明形態史觀以文化或文明作為歷史研究的最基本單位,從形態學的立場出發,采用學科交叉比較的方法對歷史進行綜合研究。斯賓格勒通過對比考察埃及、印度、希臘、阿拉伯、中國和西方等八種文化以后,得出的關于文化興盛衰亡的一般性規律,這實際上一種對于傳統史學研究“歷史性”方法的反動,強調文化形態的“同時性”。湯因比更是將文明比較的范圍擴大到二十七個之多,通過各個文明的比較尋求它們之間的異同、發展特點及發展趨勢,試圖“打破我們自己國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們短暫的歷史所造成的束縛。”[2]136
學者的思想反映的是其所處時代的狀況和意識的顯現。20世紀初,西方社會的深刻轉型帶來了文化焦慮和文化危機。斯賓格勒的憂患意識正是被此激發的,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對西方文明產生了悲觀的預言,也突破了近代史學研究傳統民族國家的理論框架。而湯因比則不甘心西方文明的宿命,從而對西方文明進行了更為深刻的透視和反思,構建了一套卓然不群的理論體系。正是對西方文明危機的解答使文明形態史觀超越了純粹的學術研究范疇,在思想界甚至社會領域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至于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文明沖突論”等也是立足于對西方文明本身存在問題的反省。
二、唯物史觀的實質及其文明理論
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哲學,它只是遵循唯物主義哲學的基本原則觀察和理解歷史的結果”[3]23。馬克思恩格斯把文明史放在物質大自然和人類歷史的宏觀大背景上進行考察,從而找到了人類文明與進步具有其物質本源性。“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4]92同時,文明體是與社會形態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總體性概念,每一個文明體的結構層次均包括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在文明由低到高的順序發展過程中,不同的文明都有著自身存在的特殊生態環境及獨特的內容和形式。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產生之后,各種文明之間發生了交匯,對人類文明進程產生重大的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文明論更為重要的特質是,將道德批判和人文精神訴求最終落實到對現實關系的改造上,批判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形態的異化,指出向公有制社會邁進,這是文明發展的必然方向和未來模式,此時人與自然的關系也真正實現了和解,從而走出了“人類中心主義”。“這種共產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5]81
三、唯物史觀與文明形態史觀的共同之處
(一)人道主義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對人類文明史考察的最終目的是,在遵循歷史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不斷揚棄資本主義文明形態中人的“異化”現象,建構更為完善的共產主義文明,從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最終目標。他們在繼承黑格爾等人道主義思想因素的基礎上,立足于唯物史觀把人道主義的實現與制度分析結合起來,從而尋求到解決非人道主義現象的途徑。
文明形態史觀努力賦予歷史研究的人文主義價值和人道主義因素。對于斯賓格勒而言,頭等重要的問題是西方文明的命運,20世紀初期西方社會的危機致使他的歷史哲學帶有很強烈的悲觀主義色彩。湯因比則不甘心于屈服西方文明衰亡的命運,從而去尋求解決西方文明危機的理論。湯因比晚年視野更為恢宏,思考的重點是全人類的命運問題,他對全球性問題考察的落腳點是為了拯救人類的整體危機和困境。但此時他卻對宗教作用過于強調,仍然立足的是唯心主義的思辨歷史哲學。
(二)超越民族國家的宏偉敘事
唯物史觀闡釋的是人類歷史及文明起源、生長和發展的總體形態,“五種社會形態”和“三大社會形態”理論均是如此。“世界歷史”理論更是立足于全球的視角來考察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對人類其他文明社會形態的影響,并把重大社會歷史事件真正放置于世界歷史的整體過程中來考察,從而全面地揭示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及方向。正是這個邏輯前提,唯物史觀拒斥了“西方中心論”。
文明形態史觀批判的直接目標之一,就是當時歐洲普遍流行的“西方中心論”。斯賓格勒提出了令西方世界震撼的“西方沒落”的預言,對“歐洲文明中心論”的前途充滿了不祥的預感和恐懼。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把世界上的各種文明都是視為“平行”的,在價值上是平等的,這也是源自考察人類歷史發展的全球視角以及長的時間觀念。湯因比晚年更加反對“西方文明統一論”,指出人類文明的未來,“這個主軸不在美國、歐洲和蘇聯,而是在東亞。”[6]294
(三)文明比較的研究方法
馬克思恩格斯通過比較對照人類的文明時代與其他時代的特點,揭示找到不同國家、民族和地區文明狀態的同中之異和異中之同,不僅將處在同一形態的文明的一般屬性與特殊屬性,而且將外在表現形式類似的文明與其實質內容進行比較對照。馬克思晚年通過對東方社會的文明歷史環境和文化傳統的研究,提出了東方社會有可能走不同于西歐資本主義特殊道路的著名論斷。恩格斯把《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明確定位為“文明時代的批判”。
文明形態史觀廣泛地應用了比較文明的研究方法。斯賓格勒的所謂歷史形態學,就是通過對比考察埃及、印度、希臘、阿拉伯、中國、西方等眾多的文化世界以后,得出的關于文化興盛衰亡的一般性規律,這是一種對于傳統史學研究“歷史性”方法的反動,強調文化形態的“同時性”。湯因比更將文明比較的范圍擴大到二十多個,通過各個文明的比較,可以了解它們之間的異同、發展特點及發展趨勢。
四、唯物史觀與文明形態史觀的本質差異
(一)理論實質的根本不同
唯物史觀通過現實的社會運動來揭示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人類文明史是一個有著自身產生、發展規律的進程。馬克思用“實踐”范疇來闡釋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因,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等范疇,指出社會基本矛盾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決定著整個社會面貌及其發展的客觀趨勢。
文明形態史觀關于文明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諸多結論則缺乏對人類歷史物質動力的根本把握,帶有濃厚的唯心主義色彩。斯賓格勒把文化比擬成為有誕生、生長、成熟和衰落四個階段的生命有機體,這種方法早在古希臘的歷史學家那里就已經運用了,并非是具有現代性的。湯因比特別推崇這樣的直覺分析的方法,強調歷史研究中靈感的作用。他提出的“挑戰與應戰”法則來自神話中“上帝與魔鬼之間的挑戰與應戰”的啟示,是依靠“靈感”提出的比附方法。
(二)關于落實人道主義解決路徑的差異
馬克思恩格斯的人道主義思想因素是建立唯物史觀基礎之上的,是與科學理性結合在一起的,進行價值判斷的根據是事實判斷。他們不僅僅局限于對人的異化、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等社會現象進行道德譴責,而是把人道主義思想因素與社會制度分析結合在一起。因此,能夠找到共產主義這一實現人類解放的途徑。同時,馬恩也十分注重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的觀念變革,尤其是達到共產主義的文明階段就必須要破除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私有觀念”,才能夠真正實現人的自由解放。
文明形態史觀也對西方工業文明產生的異化等現象進行批判,但這種批判僅僅停留在道德層面上,并不具有真正的科學理性精神。斯賓格勒明確表示與英國式的理性主義斷裂,認為“歷史研究者同真正的科學的關系越是疏遠,他的歷史學反而越是出色”[7]154。湯因比仍然以人道主義的價值判斷指導事實判斷。他晚年借助于高級宗教來解決人類的全球困境問題,試圖重建宗教型價值觀。這無疑是歷史的退步,是向中世紀的回歸。
(三)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差異
在方法論的層面上,文明形態史觀的基本內容是文明過程論和文明比較論。前者旨在說明文明的內在性、獨立性和運動過程的規律性,后者則考察文明之間的聯系及其性質,目的在于構建一種總體的世界史觀。但馬克思在人類文明史的研究中的方法全面系統,運用了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系統研究、經濟分析、階級分析法和歷史比較等方法,在理論的深刻性上超越了純粹的文明比較法。
參考文獻:
[1][英]沃爾什.歷史哲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
[2][英]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張奎良.關于唯物史觀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概念辨析[J].哲學研究,2011(2).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英]湯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
[7][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