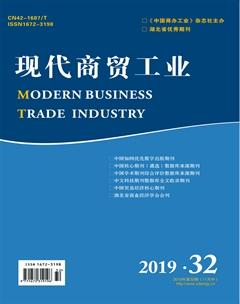“刑事伙伴”關系下犯罪人的刑事責任探究
李敏婷
摘 要:在“犯罪——被害”的過程中,我們往往更關注犯罪人的殘忍行為與危害結果,但卻忽略了被害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犯罪的發生離不開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相互“促進”,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形成了一種“刑事伙伴”的關系。在很多起案件中,被害人的反映、反抗激化了犯罪人的犯意,因此遭受了更為暴力的加害,甚至是二次加害。所以,探究了被害人在“犯罪——被害”過程中的作用與責任。
關鍵詞:刑事伙伴;被害人責任;刑事責任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2.070
本杰明·門德爾松用“刑事伙伴”一詞形容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絕大多數案件被害人對犯罪和被害的發生都負有一定責任。被害人在犯罪中的反映、配合、反抗等舉止也許就造成了被害的發生。我們可以理解為被害人被期望以理性合理的方式打消、至少不要激化犯罪人的犯意,但事實上,人永遠沒那么理性。在案件審判中,正確審視被害人在“犯罪——被害”過程中起的促進作用以及自身責任程度,對犯罪人的刑事責任有重大影響。
1 被害人過錯責任劃分
門德爾松將此劃分為六種類型:完全無罪的被害人、罪責較小或者疏忽的被害人、罪責同等或者自愿的被害人、罪責較大的被害人、罪責最大的被害人、偽裝或假象的被害人。
其中罪責較小被害人一般是由于自身的輕信、無知使犯罪人獲得加害機會,例如,在多數高校電信詐騙案件中,高校學生自身薄弱的防騙意識與信息保護意識,使得犯罪分子有機可乘。自愿被害人,是甘愿成為被害人或者過于相信犯罪人而落入犯罪人圈套的人。罪責較大的被害人,是指自己先行行為誘發加害行為或者因疏忽具有重大過失導致受侵害的被害人,如交通肇事案件中負主要責任的被害人。罪責最大的被害人,一般指攻擊性被害人,先動手攻擊他人,對方由于正當防衛予以反擊使加害人成了被害人,比如昆山龍哥案。這兩種類型中可能涉及“犯罪人”與“被害人”身份間的轉化。
2 被害人過錯責任的認定
被害人的責任與被害人的三大特性——被害性、互動性、可責性關系密切,“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犯罪人,每個人都是潛在的被害人”,被害人自身存在的致害因素往往導致被害人被加害人挑選為侵害的目標,當加害人著手實施侵害行為時,被害人的應激行為、反抗行為、配合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犯罪人的犯意。在犯罪前和在“犯罪——被害”過程當中,被害人與犯罪人始終是相互作用的,被害人促進了犯罪,而犯罪人又造成了被害人。將被害人自身的過錯視為酌定量刑情節,對降低犯罪人的刑事責任具有重要意義。當被害人具有應受譴責的責任,如疏忽大意、先行行為導致犯罪人的報復,亦或者被害人的主動挑釁、攻擊、辱罵等行為,毫無疑問可以降低犯罪人的刑事責任,以確保公正裁判。但是在有些犯罪中,被害人被盯上成為犯罪人侵犯的目標時他們呈現的是純粹,無辜的特性,但在被侵害的過程中,被害人的應激、反抗、配合等行為對被害的促進作用亦或是阻遏作用的情況下,應當如何認定被害人的責任呢?
比如我們將被害人的反抗行為看作是促進犯罪人犯意轉變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分為積極,一般,消極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指被害人的激烈反抗行為使犯罪人的最初犯意轉變成更大的犯意,往往給被害人帶來更危險的侵害。如遭到搶劫的被害人激烈反抗,謾罵犯罪人,致使犯罪人搶劫的犯意轉換成故意殺人的犯意。第二個層次是被害人基本配合犯罪人最初犯意,其過程可能是先抵抗后配合,致使犯罪人放棄二次加害或者二次加害犯意小于最初犯意,如遭受搶劫的被害人沒有過激的反抗,基本配合犯罪人實現搶劫犯意從而避免了被進一步侵害的可能。第三層次是被害人通過有選擇性的配合犯罪人的最初犯意,致使犯罪人犯意大大降低甚至放棄犯罪,如通過被害人同理心交流使犯罪人認為被害人與之境遇相同,最后放棄犯罪。
可是在上述情況下我們要如何認定被害人的責任呢?在暴力型犯罪以及其他侵害被害人人身權利的犯罪中,被害人完全不反抗是不可能的,也許會使他們更加順利得受害,但往往犯罪人的犯意又是受被害人的影響而提升的,社會上對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在犯罪中起的作用缺少理性地思考,簡單地將苛責于犯罪人或被害人一方,比如強奸案件發生后,有聲音會說是被害人穿著暴露,盡管這只是他們的一種偏見。很明顯,在純粹,無辜犯罪與被害過程中,犯罪人的惡性是極大的,被害人因反抗而受到犯罪人更惡劣地侵害,甚至致殘致死,但在社會上有聲音主張如果不是被害人自己失去理性怎么會惹怒犯罪人呢?但我認為不是每個人遇到違法的事情都能冷靜理性,法律也不能強人所難,誰愿意受到不法侵害呢?作為犯罪案件中生理和心理都受到巨大打擊的被害人,我們要從中尋找他們的過錯,力求對犯罪人準確定罪量刑,這是否就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呢?倘若這種類型的案件我們要對被害人的過錯責任進行認定又應當以什么標準進行認定呢?
3 被害人過錯責任在司法實踐中的現狀
在司法實踐中,被害人過錯行為、過錯責任作為酌定量刑情節常被提及,尤其是在暴力型犯罪中,律師常運用被害人的過錯責任作為辯護理由已是常態。但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對被害人過錯責任認定仍是處于認定標準不明,認定模糊現狀。
我國法律對被害人過錯責任相關規定主要體現在《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的決定》中規定的“對于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刑事審判工作的認定》中提到的“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案件,因被害人的過錯行為引起的案件,案發后真誠悔罪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案件具有酌定從輕情節的,應慎用死刑立即執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中提到的“對于被害人有過錯或者對矛盾激化負有責任的,應當綜合考慮案發的原因、被害人的過錯的程度或者責任的大小等情況確定從寬的幅度”。在以上的相關規定中,并無對“被害人過錯行為”有一個明確的劃定,且對被害人的過錯程度也沒有明確的區分標準,再者就是影響量刑的規定不明確,如《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中“被害人有重大過錯的,對被告人輕處30%;有一般過錯的,輕處10%”。
司法解釋涉及被害人過錯責任的規定有增多趨勢,不得不承認這對犯罪人的定罪量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首先是能保證對犯罪人準確的定罪量刑,合理分配雙方責任,確保公正裁判,這是法的正義價值追求的必然內容,然后可以推動對被害人在“犯罪——被害”過程中作用的研究,推進被害預防理論研究和實踐的發展。但在另一方面,對被害人過錯責任認定標準不明確、模糊雖然給了法官一定的裁量空間,但同時也令司法人員適用法律或司法解釋時猶豫不決,想用又怕適用錯誤,無從下手,且不同法院對被害人的過錯的情節認定不同,最后認定結果參差不齊。
4 “刑事伙伴”關系下被害人過錯與犯罪人刑事責任間的平衡對策
犯罪人與被害人幾乎是形影不離的關系,有時候也許是一個人的過錯行為導致另一個人犯意的萌芽,激化,其中包含著一種復雜的因果關系,最終產生了犯罪人與被害人。既然大部分案件里犯罪人與被害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過錯責任,那應該如何平衡被害人過錯與犯罪人刑事責任間的關系呢,關鍵在于完善“被害人過錯責任”在立法和司法中的實踐。一些學者主張將被害人過錯這一酌定量刑情節升格為法定量刑情節,如高銘暄,張杰在《刑法學視野中被害人問題探討》中提到“應當在立法上將‘被害人過錯可以減輕或者從輕犯罪人的刑罰這一酌定情節法定化,實際上,這也是限制死刑的需要”,劉麗萍在《論犯罪被害人的過錯》中認為被害人過錯應采取總則宏觀規定與分則具體罪名確定的模式,莊緒龍在《刑事被害人過錯責任細化研究》中主張按照被害人過錯責任的程度將被害人過錯劃分為完全責任、重大責任、一般責任和擬制責任,量化其對刑事責任的影響。被害人過錯責任在法律中的地位應當有所上升,這樣對被害人提升危險預防意識也能起到一定作用,且有利于他的“刑事伙伴”——犯罪人的定罪量刑。
另外,司法機關應當增加對被害和被害人的研究,分析被害人的類型以及致使被害人遇害的因素,推進被害預防理論研究和實踐的發展,并且普及被害預防教育,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降低犯罪率和被害率,保障社會秩序穩定。
5 結語
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無形的“刑事伙伴”關系,讓部分案件的被害人在具有可責難性,從而對犯罪人的定罪量刑產生一定影響。但追究被害人在其中的責任并不是最重要的,更為重要的是每個人應該盡力避免淪為被害人,同時也不去侵害他人利益。
參考文獻
[1]劉軍.事實與規范之間的被害人過錯[J].法律論壇,2008(05):83.
[2]伍順豪,李金鋒.刑事伙伴關系視角下的高校電信詐騙機制研究[J].法制博覽,2019,(05):2022.
[3]張澤堯.在“刑事伙伴”視野下探討被害人的“反抗”與加害人的“犯意”[J].法制與社會,2018,(34):208210.
[4]謝欣欣.被害人過錯行為對刑事責任的影響與適用[D].南昌:江西財經大學,2019.
[5]張遠煌.犯罪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6]高銘暄,張杰.刑法學視野中被害人問題探討[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6,(01):1116.
[7]朱方圓.論被害人過錯對定罪量刑的影響[D].揚州:揚州大學,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