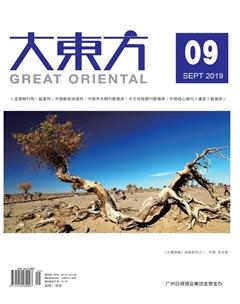論老舍小說《歪毛兒》中主人公的“病眼”
張藝偉
摘 要:老舍的短篇小說《歪毛兒》模仿了英國作家貝雷斯福特的小說《隱者》,主人公以一雙“病眼”觀世,透視了人格結構中本我、自我與超我三者之間的沖突,將人性的特點暴露出來,本文試圖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視角解讀主人公“病眼”產生的原因、表現以及揭示出其深層意蘊。
關鍵詞:“病眼”;人性;本我;自我;超我;社會文化
引言
老舍短篇小說《歪毛兒》,載《文藝月刊》4卷4期(1933年10月7月),小說以第一人稱敘事,“我”與主人公歪毛兒為舊時同學,在闊別二十余年后意外重逢,講述各自若干年的人生經歷,從中我們了解到歪毛兒的思想性格以及他神奇的“病眼”,展現了五四時期“畸零人”的人生境遇。
《歪毛兒》是老舍的模仿之作,卻并未完全照搬,有一部分來自作家的生活經歷,少年歪毛兒以老舍幼時同學羅常培為原型,文中“可惡的神氣”又可與老舍小說《大悲寺外》中丁庚的性格聯系起來,可見,老舍在創作《歪毛兒》時將過去熟悉的人、熟悉的人物加以重組塑造新的人物,與以往不同的是,歪毛兒的性格并不能簡單歸結于生理疾病,而是深入精神層面,他透視人的思想活動,看透人世的丑惡而厭世。
一、與《隱者》的關聯
老舍曾自述云:“《歪毛兒》摹仿了英國作家貝雷斯福特的小說《隱者》。”1并說:“我老忘不了它,也老想寫這樣的一篇……結果是照樣摹了一篇;雖然材料是我自己的,但在意思上全是鈔襲的。”2
《隱者》主要敘述一位名叫“考不來”的隱者,他由于自幼患有一種“眼病”而獨居小島。《歪毛兒》主人公白仁祿同樣患一種“眼病”,與考不來回頭便看見他人的可惡所不同的是,歪毛兒“病眼”的發作是間歇性的,一旦發作他眼中的老師、同學、父母兄弟的臉上都是可惡的神氣,老舍對貝雷斯福特奇幻的想象深入到了心理層次,觀測其心靈面貌。
兩篇小說在主題上有些差異,《隱者》悲觀消極,考不來無法忍受所看到的“畜類世界”,連最親最熟悉的人也是如此,因而選擇逃避荒島;而歪毛兒也十分苦惱自己的“病眼”所帶來的矛盾,一直在堅守自己與改善自己兩者之間徘徊猶豫,最后他選擇了渾渾噩噩流蕩在世間,成為一個“孤獨者”,體現了老舍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揭露以及對人性本質的探求。
二、“病眼”的成因
“病眼”是作家創作的必備條件,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這種“第二視力”超越了生理視力,具有透視的能力。
1、壓抑與分裂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特別強調成年后的心理與行為往往可以追溯到兒童期,弗氏在《精神分析引論》中指出:“我們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經驗和成人生活的經驗,卻完全忽視了兒童期經驗的重要。”3從歪毛兒兒童時期的表現來看,早已顯出異端:“每逢背不上書來,他比老師的脾氣還大……就是不背,看你怎樣!”4歪毛兒作為師娘的“歪毛寶貝”本可以免此手板,卻迎風直上,寧肯淚花在眼里打轉也不妥協,到了中學,只因為別人叫他“姑娘”,便大打出手,歪毛兒此時的心理正是以后的“病眼”形成的基礎。
步入社會后,歪毛兒與社會人的沖突愈演愈烈,歪毛兒的“病眼”甚至影響了正常的生活,他一方面強加干預,另一方面又時刻壓抑自己,使他在這兩者之間痛苦矛盾。“壓抑”在精神分析中特指社會性意識對人本能欲望的監視和壓制作用,白仁祿說:“三十多也就該死了,一個狗才活十來年。”1可以看出白仁祿對于人生是不抱有希望與出路的,社會于他而言就如同狗在人世一樣沒有意義。欲望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人混跡于社會必須要隱藏的東西,社會使他備受壓抑,對他自身也進行重重封鎖,他被視為異端、神經病,人類文明的歷史正是本能被壓抑的歷史,由于本能始終處于人格的深處,從未放棄過抵抗,正是在抵抗與被壓抑的過程中,造成了人精神上的分裂與痛苦。歪毛兒在壓抑本能的環境中,通過“病眼”來釋放自己的本能,用極端的方式表達出來,情況歸根結底是未被抑制的本能的發展與被抑制的本能的受挫相矛盾的結果。
2、癔癥。
1987年,弗洛伊德與布洛伊爾出版了《癔癥研究》一書,將癔癥的起因歸于意識與潛意識的沖突,是人潛意識受到壓抑的結果。
有研究表明,人格特質是癔癥產生的重要因素,歪毛兒的情緒不穩定,易產生焦慮、憤怒等不良情緒,當他看到“可惡的神氣”就想打、想罵,而且他的注意力過度集中于不良事件,他對“病眼”透視出的現象久久不能釋懷,由于他所受到的教育以及社會秩序對其規范制約,他的潛意識企圖侵入意識或前意識,而意識或前意識嚴格把關,致使潛意識一直處于被抑制的狀態,同時他又對外部的環境充滿敵意、難以適應,當發生應激的事件時,他那種不良情緒積壓,難以排泄,因此產生癔癥。他處于憎惡與敷衍的雙重焦慮之中,這種心理動機的矛盾,使得癔癥愈演愈烈,不得不躲避人際交往,脫離正常人的生活。
三、人性惡
達爾文生物進化論認為人類是由猿類演變而來,同時也會保留著動物的獸性特點,人與動物存在必然的聯系。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論深受達爾文的學說的影響,本我便是人格中最原始的部分,包含著人的基本欲望、沖動和生命力。弗洛伊德由此認為人性本惡,在人的理性之下,有著許多的生理需求和本能欲望。汽車夫對一個無辜的小女孩要軋碎了的心理,這種破壞性的本能欲望在人的心理深層或多或少的存在著,弗洛伊德明確主張“人性惡”,本能是先天存在的。
弗洛伊德認為死的本能是最原始和基本的本能,當其內在的活動時,便保持沉靜,只有它轉向外部成為破壞本能。當歪毛兒不犯病時,他便與世界復和,對小貓小狗都很和氣,可他犯病時,便沒法管束自己,動起手來;汽車夫軋死小女孩的心理過程正是人性之顯現。死的本能表現出來的便是破壞、征服、殘暴等,所以人性是惡的。另外,死的本能為了保護自己而對外部世界的危險有破壞的沖動,因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以,弗洛伊德認為人本性為惡。歪毛兒“病眼”的發作,一方面是希望破壞眼前人性之惡,另一方面自己的行為也是一種破壞性的,也是可惡的。
弗洛伊德作為性惡論者很注重人的自然屬性,肯定本我的價值,承認人欲望的合理性,本能之所以有破壞的力量,是因為它無時無刻不在追求自身的滿足,是一種純粹的、自由自在的力量,無論汽車夫殘忍的心理還是歪毛兒破壞性的本能都從側面反映了人的本能由于受到壓抑,不得不通過別種途徑發泄,或者隱約可見或者無法遏制,其根本都是本我的沖動。
四、揭示潛意識層面的二重人格——本我與自我
歪毛兒的“病眼”表現出來的雖是破壞性的本能,但從另一個視角來看,“病眼”又是歪毛兒本我反抗壓制的必要途徑,從中揭示了歪毛兒自身的二重人格。通過歪毛兒的“病眼”所反映的社會、人性等問題,從人性本質來看,可以認為是老舍的創作動機,這部作品反映了作家內心的矛盾沖突,老舍向往新文化新道德,卻又不能割舍舊文化舊道德,他的思想新舊參半,復雜且矛盾,處于抗爭與妥協的過程中。在這部小說中,老舍將此種矛盾投射在歪毛兒的身上,將本我與自我的斗爭展示出來。
歪毛兒從學童時的沖動、執拗的脾氣與其說是天性使然不如說這便是本我的一種表現,歪毛兒不愿違背內心的聲音,后來他也說起都是這雙“病眼”在作怪,歪毛兒的本我可以說是最純粹自然的,對于表里不一的人極其厭惡,通常人的本我都被壓制在意識的最深處,展露出來的只是自我與超我,這二者又是迎合社會現實與道德規范形成的,必然有其社會性的一面,人人如此便得出人人可惡的結論,白仁祿的“病眼”正是其本我的眼睛,本我一直處于壓制的狀態,當他犯病時本我極力反抗,沖破薄弱的監管機制,當他正常時,本我便被重新壓制,自我和超我成為了主體,于是想“回到人生的舊轍”“老老實實去作孝子賢孫”,但終究歪毛兒的本我異常強盛,他看到太多丑惡的現象,有時甚至自我懷疑,認為自己也是可惡的。
結論
本文通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相關理論對歪毛兒的“病眼”進行了分析,老舍對精神分析學有所研究,老舍在齊魯大學《文學概論講義》的講稿講到弗洛伊德以及心理學對文學的影響,但本文對于精神分析對老舍的影響來源尚未研究,此外,老舍在《我怎樣寫小說》中將《歪毛兒》定義為模仿之作,但是對被模仿的作品《隱者》的作者及其創作情況缺少充分的研究資料,這與老舍在英國時所做的文學研究有關,還有待進一步搜集資料,以便更加詳實的分析老舍這部小說。
參考文獻
[1]老舍:隱者[A],《齊大月刊》1卷4期,1931.
[2]老舍:《我怎樣寫短篇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3]老舍:《老舍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4]弗洛伊德著,高覺敷譯:《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