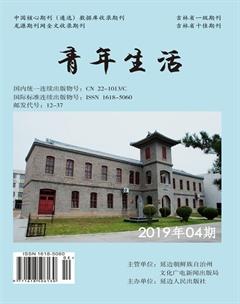生態角度下解析狄更斯文學倫敦
李灑灑
摘 要:作為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現實主義小說家之一,查爾斯狄更斯把寫作重點更多地放在下層階級的生活描寫上,以反映現實社會中的假惡丑,表述他對維多利亞社會的態度。然而,他的作品在反映社會狀況的同時,也披露了一系列嚴重的生態問題。小說對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問題,及生態惡化的根源進行了批判。其生態批評思想對人類在文明的進程中思考生態與人、生態與文學的關系奠定了基礎。本文從生態批評的角度對狄更斯的作品進行分析和欣賞,并隨著對“真實”倫敦的介紹,試圖將真實的倫敦與真實的倫敦聯系起來并加以區分。
Abstract:As a realistic novelist, Dickens laid more emphasis on the lives of the lower class workers to reflect the odiousness of real society and to voice his attitude towards Victorian society. Therefore, His works reflect not only the Victorian social conditions but also a series of serious ecological problems. On one hand, Charles Dickenss depiction of Londons environment can be viewed as eco-literature, and this thesis analyzes and appreciates Dickens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On the other hand, Dickenss rhetorical depiction exaggerated the ugliness that existed in the society.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real” London, in the end of this thesis, this thesis alternates between fact and fiction and attempts to connect and distinguish literal London and real London.
一、引言
作為維多利亞時期的文學巨匠,狄更斯在作品中從各方面再現了倫敦的面貌。其作品以描繪人心、批判現實為名,能夠很大程度上激勵人類去思考和探索正確的、可持續的工業科技的發展方式。因而,解析其作品中人、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便成為狄更斯研究者任重道遠的使命。而生態批評以結合歷史賞析文學為前提,將文學與自然合二為一,以自然為前提,探究文本中人與人、人與社會、社會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的內心世界,從而揭示文學作品所隱含的生態思想、生態危機、生態審美等藝術表現。因而,從生態批評的角度來賞析狄更斯筆下的文學倫敦與真實倫敦意義深遠。本文從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及精神生態展開論述,以對比賞析狄更斯筆下的文學倫敦與真實倫敦。
二、生態批評角度下的文學倫敦與真實倫敦
倫敦是狄更斯的生活之地,更是他創作靈感的源泉。狄更斯用其一生去探索倫敦的奧秘,倫敦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景都被他融進作品之中,他以倫敦為真實背景,加以虛構的人與事,構建了自己的倫敦城。
第一節 倫敦的自然環境
倫敦的新生者——煙霧
社會工業化帶給人們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問題。英國工業革命和城市化在科技、交通等方面都取得了偉大成就,然而工業化的發展在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對生活環境造成了破壞、埋下了健康隱患,比如臭名昭著的“倫敦霧”。而生態文學揭示自然與人之間的關系,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深入思考人、自然與社會的關系,反思社會進步的過程中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狄更斯在其作品中將作為文明象征、熙熙攘攘的大都市倫敦,描繪成“霧都”,實則可以啟發讀者反思工業化的發展,以達到人與自然和諧進步的目地。
城市,作為人類征服自然的產物,與自然對立存在。隨著工業的發展,倫敦這座輝煌的城市變得越來越強大,享有“世界工廠”之美譽,然而靚麗的背后卻是不堪入目的骯臟、犯罪與混亂。“煙霧”,作為狄更斯小說中常見的意象,具有特殊的意義,它代表倫敦空氣的惡化,也暗示倫敦人對物質的欲望漫入倫敦的各個角落。那么,狄更斯筆下的煙霧是否就代表狄更斯內心確實有種生態保護思想或是生態意識?作為讀者,沒有經歷過作者的人生歷程,我們無法對此下論斷,因而本章節僅結合史料與小說,從生態思想來論述、分析狄更斯筆下的倫敦。《大霧霾:中世紀以來倫敦空氣污染史》(PeterBrimblecombe,彼得布林不爾科姆,1988)與《發明污染:工業革命以來的煤、煙與文化》(PeterThorsheim彼得索爾謝姆,2006)兩書均為對倫敦煙霧污染研究的代表作。前者側重于描述煤煙污染是主要污染源,而后者則側重于論證英國人對“煤煙是屬于空氣污染物”的逐漸理解。該書表示,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人并不認為煙屬于污染物,反而是一種社會構建。也就是說,在19世紀的倫敦人看來,煤煙是一種社會產物,而不是污染物。
狄更斯對倫敦霧的感受頗為復雜些。狄更斯生活和創作的時間,正是19世紀中葉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前期、工業革命基本完成的時代。他以作家敏銳的觀察力加以撰寫文稿的經驗,將此時倫敦的面貌還原到小說中去。“狄更斯的小說反映了19世紀早期倫敦的一個重要問題,那便是煙霧以及令人窒息的腐蝕物氣味”[[1]]。正如他在《荒涼山莊》的開篇所述,“到處是霧”,霧彌漫在“小島”與“桅檣”之間,鉆進了“格林尼治區”。霧,無所不在。那么這里的“霧”是指大自然的霧嗎?實際上,筆者認為,狄更斯筆下的霧,是自然氣候條件與工業污染合成的結果。從小說開篇不難看出,狄更斯描寫的是沿海場景,有船、小島,這里的霧氣可以解釋為自然現象,但是文章后面又寫到“大街上,有些地方的煤氣燈在濃霧中若隱若現”,這里的“霧”就難免帶有工業氣息了。煙霧是工業化的象征,記錄了倫敦的工業革命,暗示著工業城市的污染。在小說《艱難時世》中,霧更是“焦炭城”的重要情景。“這個小鎮到處都是機械與高聳的煙囪,它們永不停歇地冒著黑煙,不斷裊繞的煙霧猶如幽幽陰魂,永遠沒有散去之日”[[2]](P34)。“焦炭城”可以看作是倫敦城的縮影,而“不斷裊繞的黑煙”則正是倫敦城上的煙霧黑煙,“永不停歇”則表明倫敦的工廠運轉不停。在《霧都孤兒》中,奧利弗一入倫敦街頭,就感到“街道非常狹窄,滿地泥濘,空氣中充滿了各種污濁的氣味”[[3]],而倫敦的夜是“夜色一片漆黑,大霧彌漫。店鋪里的燈光幾乎穿不過越來越厚濁的霧氣,街道、房屋全都給包裹在朦朧混濁之中。”可見,倫敦這座工業之城儼然飽受工業廢煙的侵襲。但從小說中“煤煙從煙囪頂上紛紛飄落,化作一陣黑色的毛毛雨,其中夾雜著一片片煤屑,像鵝毛大雪似的”這段描寫可以看出,狄更斯沒有直面指出煙霧對人類的危害,而是將倫敦霧美化為小說中的意象。身為作家,為渲染情感基調,美化周遭環境并無可厚非。但這并不代表狄更斯就反對或著支持工業發展。唯一不可否定的是,狄更斯已經注意到倫敦的空氣污染,并將這一現象記錄在自己的作品中。
第二節 倫敦的社會環境
新型社會的新生物——火車與工廠
“生態文學對工業和科技的批判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工業和科技本身,而是要凸顯人類現存工業文明和科技文明的致命缺陷,促使人類思考和探尋發展工業和科技的正確道路,以及如何開創一種全新的綠色工業和綠色科技”[2](P230)
作為現實主義作家,狄更斯對工業科技的發展有自己的見解。他在構建“文學倫敦城”時,選取現實倫敦的社會背景,包括當時發達的交通運輸,即馬車與海運,而火車作為新型運輸工具更吸引了這位文學巨匠的注意。當查爾斯狄更斯13歲時,第一條鐵路在英國建成,并持續快速發展。1825年時,英國的鐵路總長為25英里,1838年已超過500英里,到了1848,約為4646英里,而在1870年,即查爾斯狄更斯逝世那年,鐵路的長度已超過13500英里。鐵路的發展一方面反映了新的運輸工具,另一方面,它對自然產生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狄更斯的小說中,《董貝父子》最能清晰地展現交通工具從驛站到火車的轉變。《董貝父子》中曾多次提及火車這一重要意象,每一次都被賦予了深刻的含義。而狄更斯正是借不同的意義去邀請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去思考——機械化的發展對人類社會究竟意味著什么?從小說中可以看出狄更斯在對火車的多次描寫中褒貶不一,同時也反映了他對工業化進程的態度——既懷疑又贊同。
當波利帶著董貝之子和蘇珊回家探望時,文中第一次出現對火車的描寫:“第一次沖擊的大地震剛剛在那個時期”[[4]](P81-82)從字里行間,讀者能輕而易舉地推測出查爾斯狄更斯對鐵路的態度。他把鐵路描繪成“地震”,給斯塔格斯的花園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骯臟的街道、成堆的腳手架、荒蕪的磚塊等等,這些都暗示了他對火車的懷疑。火車也被賦予了死亡的象征——高速列車是保羅快速死亡的象征。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反映了狄更斯的態度—工業的快速發展將會導致人類死亡。正如他在小說中所說的:“火車疾馳而過的速度,嘲弄了這條疾馳而過的年輕的生命,這種生命被如此堅定地、如此無情地帶到了它命中注定的終點。”[9](P348)在故事的結尾,狄更斯更是把火車描繪成“火辣的魔鬼”和“這些接近的怪物”,并用“兩只紅眼睛”和“兇猛的火焰”試圖毀滅世界。與擁有不可抗力量的火車相比,人類和大自然只能忍受它的折磨——噪音和毒氣。然而,這種極具破壞性的新型物真是人類進步的產物,它確實給人類帶來了很多好處。因此,狄更斯并未表明禁止使用火車,只在文中指出火車所代表的新事物的弊端,以告誡人類合理使用新發明,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不僅在交通運輸上取得了飛速發展,在生產方式上也一改前貌。工廠的生產方式以機器運作為主,因而很快興起了一批如倫敦、伯明翰等的工業城市。然而星羅棋布的工廠在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在肆無忌憚地排放滾滾濃煙,給工業城市染上一層陰沉的黑色,正如朱虹在《狄更斯小說欣賞》中所述“狄更斯筆下的現代工業圖景是一片混亂、喧囂、污穢與恐怖。”[[5]]除此之外,隨著新興工業城鎮的興起,大量勞動力涌向工業,唯利是圖的資本家也開始壓榨工人階級,“這里的人們,是工業的犧牲品和機器的奴隸”。狄更斯作為現實主義作家,當然也少不了在其作品中下濃筆針砭時弊一番。
在《老古玩店》中,狄更斯在描寫吐倫特與外孫女耐兒之間感人的親情時也揭示了工業化進程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當他們被迫逃離倫敦,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時,狄更斯寫道“煤灰和煙塵”給枯萎的葉子和花朵“鍍了層黑色”,而“掙扎的蔬菜”像是“生了病似的在火灶和熔爐的熱氣噴射之下低下頭來”,周圍的一切好像“更要枯萎而又死氣沉沉”。可見,工業污染的魔爪已經伸向了代表淳樸、善良的鄉村自然之景,這也預示著耐兒的不幸。廖無人煙的荒野之地,沒有一根草的生長,沒有一朵花開放,唯一透著生命之綠的便是“黑土道旁懶洋洋地噴撒著熱氣的死水池塘的水面上浮起的一層青碧的苔蘚。”狄更斯清楚地意識到工業化與自然美的矛盾所在,工業化的進程必將導致自然美的不復存在,詩意的生存環境將江水東去般一去不復返。因而不惜花大筆描寫周圍被破壞的環境,以在讀者閱讀小說的同時,激發其生態保護意識。
第三節 倫敦人的精神生態
三、物欲橫流的倫敦人
作為小說的一大要素,人物描寫的好壞直接決定作品的優次。而狄更斯筆下的倫敦人物通常有兩種,扁平人物和圓形人物。圓形人物一般指性格比較飽滿,通常為小說中的主角,比如《遠大前程》中的主人公皮普,先是淳樸節儉后變得揮金如土,最后承認錯誤重拾淳樸。而扁平人物在小說中則表現為性格單一,比如《艱難時世》中的龐得貝一味強調“事實”,《遠大前程》中的喬,正直如一。為了全面鑒賞小說,生態批評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將人物考慮在內,重點對人類欲望進行批判,包括對大自然不計后果的掠奪以及由欲望而導致的自然淳樸天性的喪失。
欲望作為經濟發展的精神副產品,是社會進步的巨大動力,同時也是最難控制的。“在生態學家看來,欲望就像從瓶子里釋放出來的惡魔——一旦釋放,就很難再控制。”[2](P243)狄更斯的時代處于經濟高度發展的時代,然而在關注經濟發展的同時,人們卻忽略的精神的同步發展,最終導致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的脫節。狄更斯這位文學巨匠,用自己筆下的倫敦人物將這一社會現狀描繪的淋漓盡致。
《遠大前程》中的皮普本是單純善良的小男孩,卻在物質的驅使下逐漸失去淳樸,追求享樂,甚至因害怕艾絲黛拉的挖苦而嫌棄自己的老朋友喬。“我開始覺得做個鐵匠是丟人的事”表明皮普的內心已經開始被上層階級的物質生活而腐蝕。而當他與喬分離的時候“手足之情的淚水竟這么快流干了”再一次證明富貴的生活擊敗了淳樸的友情。而后皮普在倫敦的奢靡生活更是與先前的貧苦生活形成了巨大差異。皮普變得揮霍、奢靡,而他心靈的扭曲正是基于對物質、金錢的渴望。幸而皮普的善念始終沒有被抹去,他最終幫助了自己的朋友、贊助人,并向老朋友懺悔。這也說明,狄更斯對當時社會的態度——他并不抵制經濟的發展,只是呼吁社會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多關注心靈的健康成長。
人性的扭曲在《艱難時世》中也得以體現。葛擂梗先生是煤炭鎮的中產階級,生活優越,卻視自己的兒女為“知識的儲存罐”,逼迫孩子按照自己的思維去生活,過分強調“事實”,然而他眼里的事實在現實生活中卻是謬論。他為了孩子所謂的“美好前程”,不顧年幼之差將自己20歲不到的女兒嫁給自己50歲的好朋友,并且認為“從你們的財產和地位來看,沒有任何不相稱;相反,非常合適。”,認為30歲之大的年齡差不足以造成婚姻障礙,最終因自己的“事實”釀成兒女的悲劇——-兒子逃往國外,女兒婚姻不幸。小說中,做為商人的葛擂梗先生口袋中總是裝著尺子、天平還有乘法表這些用于測量“事實”的物件,說明金錢利益已經融進他的身體,與他終日相伴。作為商人同樣的精神狀態在《董貝父子》中也可以看到,在董貝眼里不存感情,所有的只是金錢關系,正如他對仆人所說“我的孩子不需要愛上你,你也不需愛上我的孩子,你的任務完成了便可離開”。他對人情的冷漠不僅僅限于對仆人,對自己的孩子,妻子亦是如此。他唯一寵愛自己的小兒子,視女兒為“一枚劣幣”,認為妻子的去世只不過是家里的值得擁有的物件少了一個,這種冷若冰霜的人際關系在他眼里一文不值。董貝認為有了錢就有了一切,然而,正是他的這種畸形價值觀導致了小兒子的夭折,第二任妻子伊迪絲的拋棄以及經理的背叛,最終人財兩空。這兩部小說中均設有對比對象來突出小說主題。在《艱難時世》中,狄更斯在描寫資本家葛擂梗是也在花重筆描寫馬戲團之女西西朱浦,即后來的塞西莉亞,并將西西的美好生活與葛擂梗之女路易莎的不幸婚姻做對比,突出自然淳樸的重要性。而《董貝父子》中的董貝生活與普通民眾,如火車工人圖德爾一家的幸福生活形成對比。狄更斯在這些普通人民身上種下了人類美好天性的種子,因而結出幸福的果實,也許狄更斯對底層民眾的偏愛正是出于對他們淳樸之心的贊賞。
四、結語
狄更斯將倫敦視為指引自己寫作的“神燈”,照亮自己的寫作脈絡。無論是從倫敦的社會狀況、自然狀況還是倫敦人的內心來看,狄更斯的作品都與同時代的倫敦難舍難分,揭露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倫敦的邪惡面。從生態批評角度賞析狄更斯筆下的倫敦能清楚的看到倫敦的方方面面,大到倫敦社會,小到個人內心,而這正是現實主義作家的寫作目的,讓讀者身臨其境般融進這虛擬但又現實的社會,并且給自己植入維多利亞時期倫敦人的思想,最后,再回頭判斷這種思想的合理性,以達到啟迪讀者反思現實的目的。之所以說狄更斯筆下的倫敦是虛擬而又現實,是因為狄更斯在構建自己的倫敦城時既選用了真實的社會背景又融進虛擬的人物與事件。但是,狄更斯筆下的倫敦環境不應該被視為科技文明與工業文明發展的結局,而文明與進步的定義也不應該僅局限于對人類而言而棄自然于不顧。但倘若將真正的文明進步視為如梭羅般通過感悟大自然豐富精神世界的話,人類就不能進行科技工業的發展。因而,人類只有在城市工業化的過程中,獲得應對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的方法,與自然和諧共處,才能達到真正的文明與進步,而這也正是從生態批評角度所獲得的狄更斯的生態觀。
參考文獻:
[1]莫林斯塔克,楊小丹.狄更斯與倫敦[J].世界文化,1986(4):10.
[2]查爾斯狄更斯.艱難時世[M].盛世教育西方名著翻譯委員會(譯).上海:上海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
[3]查爾斯狄更斯:《霧都孤兒》[M].榮辱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1984.
[4][英]查爾斯狄更斯:《董貝父子》[M].祝慶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5]朱虹.狄更斯小說欣賞[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