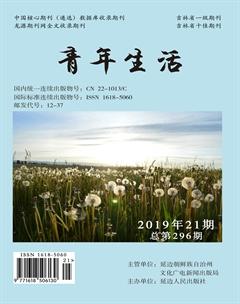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李靜
《法律的道德性》一書產生于哈特與富勒的一場著名論戰(zhàn),圍繞著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和“惡法是不是法”這兩個分歧而展開。哈特認為應分清法與道德,富勒指出法律自身具有道德性,法律秩序要以道德為基礎,法律與道德是密切聯(lián)系的。本文認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且法不溯及既往。
一、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哈特認為法律與道德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聯(lián)系,這是源于人的“自我保存”的需要,但是這種聯(lián)系是一種“偶然的”聯(lián)系,而不是一種“概念上的”必然聯(lián)系。富勒基于惡法非法的前提下,認為道德的外延比法律大同時包含著法律,也就是說法律屬于道德的一部分,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并不是法律與其他類似規(guī)則之間的存在于外部的關系,而是法律規(guī)則自身的內在要求。其表現(xiàn)形式則可以是規(guī)定于法典中的各項條文,更可以是種種一般原則,而法院的司法過程則是在憑據(jù)他們的良心和知識,以這種最低限度的道德而對種種行為進行衡量,以斷定各種行為是違法還是合法。總之,法律不能違反良知,使人服從規(guī)則治理的時候,如果情和理發(fā)生沖突,西方普遍的觀點是尋求良知的指示。
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強調仁者愛人,仁者先培養(yǎng)其主觀之仁心,復按其能力所及由近及遠推廣其客觀之仁行,對人們的內心的道德以及自身修養(yǎng)的要求是比較高的。法律的規(guī)則,其實是將很低要求的道德規(guī)制起來,即作為一個存在于社會生活中的人,無論修養(yǎng)水平是何層次,都不能觸碰的底線。如果把過高的道德轉化為法律義務,那定會適得其反。傳統(tǒng)儒家的思想中主張德主刑輔,治國方法為“養(yǎng)”“教”“治”,“養(yǎng)”“教”之手段為德、禮,“治”之手段為刑、政,教化為核心,故以德禮為主,刑政為輔,這是一種比較完善的理想,但是離現(xiàn)實較遠,因為規(guī)則治理從很高的道德來轉化是比較困難的。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關于故意殺人,是法律明確禁止的,因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所以不能實施故意殺人的行為就是很低很低的道德要求了,所以它能得到普遍認可并成為法律。關于對他人生命的尊重,高的道德要求就會要人們博愛每一個生命,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等,如果法律要求如此的話,要得到普遍認可并遵守就會很困難,從而變成一個高高在上不能實現(xiàn)的理想型法律。
法家主重視法律的作用,以倫理道德為無用之物,強調斷于法,賞罰分明,重刑輕罪,統(tǒng)一標準,以吏為師。而儒家思想則是完全相反,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家強調法律的作用,一家強調道德的作用,但兩家都屬于對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式推向了極端的狀態(tài),兩家所言各取一部分相結合,就會是很好的,即所說的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道德是以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方式來約束著人們的行為,而法律不行,它要靠外力,具有他律性。但是“強扭的瓜不甜”,不是發(fā)自內心的去遵守并不是真正的遵守,也并不能真正實現(xiàn)法律存在的目的。只有樹立法律的權威,建立人們法律的信仰,才是真正的法治之路。如伯爾曼所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法律只有符合正義,符合道德要求,才能喚起人們內心的共鳴,才能取得人們的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
二、法不溯及既往
法不溯及既往意味著一部良好的法律的時間效力范圍是以法律的生效時間作為法律效力的時間起始點,即法律是前瞻性的,它調整的主要是人的未來行為。同時,法不溯及既往也是對人權保障的內在要求,每一種類型的法律都是在誘導或阻遏人們做出某種特定類型的行為,如果一個行為在作出時是合法的,那么行為者必然會毫無顧忌地去實施,而新的法律出現(xiàn)時卻要求為原行為負責,這就是很恐怖的。正如富勒所說,法律是用規(guī)則來規(guī)范人的行為,說用明天將會制定出來的規(guī)則來規(guī)范和指引今天的行為等于是在說胡話。
在《法律的道德性》附錄中,提到的怨毒告密者的難題,紫衫黨統(tǒng)治后遺留下來的告密者的問題,我認為應該從法不溯及既往的角度考慮。首先,應當考慮告密者行為作出時的統(tǒng)治背景:《刑法》條文的公認含義被扭曲,以便將政治上的反對派投入大牢。秘密法規(guī)獲得通過,其內容僅為黨內高層領導所知。溯及既往的法律紛紛出臺,將履行之時完全合法的行為確定為犯法。政府毫不理會憲法、早先的法律甚或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所設定的限制。反對黨,持不同政見的人被迫害。從告密者的目的來說,許多人是為了泄私憤而舉報仇人,但我認為這不影響其行為在當時具有合法性。他們所舉報的行為根據(jù)當時掌管國家事務的那個政府的規(guī)則是非法的。他們的受害者所遭受的處罰是根據(jù)當時有效的法律原則來作出的。這些原則以我們認為可憎的方式背離了我們所熟悉的那些原則。不過它們的確是當時的國法。而且他們所舉報的有些行為在后來的統(tǒng)治時期看來是一些比較輕微的小事,但對當時的統(tǒng)治可能產生較大影響從而懲罰較重,不能由此而認為告密者將受害者陷入了絕境。不可否認,紫衫黨統(tǒng)治時期的法律是惡法,時代過去之后,我們可以用惡法非法來評論當時的那些法律制度,因為當時的所謂的法簡直就是一種“無法”,它的規(guī)則完全取決于統(tǒng)治者一時任意的思維想法,但是我們卻不能要求那個時代的每個人都有能力去識別這些規(guī)則的好惡,或者說,即使大家能識別出來那是惡法,我們能要求他們有能力去對抗惡法嗎?我認為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因有一點是既往的行為有當時的時代背景,物質條件、統(tǒng)治思想的差異都會造成思想價值和行為方式的差別。針對紫衫主義的弊病,還是應該制定法來撤銷和矯正,使社會秩序回歸到一種有序的統(tǒng)治時期,規(guī)則治理,而不是那種任意性極大的統(tǒng)治者意愿治理。但是這樣的法律只是為了維護現(xiàn)在及今后的秩序,而不關系到之前的行為。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是立法者旨在提高法律的穩(wěn)定性和可預測性,合理地安排權利義務,實現(xiàn)歷時性社會公平的調整機制。
結語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如此緊密,如果沒有道德的評價、滲透與補充,法律根本就不能得到很好施行,所以,法律必須包含著道德的要求。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所以,法不強人所難,在法的實施中,堅持不溯及既往就是一種體現(xiàn)。
參考文獻:
何卿源,嚴國瓊:“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從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中尋‘法律是什么”,載《法制與社會》,2007年4月,第45頁。
劉風景:“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的法治意義”,載《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4卷第2期,第18頁。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