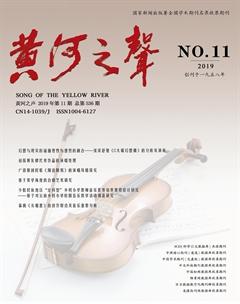樂器教學中影射的性別問題
張煦
摘 要:性別差異是社會中最為常見的群體差異現象,它滲透在社會互動交往中的方方面面,在音樂教育中性別差異雖然被弱化,但同樣存在因性別差異產生的種種問題。樂器常常被人冠以性別的刻板印象。本文通過列舉兩例樂器教學的性別問題,討論當下樂器學習現狀存在的問題,簡要分析樂器性別刻板印象的歷史由來,并提出一些能夠改變現狀的期寄。
關鍵詞:樂器教學;性別差異;刻板印象
在我們身處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都存在相同與差異,相同產生凝聚力,差異則隱藏著挑戰。這些差異包括性別、人種、社會經濟地位、性取向、年齡、民族、能力大小以及地域等等,其中性別差異是社會互動中最常見且最容易感受到的差異之一,也是社會公平問題中的焦點。例如,性別的差異在就業中被放大,一些工作只接受男性工作者,或在有特殊需求的女性群體面前一味追求“平等”,還有一些工作被性別固化,比如當男性工作者從事護士這一職業時很大可能會遭到歧視,再如大部分女性常常被認為駕駛技術欠佳,從而產生“女司機”的標簽,導致從事駕駛行業的女性也同樣會遭到質疑。諸如此類的性別差異所導致的公平問題存在于在社會活動的任何空間與時間,而在音樂中,性別差異的境況卻不太一樣,大眾認為音樂和音樂教育為同性戀、雙性戀以及變性者提供了“避難所”,雖然這一點迄今為止還沒有相關研究予以證明,但是這或許可以提示我們不僅在性別甚至到性征、性向的差異在音樂與音樂教育中都被弱化了,音樂向來崇尚自由的表達,不排斥差異鼓勵新穎,因此對此差異具有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在這樣大眾普遍認同的公平沃土上,音樂教育與學習中性別公平是否真的不成問題了呢?
在音樂學習中我們可能會聽說過這樣的言論或者甚至自己就是這樣認為的,當我們聽說一個男孩學習古箏,可能會感到詫異,認為這不是他們合適的選擇,因為傳統印象中古箏無論從音色、調式以及演奏形態來說都富有女性特質,學習古箏可能會使男生陰柔缺乏“男子氣概”,相對的,如同搖滾這樣充滿反叛精神且激烈躁動的音樂形式同樣不適合女生學習,其氣質違背了傳統女性被認為應該具有的恭順與溫柔。由此我們可以引出一個討論,既樂器演奏中是否存在性別角色定勢,目前看來顯然是存在的,那么這樣的現象是如何產生的?器樂教育與學習是否應該被性別所限制呢?
對樂器賦予性別化自古以來便是人們內心根深蒂固的一個認知。并且這種認知并不具有外顯性,它像是已被深深內化,滲透進血液里的一項基因,難以察覺。但非凡的音樂學家們往往具有這樣的能力,他們敏銳的眼光能夠捕風捉影,并且從紛繁復雜的歷史脈絡中梳理出一條康莊大道來。古希臘羅馬時代是西歐文明的起源之所,而其子民的啟智皆來源于赫西俄德的《神譜》,其中可知,掌管文藝的神——繆斯即為女性,據《神譜》中對繆斯的描述可了解到,繆斯一共9人。他們象征著各類古樂器,這一狀況,人們便開始認可樂器本身是專屬于女性的。那時的主要樂器主要分為兩類——吹管類,即阿弗洛斯管,以及撥弦樂器——里拉琴。吹管類較為耗費體力,且音色較為粗獷,而里拉琴演奏出來的風格都較為輕柔、流動、柔美。在這種樂器本身的特征下,加上樂器對一定生理狀態的需求,人們逐漸默認,男性往往適合演奏一些音色較為陽剛、外向的器樂;而女性則相反,她們被認為是情感的代表,是感性的存在,因此那些音色內斂的,陰柔的樂器便被默認為是女性的樂器。在這樣的歷史演變進程中人們一代又一代的將性別與樂器的對應固化進大腦中,直至當今時代仍存在這樣的現象。由此我們思考,為什么會出現上述狀況,學者們提出了一個深刻的觀點,即男女“性別”在社會地位中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社會制度的“父權化”,在這種體系下生存的女性一直處于社會的劣勢,及被忽視的狀態,例如說當我們看到一個男性具有某些“女性”性征的行為出現時,便會不假思索的將此人冠以“娘娘腔”這種極具貶義及歧視的字眼。更為可笑的是,大多數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加排斥這種現象,評頭品足,表現的不亦樂乎。然而卻從未深刻的思考過,在嘲笑這些“女性”特質時,難道不是嘲笑自己嗎?而一旦某些女性具有“男性”的意志、能力。比如面對“女強人”這一類群體時,這些社會人士的眼光們更像是看待“外來物種”一般表現得令人匪夷所思。以上種種社會現象皆闡釋了為何當男性學“古箏”這類被刻板的認為專屬“女性”的所屬樂器時,人們緣何不能“平心靜氣”的接受。抱以詫異的眼光看待,實在令人可笑不已。
現代音樂教育研究的第一代學者已經將性征與性別問題作為音樂教育研究項目的變量來看待,性別的差異在音樂教育中不容忽視,但這些研究只是出于記錄,并非為了改變現狀。而發展到現在研究開始關注那些打破了性別定勢的男孩和女孩們,雖然這些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思路,至少打破音樂學習中的性別角色定勢是一個正確的方向,盡管一些樂器學習已經形成了性別比例嚴重失調的現狀,但是仍然有許多人愿意打破刻板印象,盡可能的脫離其束縛,我們不得不承認,那些突破樂器被賦予刻板性別來選擇學習對象的人中,確實不乏優秀的人才,甚至躋身大家之列,所以無論器樂、聲樂乃至任何音樂領域的教育與學習都不應該至少不能人為的為其下一個定義,設置一個禁錮,在音樂中我們應該擁有公平的選擇,出于個人的愿望與需求進行選擇,不應該因擔心自己內心的趨向與大眾愿望相悖而壓抑自己,不應該被社會其他成員質疑,更不應該被教育者以性別理由排斥拒絕。器樂教學中映射出的性別公平是一個嚴肅且重要的話題,需要得到研究者的重視和開發,在性別差異不可避免的大環境下希望音樂能夠成為真正的避難所。